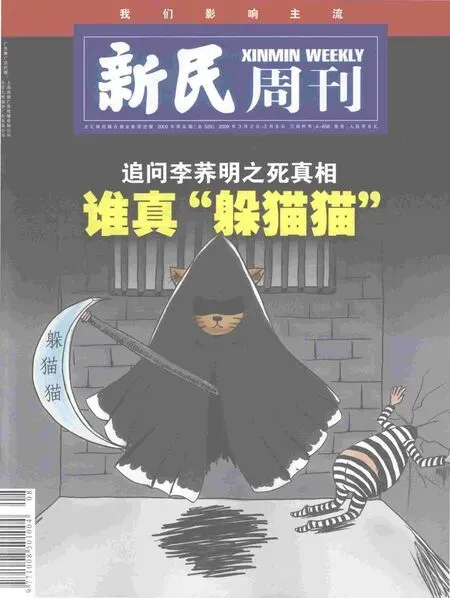“網(wǎng)民各界人士調(diào)查委員會”的困局
王 雷 楊 江 阿玉成

作為調(diào)查委員會的一員,我昨天(1月20日)全程參與了調(diào)查。由官方召集組織網(wǎng)民、媒體組成調(diào)查委員會,對一刑事案件進行調(diào)查,這種方式在中國還是第一次,雖然我做了近十年記者,采訪過許多案件,但像今天這種“身份”去調(diào)查,也是第一次。
刑事案件的偵查、立案、審理有一整套程序,對應(yīng)的職能部門是公安、檢察院、法院,它們的司法權(quán)力來源于國家授權(quán)。記者采訪雖然在我國還沒有得到立法保護和規(guī)范,但是輿論監(jiān)督是媒體的天然功能,早已深入人心。與司法機關(guān)強大的權(quán)力相比,新聞媒體權(quán)力的邊界要模糊得多,而昨天才成立的調(diào)查委員會,它的權(quán)力有多大?邊界在哪里?調(diào)查委員會很快就遇到了這些問題。
到達晉寧縣公安局后,調(diào)查委員會成員、媒體記者與該縣公安局、檢察院7名負責人在會議室展開了第一輪詢問。如果說詢問的環(huán)節(jié)順利,那么調(diào)查委員會的“危機”很快就出現(xiàn)在晉寧縣的看守所內(nèi)。
晉寧縣公安局閆副局長表示,考慮情況特殊,經(jīng)請示后,準許調(diào)查委員會成員進入看守所——可以說,調(diào)查委員會突破了法律的規(guī)定。
在看守所內(nèi),當調(diào)查委員會要求與李蕎明同倉的嫌疑人見面時,原本已同意的晉寧縣公安局、檢察院卻突然改變了主意,拒絕調(diào)查委員會成員會見嫌疑人。
這給調(diào)查委員會帶來很大困惑:會見嫌疑人被認為是最有可能“查明真相”的方法之一,但是調(diào)查委員會是否有權(quán)力這樣做,卻是我們之前沒有想到的。
我認為,盡管社會輿論對辦案的晉寧縣公安局、檢察院表現(xiàn)出極大懷疑,但釋疑的調(diào)查及最終結(jié)論仍應(yīng)該是相關(guān)部門,例如上一級公安、檢察院或紀委等單位作出,調(diào)查委員會沒有權(quán)力,也缺乏專業(yè)能力去“偵破”案件,調(diào)查委員會不能用違背甚至凌駕于法律之上的方法手段謀求真相、公正。
如果大家對晉寧縣公安局、檢察院,甚至更高級別的司法部門喪失信心,那是我們的司法制度出現(xiàn)了問題,正如湖南湘潭黃靜案,在公安部物證專家都介入調(diào)查的情況下,法院判決仍引起極大爭議甚至質(zhì)疑一樣。
晉寧縣公安局、檢察院隨后又以涉及機密為由,拒絕了調(diào)查委員會查看9號監(jiān)倉監(jiān)控錄像和其他證據(jù)的要求,對此,調(diào)查委員會也沒有辦法。
我認為,云南省委宣傳部組織的這次調(diào)查,雖然沒能“查明真相”,但如因此就把這次活動指稱為“作秀”、炒作,仍然是有失公允的。
首先,調(diào)查委員會的介入,使案件的更多細節(jié)得以披露,從而使晉寧縣公安局、檢察院“作弊”的風險增加。
其次,通過這種獨特的調(diào)查方式,使得更多普通公民有了一條新的渠道更接近真相,想到那些閉門偵查、閉門立案、閉門審判而造成的冤假錯案,這條路徑至少提供了一種新形式的監(jiān)督——雖然這種監(jiān)督還很不成熟。
再次,今天我認為自己有兩個身份參加了調(diào)查,一個是調(diào)查委員會成員,另一個是作為首發(fā)李蕎明案件的云南信息報副總編,相比我近年的案件采訪經(jīng)驗,能讓公安、檢察院坐在對面有問必答,在幾年前甚至幾個月前都還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說,調(diào)查委員會的形式,對中國媒體輿論監(jiān)督的價值意義深遠。
最后,調(diào)查委員會本身就是一個鮮明的信號,可以解讀出政府對主動公布、公開信息有了更大壓力,也具備了更自信的心態(tài),而公眾參與公共事件的熱情、愿望、渠道與技巧,也發(fā)展到了一個新高度。
雖然全國第一次民間色彩的調(diào)查委員會的第一次調(diào)查,在倉促中起步,有很多問題、不足,但如果能有更多人提出建設(shè)性意見,使其更符合法治精神,更具有操作性,那么,這一次中國大眾民主監(jiān)督的重要嘗試,意義便大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