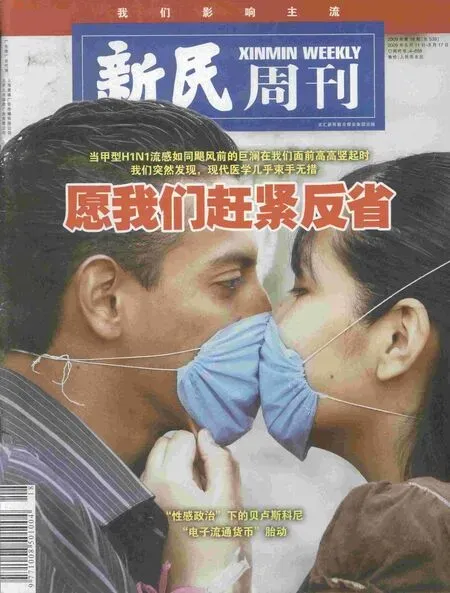面對戰爭的“反諷”
沈 雙

五一小長假回家探親,本來是為了享受親情,沒曾想內地一片戰火硝煙。五一期間電影院上映的兩部大片,《南京!南京!》、《拉貝日記》都是關于上世紀最殘忍的歷史事件——南京大屠殺的。電視里熱播的也是有關戰爭年代的電視劇,《我的團長我的團》和《潛伏》。我先后逛了幾家書店,無意中撿來的書居然也和戰爭有關。宋曉軍等人撰寫的《中國不高興》所倡導的“大目標”實際上就是一種新時代的戰爭思維。
在飛機上翻看海上性文化專家小白的一篇訪談,其中被問及什么是對待性文化最適當的態度,小白答曰,反諷。反諷是一個非常英美自由主義的字眼,意思是說對什么都保持一點距離,最好不要跳出來表達明確的態度和觀點。小白的意思是說,對禁忌固然要采取反諷的態度,對性亦應如此。想起來這戰爭文化,實際上是最反對反諷的。王曉東在《持劍經商:崛起大國的制勝之道》中呼吁:“我們中國需要一群英雄,一個真正的英雄集團。”這是反諷的絕對反面。即便是默默地懺情似的描寫戰爭的陸川,在作品中也是摒棄反諷的。《南京!南京!》里虛構成分最多的那個唐翻譯,本來是很具有“反諷”潛力的一個角色。他為德國人干事兒,稱日本人為“朋友”,保護同時也迫害了一大批中國軍人,保護同時也傷害了自己的女兒和妻妹。他是最準確地理解了“難民營”這個詞的意義的人:難民營就是在兩軍對壘的情勢下為無辜的老百姓提供的一個避難所,而他就是一個老百姓。但是他也是第一個摧毀這個避難所的人,他的告密將日軍引入安全區,使它的中立性不復存在。應該說,陸川的電影里沒有給反諷留有空間,因為情勢太對立了,不可能保持距離。不管是日軍還是中國人,不卷進去的唯一出路就是死亡,要么成為烈士, 要么自殺,像角川那樣。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潛伏》是戰爭文化中的另類。它的主角余則成對待戰爭的態度不能說得上“反諷”,是一種略帶幾分無奈,略帶幾分超脫的復雜態度。余則成因為臥底從一開始就在戰爭的最外圍,大部分時候是沒有辦法顯露他的真實身份的,他甚至懷疑除了自己之外還有沒有第二個人知道他是誰。電視劇剛開始,余就想“自殺”,不是真死,而是借敵我雙方都不知道是誰殺掉漢奸李海豐之后,假裝“殉國”,和他的女朋友遠走高飛,去過自由的日子。
其實我不覺得“反諷”作為一種人生態度在中國文化的土壤里能夠生根開花,這大概是因為我對“反諷”的理解比較狹隘。我更愿意把這兩個字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英國劍橋的知識分子對待現代文明,現代文化的態度聯系在一起。這樣的理解并不意味著其他的文化中沒有“反諷”的態度。
20世紀初劍橋知識分子提倡“反諷”,恰恰是一種面對戰爭的反應。戰爭動搖了精英知識分子對于現代文明的信念,他們需要一種新的宗教,一個新的信仰替代物。于是找到了詩,并把詩的原則定義為“反諷”,也就是說既不擁護,也不摒棄現代機械文明,而是維護自身的原則,屬于一種自善其身式的哲學思想。現在看起來這只不過是一部分精英知識分子對于現實的一種被動和理想化的反應。
而且“反諷”兩個字真的很英國,很冷。或許小白對于性文化的“反諷”態度,來自于上海這個地方某些人對于英國人格的持久迷戀?恰巧《南京!南京!》里的唐翻譯和太太講的是上海話,或者是帶有強烈上海口音的普通話,坐在我邊上的滬籍朋友詫異地說,為什么發生在南京的故事要講上海話?我在想,或許“反諷”就是一種上海文化?
《潛伏》的熱播大概告訴我們除了對于英雄主義的崇拜之外,民間還有一些其他的情緒存在。你說它是“犬儒主義”,但是不能否認,它實際上有原則,有信仰;而且特別重要的是,它是有感情的。實際上,現在全部關于戰爭的敘事都不是在講歷史,而是在講當下。我覺得,《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們如果對當下的流行文化進行一個認真的解讀,而不是從一個未經考察的結論出發,他們對于“中國”以及“高興”的答案都會更為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