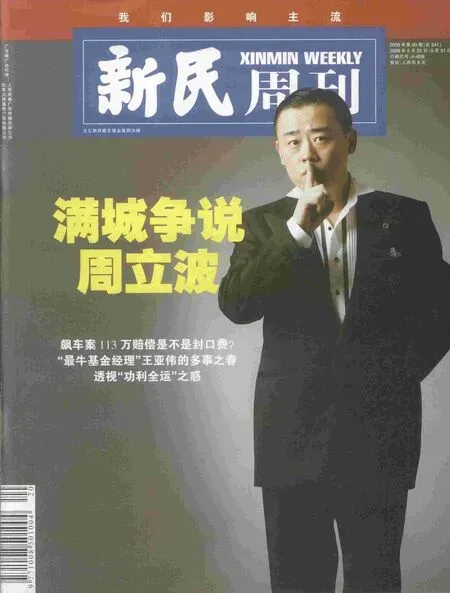從印度大選看“民主”
丁學良

民主制首先是作為一種理想而出現,但對達到理想的過程,不能看得太美好。
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之一印度正在舉行全國選舉。1967年印度大選時,一位英國記者去采訪,給他印象最深的是選民的冷漠與無助情緒。一圈看下來,他得出結論說,經過20年的試驗,印度的民主制度已經失敗了。那是印度第四次全國選舉,他斷言,這將是印度的最后一次全國選舉。BBC的同事對此頗有感慨。
從那時到現在又過去了42年,印度還在舉行選舉。它10多億人口里,選民超過7億,實際去投票的人超過4億。大選是非常復雜的,今年也出現了針對選舉的暴力行為,估計還會有更多暴力發生。因為這些原因,國內有些人像42年前那位英國記者一樣,認為印度的民主已經失敗了。不過,國際上的主流觀點認為,印度的民主試驗基本上是成功的。判斷的標準是,每次大選后,選舉結果都會被主要政黨和絕大多數選民接受,也就是說,新上臺的執政黨具有法統。
對印度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實踐之得失,之所以會出現截然相反的評價,是因為很多人把作為一種制度的民主(民主制)和作為一種過程的民主(民主化)搞混淆了。
簡單地說,沒有民主化是不可能有民主制的,但民主化和民主制是兩個概念。不久前去世的政治學大師亨廷頓,一生中最有名的著作是《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其中有個論點,對全世界的政治學研究者影響極大。他說,關于政治和社會穩定,可以觀察到兩極相似而中間千差萬別的現象。兩極相似是指高度民主的國家和高度專制的國家,都相當穩定,而最不穩定的是兩極中間的那些社會,即追求現代化、迅速發展的國家。為什么會是這樣呢?
人們理想中的民主制,是穩定、公平、廉潔、有效的。這就是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愿意為之奮斗甚至不惜犧牲的原因。而實際上,在民主化過程中發生的種種現象,同人們對民主制的理想之間,落差實在太大。從1980年代末即所謂第三波民主化以來,對民主的許多批評,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比如,民主化過程中常有不同程度的暴力,常有腐敗和不公行為,包括賄選和舞弊,還有一個現象,就是黑社會勢力介入選舉。我們怎么看待這些情況呢?
大部分學者認為,只要局部暴力沒有推翻民主選舉的結果,民主化就邁進了一大步;只要沒有出現系統性的賄選,民主政治運作的結果基本上就被公眾認可了。至于黑社會勢力介入選舉,也要公平看待。不推行民主化,并不等于就沒有黑社會勢力。一個社會里,只要有些事情是真正的主事者不愿出馬親手干,就會有黑社會的市場。
民主選舉要合法地花掉大量錢財,因為有錢才能組織大型集會、買黃金時段廣告等等,所以對民主花錢多的指責也很常見。但民主政治運轉的成本是不是太高,必須拿它和不民主的政體運行的成本做比較。實際上這幾乎不可能,因為在非民主制下,浪費和貪污的公款,那種拍腦袋決策導致巨大項目失敗造成的損失,等等,絕少會公開,無法全面計算。
最后,有時會在一些地方出現的,民主化過程中的分離主義勢力。這一問題比前幾個問題更棘手,但并非說只要有民主化就一定會出現。1967年印度大選的時候,那位英國記者認為這個國家將四分五裂,因為印度的民族、語言和宗教的多元程度,是全世界最高的。但到現在為止,印度并沒有分裂。倒是它旁邊的巴基斯坦,現在面臨分裂的危險。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民主化并不一定帶來國家的分裂,而專制往往醞釀著分裂的種子。
民主制首先是作為一種理想而出現,但對達到理想的過程,不能看得太美好,不然,當遇到能想象和不能想象的困難,就不會理性地處理,而對困難不能以正面的、建設性的方式來對付,就易半途而廢,甚至走回頭路。越是缺乏民主由基層做起來的社會,就越是難把民主內化成生活方式,因而就越容易出現民主大躍進的幻想。那種以為幾年內可在一個兩千年沒有實行過民主的國家建成民主制的想法,很有害。
民主制和民主化的關系就像造高樓。任何一棟百年基業的高樓,建造過程中都會有噪音灰塵的污染,甚至有工傷事故。建成民主制也一樣,有它的代價和麻煩,要做好物質、技術和心理上的準備。
民主制是人類絕大部分所向往的。在當今世界上,敢于正面否定民主的人很少,但是,那種把民主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當作拒絕實踐民主的人,還相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