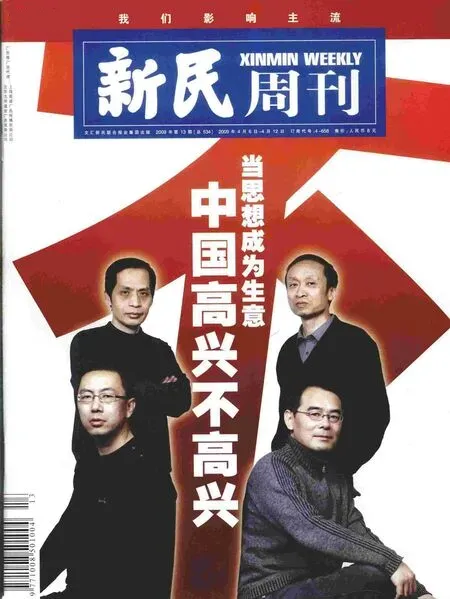商而優則“投”
張 靜

匯源并購被否后不到一小時,身在國外的朱新禮即通過越洋電話向大區經理訓話:“我們要好好干,回報國家。”
這位強勢的掌門人去年甚至放出豪言:“不批,說明國家很重視匯源。估計更多的中國人會猛勁地喝匯源,讓可口可樂買不起了,50億咱也不賣了,100億都不賣,弄不好咱還把他收了呢。”
但就在朱新禮大把燒錢、密集進行大規模的廣告投放,并準備推出一系列新產品迎戰即將到來的銷售旺季時,消息傳來,這一切似乎并不是為重振民族品牌、做百年老店而打拼,只不過是為了增加“再嫁”的砝碼,并購告吹并沒有改變朱新禮的心意。
在采訪中,匯源一直沒有給予記者正面答復。《投資者報》的總編輯何剛認為: “匯源目前的資金壓力很大。不能整體賣給國外企業,并不意外著不能賣給國內企業。如果估值偏低,未必不可以以其他的方式來參股、收購,只是朱新禮沒法高價套現了。”
記者了解到,曾有人士探過娃哈哈老總宗慶后的口風,宗慶后并非不感興趣,但他覺得匯源只值30-40個億。
回顧當初的“賣豬”沖動,朱新禮曾多次通過相熟的媒體向外界吹風,這不過是在尋找企業更大利潤和發展空間的理性思考。當眾多國際國內品牌紛紛進入果汁飲料這片紅海進行搏殺時,他已經開始接連投資布局水果基地,謀求上游這片藍海,完成由果汁制造商向全球供應鏈體系的轉型。更何況,可口可樂還承諾在同等條件下,優先采購匯源的濃縮汁。
他在今年春節前給全體員工的公開信中也明確表示:“為中國農民的億萬噸水果找出路,解決果農賣果難的問題,是匯源的使命。果醬、果泥、果茶、果脯、果脆片、鮮果鮮銷……匯源可以大顯身手,大有作為。”
“壓力說”和“轉型說”,顯然為朱新禮贏得了不少同情分、認同感。1月20日,在看完“2008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揭曉儀式”當晚,一位商界人士曾向記者表示,聽完朱新禮的感言后,開始理解他的選擇。
然而一位熟悉果汁行業的人士認為這些說法在業內“都不著邊”。“事實上,果汁行業的上游高度過剩。可口可樂同等條件下優先采購的說法也是標準不清、模糊曖昧。全中國價格低、質量好的原汁多的是,打入可口可樂原汁供應只能說是一廂情愿。”在他看來,這些不過是為“賣豬”而粉飾的托辭。
在一次與媒體的私下溝通中,朱新禮向在座人士解釋“因為可口可樂是一家偉大的公司”,其中一位接著話茬反戈一擊:“為什么你自己不能把匯源做成一家偉大的公司?”這一下戳中了要害。據說話音剛落,朱新禮神色大變,激動得幾乎失控。
1994年,剛從沂蒙山區走出來,轉戰同樣荒涼的北京順義縣時,他曾經改編了一首歌來鼓勵員工:“咱匯源的人,有什么不一樣,自從離開了家鄉,就想干出個樣……”匯源的發展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朱新禮的個人奮斗史。這位曾經的山東沂源縣外經委副主任,帶領一家瀕臨停產的水果罐頭廠,直至登上了內地果汁飲料的頭把交椅,他對自己一手打造的企業理應傾注了強烈的情感。是什么因素促使他放棄了堅守16年之久的企業家理想,一再要把自己辛辛苦苦養大的兒子賣給別人?
“我覺得他是一種必須的選擇。富豪們的不安全感是肯定的。由于歷史和制度的原因,民營企業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權錢交易這種事都難免,到一定時候不清理掉案底會有很大的隱患。此外,企業做得越大,企業管理和資源整合的能力就要求越高。目前民營企業多是家族制延續發展起來,這種管理結構能夠承載的營業額和規模有一個天花板。對民營企業來說,一般的規模就是10億、50億,發展到100億的時候,再靠家族式管理往上做非常難。要么變身為公眾公司。這意味著他必須進行比較大的股權結構、治理結構的改革,放棄控制權。而在職業經理人、股本結構、董事會的治理各方面都不是很規范的情況下,一旦放棄控制權,企業不僅不能做大,反而可能更慘,這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干脆變現賣掉它。所以我認為他的安全感是一個隱含的因素,而他已經到了發展上限,從企業周期來講,很難再高速成長,賣掉是一種比較理智的選擇。”《投資者報》的總編輯何剛分析道。
朱新禮曾向外訴苦:“我想稍微休息一下,因為做匯源確確實實是辛苦,沒有比它更辛苦了。16年了,創業的時候我一根白發沒有,現在我頭發基本上全白了。16年了,我就沒有休過一個星期天,尤其在春節等節假日。除了1993年我從瑞士考察回來,病倒了,在醫院里躺了20天,我從來就沒有休息過。”
“和君創業”總裁李肅認為:“壓力面前導致的退縮、厭倦心態有沒有?從他向龍永圖、《中國企業家》的社長劉東華大嘆難處,身邊的人使勁替他散播去看,他確實身心憔悴。但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不是一個把全部身心撲在公司里,興致勃勃當樂事,非要干到底的企業家。”
如果說從前是商而優則仕,這幾年商而優則“投”已經成為中國產業界一個醒目的現象。樂百氏創始人何伯權曾被悲情地解讀為中國民族品牌衰敗的又一個犧牲者。但等到沉寂了一段時間他再次出現在公眾面前時,已經悄然在國內構建了一個投資王國。而華宇物流的創始人王振華在把企業賣給荷蘭郵政集團(TNT)后,也完成了從民營企業家到風險投資家的華麗轉身。
李肅認為基金熱潮顯然也對朱新禮造成了不小的刺激。“他肯定會想,如果我拿套現的70億去做投資,賺80倍是什么概念?所以就算別人不逼他賣,他也是有沖動放棄實業,去做一個風險投資家。據我們所知,朱新禮的兒子朱小華對企業經營毫無興趣,堅決不肯繼承父業,在北京成立了一家風險投資公司,去山東投資了一家馬鈴薯企業,實際上已經變成投資家了。”
坊間還傳言,朱新禮已經和中央電視臺《贏在中國》的評委牛根生、吳鷹、馬云、俞敏洪、王利芬等一起,共同出資成立了一個人民幣PE基金。
“宗慶后也遇到過同樣的誘惑。”李肅透露:“達能一開始出40億,他不賣。結果人家到處告他的狀,向他施加壓力。宗慶后就打回去一張牌:‘我要按15倍市盈率賣你。計算下來,宗慶后賣掉控股權,同樣也可以套現70多個億。宗慶后想我值了,有這70多個億,就可以去投資一系列項目。他當時面對的資金誘惑,其實和朱新禮差不多。但是他回去和團隊一商量,遭到全體反對,他自己也越來越感覺不該賣,于是又反悔了。說到底,還是看企業家本人是不是有這個毅力,能夠堅定不移地干到底。”
“中國企業家實際上經歷了三代,80年代是政治型企業家,90年代是機會型企業家,現在則是新一代戰略型企業家。對于機會型企業家來說,他們從一開始就不認為可以做到基業長青,大部分至今還停留在草根時代,并沒有完成向戰略型企業家的轉折。所以對他們而言,把‘豬養大了賣掉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人家出了高價,打破腦袋也要賣。華宇物流曾經做到了汽車物流第一塊招牌,當時如果跟中外運重組真的可以成為領袖企業。沒想到談著談著TNT給了13億人民幣,于是不顧一切就賣了。過了一年半,王振華在上海萬豪酒店碰見我,這回輪到他捶胸頓足,說賣虧了,再晚賣一年就是26億。我說,如果當初按我的思維做成中國最著名的大型物流公司,融資上市,你公司的市值不是26億,而是150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