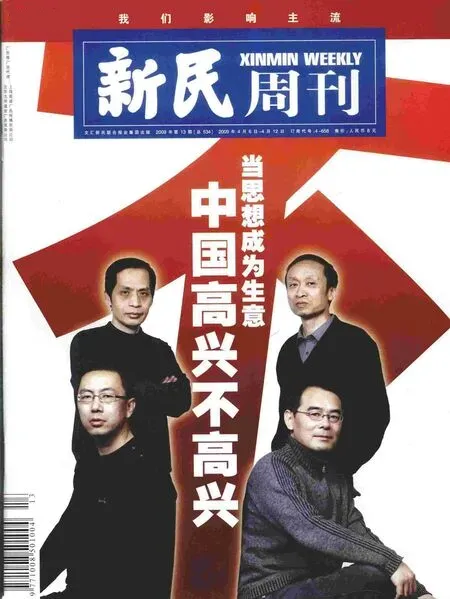懸崖邊上的評級機構
馬紅漫

金融危機還在繼續,反思和修正就已經開始,首當其沖的正是金融危機的“幫兇”——信用評級機構。央行金融研究所日前發表題為《對改革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的幾點認識》的文章,文中建議金融機構不能把風險評估職能外包給評級機構;監管者應鼓勵金融機構提高內部評級能力,減小對外部評級的依賴;要求金融機構對外部評級的依賴度和使用率不超過業務量的50%。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能夠迅速蔓延擴散,信用評級機構的推波助瀾作用顯而易見。次貸危機從策源伊始,評級公司就扮演了一個重要的不光彩的角色。當初大量被標以AAA和AA級的高信用等級債券產品,事后證明被嚴重高估。看似毫無風險的投資品,瞬間倒債崩盤,數萬億美元的資產隨之變為廢紙。毫不客氣地講,正是由于評級機構和投資銀行的共謀,才使得大量的投資者被引入迷途。如果不是因為對標普、穆迪等評級公司的過度信賴,次貸危機或許根本就不會發生,至少其影響力和破壞力不會如此巨大。
評級機構成熟于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彼時大量企業破產和銀行壞賬爆發,反而成就了評級機構的權威地位。但是歷經近百年的演變,曾經的金融新銳,如今已是老態龍鐘。競爭機制的消亡和監管懲戒機制的缺失,讓評級行業不再堪當甄別風險的重任。
百年歷練,大浪淘沙,最終存活下來的一線評級公司只有標普、穆迪和惠譽三家。當下的國際評級行業已經處于自然壟斷之中,除此三家之外,再無新競爭對手的空間。更為重要的是,較之于其他金融中介行業,評級機構擁有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尚方寶劍”,即“只有權力但無約束”。基于歷史沿襲的慣例,沒有任何監管機構擁有懲戒評級機構的權力。2006年美國頒布的《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就明確規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無權干涉評級公司。用評級業內人士的話說,評級機構只“負道義上的義務,而無法律上的責任”。但對于全球投資者而言,直至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后才恍然大悟,原來那些聲名卓著的國際評級機構,根本不會為他們那些低級而愚蠢的評級結論承擔任何責任。
“內部無競爭、外部無監管”,在市場經濟體制較為完善的當下,居然有如此滋潤的金融行業存在,這的確令人匪夷所思。
盡管國內本身的評級機構因為市場能力所限,并未涉及到次貸危機之中,但是海外的“城門失火”最終還是殃及了國內“池魚”。央行金融研究所的報告已經在事實上否定了外部評級存在的意義,封殺了國內評級行業的發展空間。試想,如果金融機構除了看外部評級報告外,還必須自行調查并撰寫內部評級報告,并最終依照內部評級報告行事,那投資者還要外部評級機構報告作何用處?當國內評級機構報告被扔進垃圾桶,這標志著全行業都陷入到了信任危機之中。
生存還是死亡,對于評級機構已經成為一個現實問題。維系全行業的生存,需要的是刮骨療傷般的深刻改革。較之于國外同行,國內評級行業更是在襁褓下滋潤生存,行業發展完全沒有經歷過慘烈的市場競爭。目前國內評級機構的資質源于相關部門1997年的一紙發文,而彼時所認定的9家評級公司就再未做出過調整;此外,行政指令性的貸款企業評級盡管備受爭議,但卻足以保證國內評級機構的生存無憂。盡管已經享受著優越的既得利益,但仍有業內人士呼吁繼續“政府推動模式”,反對“市場競爭模式”,試圖把海外的準入限制在國內復制。這樣的思維可謂短視至極。
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評級行業都需要徹底打破壟斷,調控部門需要鼓勵新興競爭者的出現,只有讓壟斷者擁有危機感,淘汰既得利益者,才能夠讓行業重新煥發青春。此外,不負任何責任的行業慣例必須被摒棄,其要害在于要建立起評級機構風險保證金制度,以評級機構事前的資產抵押作為對評級結論失靈的懲戒。總之,次貸危機把評級行業推到懸崖邊上,唯有強化內部競爭和外部監管,才能夠讓評級業生存下去,否則就只能是全行業的集體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