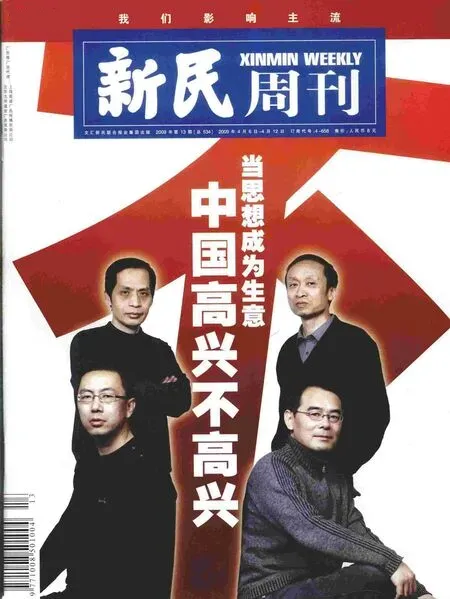文化遺產也有假
沈嘉祿

人類文化遺存之所以珍貴,首先在于它以標本的形式,忠實記錄了人類從愚昧走向文明的過程;其次是它的脆弱,在工業化的進程中,它的原生態與生存環境面臨著難以抗拒的風化腐蝕。
上周日,方教授來寒舍品茗聊天。方教授是費孝通的女弟子,研究藝術與人類行為的關系。寒窗數年,出了好幾本專著,費老生前對她的成果很肯定。但一個女人,餐風宿露地做田野考察有諸多不便,比如有時得與原住民同住,一個大炕睡七八人,男女混雜。農民純樸得很,拉屎撒尿不避人,但對大城市來的知識分子來說,心理障礙巨大。有時她就只好抓先生的“壯丁”。前不久她在陜西一個鄉村考察,先生就被她抓去了,協助拍攝錄像,兼做口述實錄。
這個鄉村的鄉土文化遺存豐厚龐雜,這幾年在政府和有關方面的努力下,整理出不少內容,比如面花(用饃饃做成動植物與娃娃的造型,被稱為小麥的雕塑),還有剪紙、年畫、信天游、民間故事等,連當地農民信奉的多神教,也在新修的廟里被供養起來。外人難以識別的山神、風神、雨神、牛神、羊神、關老爺、灶王爺等,擠在一起享受香火。今年除夕夜,吃過水餃,放過鞭炮,他們還跟隨一個腰鼓隊串村走鎮地演出。一路上同吃同住,腰鼓隊在某個村子扎下演出時,他們夫婦倆是最最忠實的觀眾,鼓掌比誰都起勁。
方教授發現,這里的文化呈現出罕見的多樣性與雜交狀態,在一個交通不發達、人口流動也不頻繁的冷僻角落,這是怎么形成的呢?極大的好奇心讓她多呆了幾天。
半個月后,考察結束了,一隊農民扭著秧鼓、打著腰鼓送他們夫婦倆出村。最后握手告別的那一刻,一個憨厚的老農民將方教授拉到路邊,滿臉愧疚地說:“方教授啊,實話告訴你吧,你看到的花花世界都是假的。”
方教授像當胸挨了一拳,身子也有點搖晃了。原來這個村子被“發掘”、“保存”的民俗文化都不是土生土長的,是前幾年由一個大學教授帶了一個考察小組,將周邊地區的一些民俗搜羅過來,手把手地教給當地農民的。經過一陣鼓搗,“湮沒”多年的“本土文化”就這樣恢復了。接下來,村里的“文化遺存”上了報,上了電視,城市里的各色人等就紛至沓來旅游什么的,把當地的知名度炒上去了,每年光旅游收入就有好幾百萬。
方教授氣憤地對我說:“這是作偽、欺詐,我在那里所做的一切記錄和研究都白費勁了,我……還寫了文章,幸虧沒有發表,否則就成幫兇了呢。”
其實,從農民的姓氏、語言等因素考察,這個村子很古老,但延續了幾千年之久的民俗,在十年動亂時已經被破壞得蕩然無存。隨著最后一個老輩子原住民去世后,集體記憶也就喪失殆盡。現在的所謂挖掘、恢復其實都是一個美麗的謊言。但是農民富了,蓋了樓,養了豬,娶了媳婦,抱了孫子,這似乎是壓倒一切的成績,是民俗文化整理結出的碩果,是最講政治的“和諧”。一個知識分子如果為了證明自己的學術良心和文化道德,應該站出來戳穿謊言。但是,“我也不愿意農民再回去過那種貧困的生活啊。”方教授說。
“我無法選擇。但是若干年后,子孫后代知道有一個研究人類學的人在這里與農民同吃同行同住過,等于承認了這種‘文化遺存,他們會怎么說呢?”
我說了一些無用的話來安慰她,還拿了一份報紙給她看:也在陜西,鳳縣政府為了發展旅游業,花了6個多億打造月光城。入夜后,這里星光燦爛,外來者可仰望星空,唱一唱《今夜無人入眠》,但到了白天,孔雀屁股就露出來了——山上安裝了3000多盞太陽燈,晚上將電閘一推,月亮和星星就露出了笑臉。這還不算,為了弘揚“羌文化”,打造“羌族故里”,地方政府還動員當地祖祖輩輩在此繁衍生息的漢族農民改成羌族,并以中央的民族優惠政策作誘餌。但農民不干,說那是數典忘祖的事,死了也不改。
方教授一把搶過報紙,掃了一眼后說:“再這樣下去,我們文化人就多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