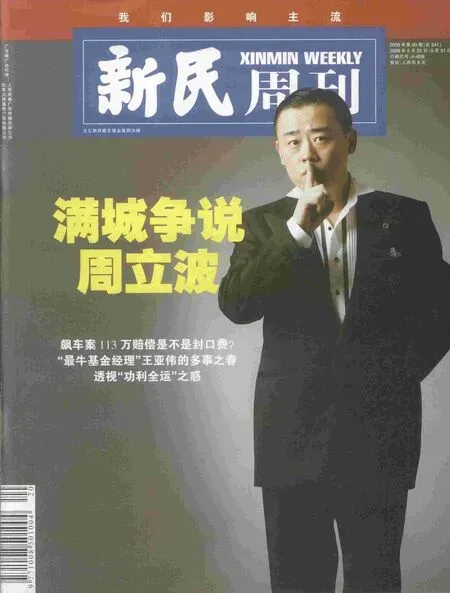U型的底會很長
金 姬

“迷失的十年”
會在世界范圍內重演嗎?
讓我們先正視一下目前的大環境。全球經濟并不令人滿意,各國都難以幸免。我當年看出了房地產業有問題,泡沫破裂之后會引發經濟萎縮,但是我沒想到它會引發和金融危機且波及全球。
這場全球金融危機對全球貿易造成很大的破壞。決策者們對此危機的反應比之前各大蕭條時期要主動積極,因為我們有前人的經驗教訓。利率快速下調,美聯儲大膽出臺了一些確保信貸流動性的措施,政府沒有重犯30年代的錯誤而降低開支或增加稅收。中美政府都采取了積極措施。不管怎樣,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不會在這次危機中重現。
全球經濟的自由落體狀態已經終止,但還沒有出現恢復的跡象。通常主要經濟體中,由于利率下調,錢很容易獲得,大家開始增加支出。因此,在這一輪衰退中,所有經濟體都已大幅下調利率,如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和中國央行。值得注意的是,美聯儲直接控制下的短期利率,實際已經降到了百分之零點零幾,相當于零,不能再進一步降了。這在美國歷史上只出現過一次,那就是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這意味著用利率來調節的常規貨幣政策已經沒有太多空間。
美聯儲現任主席伯南克是普林斯頓經濟學系的教授,他和其他美聯儲官員采用常規可用方法來應對現在的危機還遠遠不夠,可能使危機終止,但不能使經濟復蘇。我擔心的不是世界經濟出現第二次大蕭條,而是可能像當初日本,出現“迷失的十年” 那樣的情況。日本經濟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的高速發展,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90年代初卻出現經濟危機,股價崩潰,地價下跌。從2003年開始,因大量出口帶來的貿易盈余,使日本實現了經濟復蘇。 現在我們面臨的情況像1990年代的日本,大量泡沫已經破滅。
美國和中國采用的財政擴張政策有所幫助,但不能讓經濟復蘇。奧巴馬希望創造350萬個就業機會,但這不能解決問題。美國可能還會出臺一些新的政策,但很多國家非常謹慎,因為他們非常擔心債務負擔。我們沒有一個全球性的財政刺激政策來使經濟復蘇。有一些國家的央行積極投入了擴張性的政策,但他們沒有降息的空間。當然,他們會采用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購買一些私營機構的債券。
我希望此次金融危機不要延續10年這么長。如果我們足夠幸運和聰明,可能全球經濟復蘇不需要10年,但我們的經濟弱勢要保持很長時間。全球經濟很可能是U形復蘇,但是U形的底會很長。
中國經濟三大問題
在金融危機下,我關注中國經濟,主要是三個方面:中國的貿易盈余問題;中國的貿易結構以及要維護中國開放市場所面臨的挑戰;在全球資源和環境壓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中國該如何應對?
在金融危機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里國際收支不平衡現象非常嚴重。美國是很大的赤字國。與美國相對應的是貿易順差國或曰盈余國,一個是新興的工業經濟體如亞洲的臺灣、韓國、香港和新加坡。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后這些地區開始有了貿易盈余。其次是中東地區的石油出口國。最大的一塊盈余來自于越南等發展中國家,而中國是龍頭老大,國際貿易中的經常項目盈余占到GDP的10%。
中國的儲蓄率很高,中國的制造業帶來了很多盈余,而中國的匯率政策讓人民幣盯住美元。2002年以來,為了保持人民幣相對美元的穩定,中國購買了大量外匯(美元)。為了避免美元流入國內引起通脹,中國政府不得不凍結美元,并把資本出口到國外。很長一段時間,這是皆大歡喜的局面,美國有更便宜廉價的資金,可以用這些錢來發展樓市,美國人借錢消費,而中國有了一個龐大的出口市場,可以發展出口驅動型經濟。2005年我就撰文指出,說美國的經濟已經成為人們靠賣房子過活的社會,他們相互買房子的錢都是從中國借來的,這絕不是一個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
我們再也不可能回到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美國當時瘋狂借錢,家庭債務達到GDP的100%,這只在大蕭條之前有過一次。現在,美國再也不可能借這么多錢,消費者又開始存錢,儲蓄率從0攀升到4%,我覺得它會繼續增長到8%左右。在美國,消費的需求會放緩。
這樣的世界中,標準的經濟學似乎已經失效。我們總說自由貿易有利于所有人,貿易盈余國家其實是幫助其他的國家,但如今這個失業率攀升的世界,這些說法都不對了。現在美國的政策是:如果你有很多貿易盈余,會使其他國家非常生氣,這是重商主義,過去重商主義是個好事,但現在不再是如此了。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將來中國的盈余肯定會讓其他國家不能容忍。中國不能再靠貿易盈余維系經濟增長了。
中國經濟的第二個問題更溫和一些,但仍然很嚴重。
上世紀80年代,我和很多人做了一個研究,研究對象是有關國家之間的同行業貿易。比如說汽車行業的貿易,即使現在,高收入的國家相互之間出口汽車,因為汽車各不相同,各國可以專長生產不同類別的汽車。這種貿易是發達國家中占貿易很大一塊。
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越來越大,很多雖然是同類產品,比如日本和中國出口都是計算機產品,但賣的不一樣,日本賣很多高精尖產品,中國會組裝以后再賣出去。事實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會遇到更大的政治阻力。由于中國和其他新興體的崛起,這種新類型的貿易其實是比較優勢的貿易。
在美國的進口中,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量在2004年第一次超過了來自發達國家的進口,主要是中國和墨西哥的出口商品占了很大份額。有一點需要強調,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相當,但如果美國從墨西哥進口商品,墨西哥制造工人工資只占到美國工人的11%;如果從中國進口制造品,中國制造業工人的工資只占到美國工人工資的4%。這會帶來很大的專業化分工和重組以及政治壓力。
我擔心的是,我們共享一個資源有限的星球。新興市場的飛速發展,特別是中國的發展對地球的影響很明顯。一年前還沒有很多人探討金融危機,當時談油價、糧價大幅攀升,這是由于新的經濟體,包括中國的需求大漲。21世紀初,油價20美元一桶,現在金融危機了,油價還是58美元一桶,這是新興工業國家對資源需求帶來的影響。
除此之外,還有對環境的擔憂。長遠來看,環境政策將主宰一切政策,環境問題比金融系統、國際貿易等都要關鍵。可能明年還看不到這種趨勢,但是10年、15年以后,特別是伴隨氣候的變化,它將會成為一切社會活動和經濟的中心。
中國2006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來源。當美國19世紀發展經濟時,不用擔心全球變暖。現在中國發展卻面臨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采取一些措施,主要是發達國家,希望美國在明年立法限制氣體排放,中國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可以獲得一些補償,希望全球就這方面達成某種共識。
中美之間,今后四五年中會就這個問題進行非常激烈的討論。美國不會輕易像過去那樣讓步,但是還會讓步。我的余生中,這些環境政策會進一步地被討論、談判。無論二氧化碳是哪個地方排放的,不采取措施的話,整個地球都會受到溫室氣體的影響。這個不光是中美的問題。盡管從短期來說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但長遠來說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相信最終會有一個美好的星球。(本文整理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5月12日在上海交大的演講。未經作者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