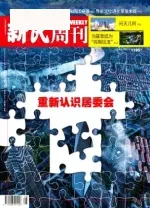NGO曲線破圍
卞 寧

原本應該是綠色事業的NGO在中國尚處在灰色地帶,總有一層說不清道不明的網罩住了NGO的發展,艱難生存的中國草根NGO只能嘗試曲線破圍。
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幕當天,正是3月5日“雷鋒紀念日”。全國政協委員劉江龍就提交了提案,建議為“雷鋒精神”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除此之外,“兩會”期間,關于志愿者和NGO(非政府組織)的聲音寥寥,觀點大爆發的“兩會”上,NGO仍然是個被冷落的話題。
NGO,“難搞哦”。
正如樂美真委員在《建立志愿者激勵機制 緩解大學生就業問題》的發言材料的最后提到的——“改善NGO發展的法制環境,發揮NGO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相關法律與政策缺失所帶來的民間組織注冊難已持續多年,這不僅造成許多民間NGO法律上的尷尬,也使得它們在發揮作用上受到局限。
原本應該是綠色事業的NGO在中國尚處在灰色地帶,總有一層說不清道不明的網罩住了NGO的發展,艱難生存的中國草根NGO只能嘗試曲線破圍。
去年的汶川大地震給了NGO一個操練場和正面表現的舞臺。種種跡象表明,在法律地位沒有解決之前,草根NGO可能利用種種變通,在政企間贏得新的生存空間。而相關主管部門的態度,亦借由大地震的特殊情境有所松動。
在中國民眾心目中,NGO和NPO(非營利組織)就是專門“學雷鋒”的。然而,草根NGO英雄的生存之路是一段長征,遠比3月5日上街給人剃個頭復雜得多。
其實不差錢?
“錢,絕不是最重要的問題。”說出徐永光這句話需要相當大的氣魄和地位。此時,淡黃色的落日余暉正好可以灑進徐永光的辦公室,窗口外不遠,是北京東三環的車流。千里之外的成都,何磊未必像徐永光這么想,對他來說,錢永遠是緊張的。
徐永光是何磊的“財神”。
徐永光已經60歲,面容白凈富態,這個前團中央組織部長和希望工程的原操盤手現在專職為南都公益基金會工作。南都公益基金會是一個非公募基金會,原始基金1億元人民幣全部來自其冠名的民營企業。這個基金會專注于支持民間公益,像何磊這樣的草根NGO可以向南都基金申請資助。何磊身材瘦高,他是一個叫野草文化的環保NGO的全職負責人。
“南都基金還沒給過我們資助,不過,徐老師已經答應過給我們錢了。”即使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野草,也得為錢愁。何磊也覺得自己的NGO不該為籌錢所累,應該專注于環保理念的宣傳,但是沒有錢的話,談什么宣傳環保。
現實是,沒有錢。
“你說像徐老師這樣全力支持草根NGO的基金會國內有幾個?南都基金又能有多少錢呢?能支持幾個NGO?”何磊說,2008年,野草的經費60%來自基金會贊助,另外40%是通過策劃項目賺來的。小小的野草也有10個專職人員,他們在成都386個社區中的140個建立了環保輔導站。
要成為野草團隊的一員絕對不能有房貸,“有房貸的我們也不要,因為房奴的生活不自由,我們向往自由的生活”。事實上,在野草工作不可能還上房貸。2006年一年,野草所有人拿的是“承諾工資”,一個承諾的數字,但一分錢也不發。2007年,發下了50%的象征性工資。2008年,野草實現了全額發工資,“算成都市民工資的中下等水平”。何磊說,即使這樣,加入野草的成員從來沒有人半途退出過,他們都在靠過去工作的積蓄生活。何磊自己曾經是一名記者,2004年初創辦野草,當年年底就從最后供職的媒體——一本叫《世界環境》的雜志辭職專職干NGO。

何磊希望在2009年能把來自基金會的資金比例再降一降,原因很簡單,這個募資渠道不靠譜。為此,何磊的團隊決定賣菜賺錢。他們聯系了菜農,又組織了市民團購,把鄉下的綠色蔬菜賣到城里去。
何磊對賣菜生意抱有很大希望,如果不能先解決生計,他的NGO就不能實現自己的愿景。但何磊也說:“如果我在美國,絕不可能去賣菜賺錢,肯定專心宣傳環保理念。”
何磊向往的“基金會專心散財,NGO專心花錢辦事”的模式在是很多西方國家成型的公益事業產業鏈,包括香港地區也是這樣。
在徐永光看來,這樣一條產業鏈在我國還差很多環節。像中華慈善總會和紅十字會這樣的“體制內公募基金會”募集了90%以上的捐款,卻沒有能力把善款分撥給NGO去使用。體制外的非公募基金會則少之又少。另外,中國NGO自身的能力也需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從官到民是一個方向。”徐永光說,我國有影響力的公募基金會都有官方背景。官辦慈善的運作方式更接近政府部門,很多從業人員是從政府出來的,有的還是退休干部,缺乏專業人才。而非官辦的基金會不向公眾勸募,有比較固定的捐贈人,實行企業化治理,項目收益、成本控制和公開透明是其長處。
不過,在業內人士看來,非公募基金會近年起步已經是我國公益事業的突破,其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松動,2004年3月,新的《基金會管理條例》頒布,200萬元人民幣成為非公募基金會的最低門檻。
回到徐永光“不差錢”的論斷,他認為,至少有三個問題比錢更重要,這些問題解決了,錢就不會成為麻煩。
其一是登記。我國民間組織管理采取雙重管理體制,一個民間組織先要獲得政府業務主管部門的同意,然后再到民政部門去登記。難就難在民間組織找不到政府業務主管部門“擔保”。原因很簡單:誰接收誰就得承擔責任。
其二是缺人。慈善機構缺乏職業化的人力資源儲備,需要培養這個行業的專業人才并用良好的薪水吸引優秀人才加入這個行業,這樣才能提高慈善的效率。
其三是NGO自身治理。NGO的普遍問題是缺乏獨立性,民間基金會大都是企業的“皮包基金會”,大都沒有建立起以理事會為核心的治理結構。NGO的理事會和企業的董事會類似,“官辦慈善機構中,理事會是擺設,政府是老大,執行層強勢”。在官辦和民間基金會都做過負責人的徐永光說。“資源其實不是問題。”徐永光又說了一遍。
企業—NGO—政府
華威廉是個可愛的美國老頭,從名字就能看出來他有意大利血統——威廉姆斯·華倫天奴。他供職于德國公司拜耳,擔任拜耳大中華區企業社會責任副總裁。不過,有的時候,華威廉比中國人更像中國人。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能說一口流利漢語,并且學會了中國式的世故卻仍保留著中國人罕見的熱情。

在四川省江油市京江一社區里,華威廉熟人遍地,有打不完招呼,好像所有的居民都認識他。迎面又遇上社區85歲的大爺放風箏,他緊走幾步,握住大爺的手,兩人互稱老朋友。“他是個老花花公子。”華威廉把大爺介紹給身邊同行的人。
京江一社區是個板房社區。
去年7月,華威廉第一次來到京江一社區可沒這么受歡迎。當時,拜耳想在災區進行志愿者服務,華威廉在團中央派駐江油的團市委副書記曾松亭的陪同下剛進社區就被人舉報了。那個階段,外國人在地震災區還是敏感人群,不那么受歡迎。在曾松亭的擔保和全程陪同下,華威廉還是有驚無險地完成了5天的調研。
后來,拜耳“落地”江油又一度出現困難,曾松亭為此跑了兩次北京,又給團四川省委打了報告。最終,去年10月,拜耳的志愿者出現在江油京江一社區。
到現在,拜耳的志愿者仍然在京江一社區服務,一批接一批,總共來過90個志愿者,服務超過17000多小時。他們為社區受災家庭提供幫助,探訪孤寡老人;在當地學校開設生動、有趣的英語趣味課堂;建立社區圖書館,每天開放6小時;努力改善社區生活、文化環境。

隱藏在全球500強企業和政府之間的,是國內一家知名NGO——茅于軾和湯敏創立的北京富平學校。
政府—NGO—企業,這形成了一個鐵三角。拜耳出錢出員工志愿者,實現企業社會責任并且加強了團隊凝聚力;北京富平學校全權負責項目運作,并派出志愿者輔導員,甚至拜耳志愿者在四川的必要開銷都是由富平學校負責;當地團組織積極倡導,政府權力支持。形成了三贏的局面。
“政府牽頭—NGO協調—企業參與,這是一個嶄新的志愿者服務模式。”已經回到團中央志愿者工作部工作的曾松亭博士告訴記者。
長期以來,與政府的溝通協調能力不佳被認為是草根NGO的一個短腿。“如果沒有當地政府的支持,志愿者根本進不了社區。”北京富平學校的項目官員王忠平博士說。
“實踐證明,NGO組織在抗震救災和災后重建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團委應該對NGO的工作加以認可,并鼓勵NGO組織開展更多的有效工作。作為認可和鼓勵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部門或群團組織放下架子,主動去爭取與NGO組織的合作,更好地發揮NGO組織的作用。”曾松亭表達了對NGO的高度認可。
對于政府與NGO的關系,曾松亭仍然出言審慎:“政府對NGO不要提管理,只能引導、鼓勵、支持、服務,其實這不是一種管理形式嗎?”清華大學NGO研究副所長賈西津認為,NGO和政府之間最恰當的關系就是伙伴。對于中國政府而言,構建這這種關系需要一個轉型。
拜耳—富平的江油案例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中共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求是》刊登了文章表揚此項目。團中央志愿者工作部部長徐曉在3月5日當天到江油參觀了這個項目。
企業把社會公益項目交給NGO操刀為不少NGO提供生存空間,NGO可以借此獲得生存的資金。另一方面,企業對于社會責任項目的執行和監督捉襟見肘,交給專業NGO打理可以更放心。這種“公益外包”方式或成NGO在注冊問題無法得到解決的情況下曲線破圍的方式之一。
觀察人士認為,在NGO與政府的合作上,江油項目有可能不會是孤例,情況會越來越好。
套上時尚的殼
“地震讓四川的NGO發展比全國快了5—10年。”徐永光如此判斷的政策依據是《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條例》,條例明確指出:在災后重建中應堅持“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的原則。在此指導原則下,NGO可以理直氣壯地去做事情。而全國最優秀的NGO組織紛紛來到四川,最終將留下本土化、專業化、長期化的NGO隊伍。四川NGO發展具有獨特的環境優勢。
在徐永光看來,政府資源是決定NGO能力的重要因素,很多NGO不愿意或者沒有能力與政府合作。草根NGO的負責人多是理想主義者,自命清高,帶著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徐永光認為,就連NGO最不愿意面對的登記問題,都并非沒有空間。許多NGO辦不下來民辦非企業單位的執照,只好辦了工商執照,這就要面對5.5%高額營業稅。“連民營老板都能和政府很好地進行公私合作,NGO為什么不行?NGO為公眾利益工作,和政府是公—公關系。”
當然,有的NGO有自己的避稅土政策,比如同時注冊工商執照和社團,進賬時以社團的名義。“有的NGO向我們申請資金時,直接把營業稅歸入成本,我們也是認可的。”徐永光說。
安豬對于草根NGO的批判氣質很有體會,他不是很適應NGO圈子中“受迫害幻想狂”的心態。“我們看到不平等,因此有了自己的理想,但又很容易把自己的理想變成綁架別人的工具,要求別人也像自己一樣“思考”。而在受到過一些不公正的對待后,我們又很容易把每個人都看作敵人,把每句話都看作敵意,于是,路越走越窄,到最后變成了小圈子的孤芳自賞,卻還在抱怨世界為什么不理解我們。”安豬在自己的博客里說。
安豬是公益旅游組織“多背一公斤”的CEO。“多背一公斤”幾乎是中國最另類的一個NGO,被稱為“時尚公益”,通過網絡傳播。它建議旅行者在旅途中探訪鄉村學校,傳遞愛心和知識,同時為自己的旅程增添意義。出行時多背一公斤,為鄉村學校帶去需要的物資。
這種方式很“人肉”。聽到記者這么總結,安豬哈哈大笑,當初他創辦“多背一公斤”時確實受到了維基百科群體協作模式的啟發。
“人肉”不僅可以用來人肉搜索,還能用來編百科全書,也能用來做公益。
“多背一公斤”的全職團隊有5個人,分別在四個不同城市soho。安豬也沒有為“多背一公斤”申請民非執照,“知道那個難,不浪費精力了”,直接辦了工商執照,“我覺得我能承受營業稅”。安豬甚至不保證要做非營利的組織,可持續發展才是最重要的。他很有野心也很有想法,正如無數個默默生長的中國草根N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