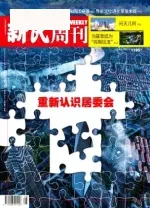一個勇敢的潛行者
沈嘉祿

初春時節,又見夏畫。年過七旬的老夏坐在藤椅上,神清氣爽,膚色白里透紅,一頭銀發在淡薄的冬陽下閃著光華,一對又長又翹的壽眉如趙子龍頭盔上的翎子一樣隨著說話的節奏微抖著,威風凜凜。窗外,數枝白玉蘭默默綻放。
去年,所有媒體都在大張旗鼓地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但是沒有一篇文章提及《青年一代》的創刊。聽說有關方面正在籌建一個出版博物館,選址上海,籌建人員找到夏畫,希望他能為《青年一代》留下一點檔案。
這本雜志很重要嗎?這要看你從哪個角度看問題了。當下出版業大繁榮,青年讀物多如牛毛,但年齡從三十歲到五十歲的中國人,誰沒有看過這本雜志?
1979年,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開始,上海出版局聞雞起舞,由夏畫創辦《青年一代》。這個時候,渡盡劫波的青年人對生活的意義、生活的目的都有些迷茫,國門洞開后,他們在來自西方國家的信息前難免驚愕,很需要有一本雜志表達他們的內心訴求,特別是給予明確的引導。當然,他們對虛假的說教已經厭惡透了,希望真誠地交流與溝通。如果向他們分析一些活生生的案例,特別是青年人自己身上發生的故事,就容易接受。我想,當年《青年一代》策劃選題時,可能也出于這樣的考慮,或許還要想得更深更遠。
《青年一代》創刊很成功,一炮打響,產生全國性影響,這里的故事太多,不及細說。每期出版購者如云,編輯部當天就會電話打爆:“這個故事是真的嗎?”“故事里的人物現在生活得如何?”
國外一些媒體也經常轉載《青年一代》的文章。還有外國的電視臺專程到上海采訪夏畫。外國記者與讀者從這本雜志上看到中國發生的變化,特別是青年人的思想狀態和生活狀態。
《青年一代》最風光時,發行量達到500萬份。這在中國出版界無疑是一個不可復制的神話。
但是,當時《青年一代》被外國媒體關注,夏畫就會有壓力。有些人還是持極左思維:西方國家為什么對你感興趣?是不是你暴露了什么,或者販賣了什么?果然,有人發話出來:《青年一代》發到500萬份了,這本雜志要注意。
有一次,出版系統某領導找夏畫談心——當時沒有“喝咖啡”一說,領導拿了一份材料很嚴肅地指出:這七篇文章有問題。夏畫當即頂了回去:這七篇都是好文章。登出來的都是好文章,不夠刊登標準的文章是不會登出來的。
還有一次,《青年一代》刊登的一篇“讀者來信”惹了大禍。這篇幾百字的“來信”說的是北京某高官因為有外遇,在家里就虐待妻女。最后好些老干部看不過去了,向《青年一代》寫了信,編輯部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認為所述屬實,就刊登出來了。誰料這個官員是通天的,一番運作后,有關部門領導責成夏畫寫檢查。當時團中央一位主要負責人看了文章說,有根有據,沒有問題,你要夏畫寫檢查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有關部門領導只得請夏畫寫一份簡單的情況說明,而領導自己倒寫了一份檢查應付上峰。
有些事情若是放在今天,情況就不一樣了。今天的中國,畢竟網絡資訊發達,法制意識強化,群眾覺悟提高,紀委監管也加強了,君不見林嘉祥,狂言既出,千夫所指,最終成了一只落湯雞嗎?所以說,改革開放三十年,是思想解放、開啟民智、健全法制的三十年。在這個過程中,《青年一代》的推動作用不容忽視。
夏畫在《青年一代》主政十年有余,建立了青年讀物全新的辦刊理念,營造了一本雜志的企業文化,帶出了一批編輯高手,團結和培養了一批青年作者,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這本雜志深刻影響了至少兩代讀者。
行文至此,我眼前出現了一個潛行者的形象,一個勇于向前的潛行者。
“勇敢”兩字好理解,“潛行”兩字,我認為夏畫辦刊物,就是處于這種忍辱負重的狀態,潛行的壓力和阻力肯定比浮在水面上大,但他義無反顧地前行,凝神屏息,默默用力,不起浪花,也不在乎別人怎么評價他的泳姿。最后,他一躍而出水了,抖去一身水珠,夕陽照在他的頭上,銀光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