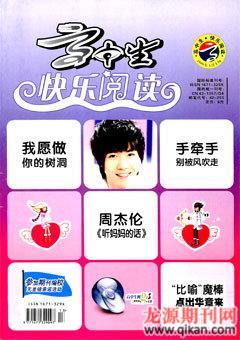張曉:謙卑的心里挺立著崇高
狄多華 張 鵬
要做含淚奔跑的人
時間回溯到張曉參加高考的第一天。那一天,等兒子張曉為自己穿好衣服,洗完臉,把自個兒挪到床邊坐好,母親曹雪紅目送兒子離開,開始“胡思亂想”。
兒子的考試結果怎么樣,尚不知曉,可一旦兒子考上了大學,“那可怎么辦?我不能再讓兒子背著我去上學,我不能再成為兒子的累贅”。
曹雪紅越想越自責:我沒有盡到一點兒母親的責任,相反拖累了孩子十幾年。兒子的童年被我剝奪了,少年時代也被我剝奪了,我不能再剝奪兒子的青年時代!
考場內的張曉無從知曉母親的心思,但他對母親的惦記卻一時一刻也沒有放下,考試當天中午,他還是沒有聽從母親的囑咐,滿頭大汗地跑了回來,為母親接尿、遞水。
張曉不說,但有書信為證:“因家中發生不幸,我親愛的爸爸離開了我們。那是1993年的事了,那時我才4歲。不到一個月時間,我媽媽由于悲痛病倒了,后來命保住了,可留下了嚴重的‘類風濕性關節炎。這可惡的病魔奪走了媽媽的自由……”這是10歲的張曉第一次寫信向別人求助,也是最后一次。
爸爸因車禍去世后,母親生病住院,雖然千方百計保住了性命,但從此以后生活無法自理。
此時,家中的積蓄已全部花完,還欠下了外債。不得已,外公外婆將張曉母子從內蒙古額濟納旗接回了甘肅平涼老家,借住在親戚家。可時間不長,他們就成了親戚眼中的包袱。一輛破舊的手推車將母子倆拉出了親戚家,眼看要流落街頭,好心的大媽騰出自家不足3平方米的看守菜地的小草房,供母子倆棲身。
兩年光景,他們又被請出搖搖欲墜的草房,租住在另一家四處透風、不足5平方米的伙房內。6年后再次搬家,擠進略微寬敞一點的磚房。房東看他們可憐,將房租由50元降到20元。這樣,他們還是承受不起,在社區的幫助下,又是兩次搬家。
筆記本上,張曉寫下了激勵自己的話語:“真正的強者,不是流淚的人,而是含淚奔跑的人。”
十幾年來,張曉一路含淚奔跑的背后,是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付出。
常年臥床的母親,剛開始尚能挪動,攙扶著可以自己上廁所。隨后病情越來越重,她一度大小便失禁。張曉每天都要幫母親穿衣、洗臉、刷牙、梳頭,還要洗腳、洗澡、剪指甲。另外,生火、做飯、洗衣服,這些也都是他的事。
我只是做了應該做的
“久病床前無孝子。”常有人驚嘆張曉的十幾年是如何堅持下來的。
張曉卻說:“這些都是生活中的常事、瑣事。我沒有什么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只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雖然生活艱辛,但張曉很少哭。“眼淚能侵蝕人的脊梁,讓你直不起腰,”張曉總把腰板挺得直直的。
不愿過多提起過去,但對于最為艱難的日子,張曉刻骨銘心。那是2000年以前,母子倆靠拾別人的菜葉子糊口。沒有面吃,就吃拾來的菜,沒鹽、沒醋,就用白水煮菜。吃的時間長了,胃根本受不了,娘兒倆都口吐綠水。
“我只要有一口飯吃,就不會讓我娘餓著。”鄰居送他一個饅頭,他要留給母親:別人給的好吃的,他總能找出自己不喜歡吃的理由,讓給母親吃。
從5歲直到上高中,張曉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撿柴火。一個風雪交加的冬日,張曉外出撿柴。天黑下來,仍不見兒子的蹤影,曹雪紅拄著拐棍踉踉蹌蹌挪到路口等待,只見兒子正吃力地將一大捆柴火往回拖。當時,曹雪紅一把將兒子摟入懷中,失聲痛哭。
苦難沒有壓倒張曉,小學階段的張曉,年年是學校的“三好學生”。進入初中、高中,他的學習也不曾落下。
張曉打小懂事,知道保護母親,不給母親添麻煩。
最初住在菜園子的草房里,狹小的空間容不下兩個人同時站立。冬天的寒風時常把木條拼成的“門板”掀翻,當時只有四五歲的張曉就用小鏟子在地上挖個坑,再找來木棍將門板死死頂住。
從菜園子里搬出來后,家中一度分文沒有,房東又催要房租。沒法子,曹雪紅忍痛賣掉丈夫生前留下的一條毛毯和自己結婚時用的一幅床罩、一對枕巾。
后來因為欠交幾十元房租和電費,房東掐了他們的電。悲憤交加,曹雪紅決定外出乞討。
拄著拐杖,在兒子的攙扶下,曹雪紅爬上長途汽車去了西安。可真坐在了西安的街頭,她卻怎么也張不開嘴,伸不出手。一連3天,沒要到一分錢,也沒吃上一口飯。狠狠心,母子倆花3.5元買了一碗面,可娘倆你讓我,我讓你,誰也不先動筷子。
記下“恩人薄”
回到平涼,在好心人的指點下,張曉給時任甘肅平涼武警某部政委的劉春灝寫了一封求助信。
很快,劉政委來到張曉家,送來米、面和慰問金。此后多年,劉政委和部隊官兵將張曉一家列入重點幫扶對象,一直關心著張曉的成長,有物質上的,更有精神上的。在張曉幼小的心靈里,軍人的堅強和勇往直前,深深地感染了他。
每位好心人的幫助,都被曹雪紅記入了自家的“恩人簿”。曹雪紅時常拿這些教育張曉,教育他要懂得感恩,懂得回報。
回首往事,張曉淚流滿面。可他不后悔,苦難的生活、好心人的幫助,以及母親樸素的教誨,讓他學會了堅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