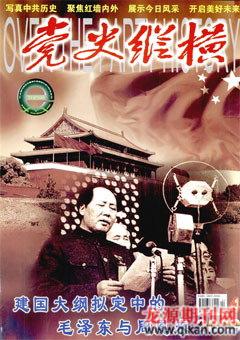蕭紅魂斷香江
周惠斌
女作家蕭紅以一部蕩氣回腸的《生死場》而馳名中國現(xiàn)代文壇。魯迅先生曾著文說,蕭紅“是我們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生死場》是“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qiáng),對于死的掙扎”的一幅“力透紙背”的圖畫。魯迅的評價之高頗為鮮見。
1940年初,結(jié)婚一年多的蕭紅與端木蕻良乘飛機(jī)自重慶飛抵香港。蕭紅到香港有兩個目的:一是應(yīng)原復(fù)旦大學(xué)教務(wù)長孫寒冰之邀前去編輯“大時代文藝”叢書;二是想尋求一個安靜的環(huán)境從事寫作。蕭紅來到香港后,受到了文化界人士的廣泛歡迎和愛戴。蕭紅十分感動,很快就融入到香港抗戰(zhàn)文化活動中。在給友人的一封信里,她動情地說:“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靜和秀美,有山、有樹、有漫山遍野的鮮花和婉轉(zhuǎn)的鳥語,更有洶涌澎湃的浪潮,面對著碧澄的海水,常會使人神醉的。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昔所夢想的寫作佳境嗎?”正是在這樣的“佳境”中,蕭紅于1940年底完成了她的又一部代表作《呼蘭河傳》,并陸續(xù)創(chuàng)作了中篇小說《馬伯樂》和短篇小說《小城三月》等作品。
“說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小說的問世為蕭紅贏得了諸多的榮譽(yù)和文學(xué)界的尊重,標(biāo)志著她的創(chuàng)作達(dá)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然而,巨大的成就卻難以減輕病痛的折磨,更掩飾不了蕭紅內(nèi)心的孤獨與情感上的寂寞。
“什么最痛苦,說不出的痛苦最痛苦。”這是蕭紅在其著名詩作《沙粒》中的收尾之句。她與端木蕻良到達(dá)香港不久,感情就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令圈內(nèi)外人士不勝唏噓。蕭紅比端木蕻良大一歲,他們的結(jié)合并非沒有感情基礎(chǔ),只是兩個人在性格上原本就存在著不可調(diào)和的沖突,卻始終沒能得到妥善的溝通和解決。熟悉他們各自情況的周黥文先生曾經(jīng)分析過:“兩人的感情基礎(chǔ)并不虛假,端木是文人氣質(zhì),身體又弱,小時是母親最小的兒子,養(yǎng)成了嬌的習(xí)性,先天有懦弱的成份;而蕭紅小時候沒有得到母愛,很年輕就跑出了家。她是具有堅強(qiáng)的性格,而處處又需求支持和愛。這兩種性格湊在一起,都在有所需求,而彼此在動蕩的時代,都得不到對方給予的滿足。”
其實,蕭紅在認(rèn)識端木蕻良之前,與蕭軍有過一段轟轟烈烈的戀愛與婚姻。她與蕭軍離婚后選擇端木蕻良時,應(yīng)該很清楚地看到端木身上的弱點。可是蕭紅還是決定與他結(jié)婚,這意味著蕭紅當(dāng)時認(rèn)為可以原諒并且容忍端木的弱點。然而事實上,由于蕭紅特殊的性格和經(jīng)歷,使得她又無法真正做到。加上兩個人初到香港,端木蕻良總是奔波忙碌于自己的文學(xué)事業(yè)而無暇顧及蕭紅的感情生活;而蕭紅虛弱的體質(zhì),特別需要親友的關(guān)懷與照顧,一旦內(nèi)心的期盼得不到溫馨的慰藉,就愈加感到落寞和惆悵。因此,當(dāng)蕭紅與端木蕻良的感情出現(xiàn)裂痕時,或許是同情弱者的緣故,當(dāng)時熟知他們的圈內(nèi)人難免把感情的籌碼放在蕭紅這一邊,在情感上更多地傾向于同情蕭紅。
“天涯孤女有人憐”
蕭紅和端木蕻良來到香港生活后,借住在九龍尖沙咀樂道時代書店一問狹小的房間內(nèi)。蕭紅身體一向多病,她常常咳嗽、頭痛甚至失眠,而且日益加重,以致于1941年初夏時,不得不因為身體原因而停止了寫作。
情感的失落,病痛的煎熬,讓蕭紅無限傷感和悲愴,她多么希望身邊有一位長者能像魯迅當(dāng)年那樣關(guān)心她、幫助她。這時,國民黨元老柳亞子先生走到了她的身邊。柳亞子的突然到來,使蕭紅既吃驚又感動。面對長者和文學(xué)前輩的寬厚安慰,蕭紅不禁熱淚盈眶。此后,柳亞子時不時地去看望她,鼓勵蕭紅堅強(qiáng)起來,戰(zhàn)勝疾病,樹立生活的信心。蕭紅慶幸自己又找到了一位像魯迅一樣的長輩,關(guān)心她的生活,點撥她的人生。
春去秋來,天氣不再悶熱。柳亞子捧來一束盛開的菊花來了。蕭紅斜坐病榻,感到生命在復(fù)蘇,感到一種激情在涌動。他們促膝暢談,關(guān)于人生和文學(xué),包括一切感興趣的話題。一對忘年交談興甚濃,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蕭紅默默地想著,自己到香港后,與柳亞子相識最晚,又訂交于病榻,而這位長者對她的關(guān)切僅次于魯迅,不禁感慨萬千。她動情地脫口吟了一句“天涯孤女有人憐”,由衷地表達(dá)了她豐富的情感和對人生的體驗。柳亞子一聽大為感嘆和動容,隨即在蕭紅病榻前賦詩一首相贈:
輕飚爐煙靜不嘩,膽瓶為我斥群花。
誓求良藥三年艾,依舊清淡一餅茶。
風(fēng)雪龍城愁失地,江湖鷗夢倘宜家。
天涯孤女休垂涕,珍重青韶鬢未華。
“你就是最慷慨的人”
在情感與病痛的雙重折磨下,走在人生最后旅途上的蕭紅感情愈益脆弱,她常常被一種無法把握命運的恐懼所包圍。隨著過去與端木蕻良之間的那種如癡如醉和夢縈情牽的感覺的漸漸消失,特別是與自己衰弱的身體狀況形成對比的是,蕭紅在精神上的渴求更加強(qiáng)烈,她需要愛,迫切需要一種情感的依托。這時,一個人走進(jìn)了她的視野和生活,而蕭紅也情不自禁地對他產(chǎn)生了一種超乎尋常的特殊感情,這個人就是駱賓基。
駱賓基是蕭紅胞弟張秀珂的朋友,他到香港后經(jīng)人介紹認(rèn)識了蕭紅。他給蕭紅的最初印象是“中等身材,有著北方農(nóng)民的魁梧,一張同屬于北方農(nóng)民的紫銅色長臉上,常常寫著質(zhì)樸和沉思。鼻梁上架著一副棕色的眼鏡,眼鏡后面是一雙不大卻充滿活力和感情的眼睛”。正是這雙眼睛讓蕭紅充滿了好感。由于蕭紅的推薦,端木蕻良將自己在《時代文學(xué)》上連載的《大時代》停了下來,繼而發(fā)表駱賓基的《人與土地》。為了感謝蕭紅夫婦對他的幫助,駱賓基常去看望他們,而駱賓基的頻繁探訪,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病榻中蕭紅的孤寂感。
不久,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香港陷于日軍炮火之中。病中的蕭紅倍感生活的空虛和孤寂。一日,疲憊已極的蕭紅在病榻上緊緊地握住駱賓基的手,慢慢地閉上眼睛。駱賓基默默地在一旁陪伴著,須臾也不離開。醒來后的蕭紅以一種復(fù)雜的感情對他說:“我現(xiàn)在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就是最慷慨的人。”蕭紅顯得有些動情,“我是一個非常矛盾的人,常常陷入與愿望相反的矛盾里,也許這就是命吧。和蕭軍的離開是一個問題的結(jié)束,和端木又是另一個問題的開始……”望著蕭紅那日益憔悴的臉,駱賓基深深地感受到了她內(nèi)心的孤獨和渴望被別人關(guān)心的期待。
“我將與藍(lán)天碧水永處”
蕭紅的病情不斷惡化,與蕭紅相熟于30年代的美國著名記者史沫特萊返美途經(jīng)香港時,知道了蕭紅因病魔侵襲而身心憔悴。她隨即將蕭紅接到沙田何鳴華大主教別墅住了一段時間,可病情絲毫不見好轉(zhuǎn),于是又將她送往瑪麗醫(yī)院就診,蕭紅最終被確診為肺炎,需要住院治療。
香港的住院費一向十分昂貴,端木蕻良和蕭紅的稿費收入根本不夠支付醫(yī)院的治療費用,生活一下子陷入了拮據(jù)。史沫特萊通過自己的關(guān)系幫助蕭紅將住院費打了折扣,而另外的費用則由當(dāng)時在香港的蕭紅東北老鄉(xiāng)、曾經(jīng)擔(dān)任東北大學(xué)校長的周黥文承擔(dān)。史沫特萊和周黥文的幫助使蕭紅暫時度過了危機(jī),然而卻最終沒有幫助她走出不幸的命運。
1942年初,為躲避戰(zhàn)火,蕭紅又被轉(zhuǎn)至跑馬地養(yǎng)和醫(yī)院,可醫(yī)生們對蕭紅的病情會診后卻誤斷為喉瘤。第二天,蕭紅被送進(jìn)手術(shù)室,接受了一次痛苦的喉管切開手術(shù),由于傷口難以愈合,手術(shù)后蕭紅的身體虛弱不堪。這時,蕭紅似乎已經(jīng)意識到自己病情十分危重,反而顯得出奇的平靜。不久,端木蕻良和駱賓基又將蕭紅轉(zhuǎn)入瑪麗醫(yī)院重新動手術(shù),換喉口的呼吸管。這次手術(shù)后,蕭紅沒有辦法說話了,病榻上的她示意駱賓基取來紙筆,寫下了:“我將與藍(lán)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這是蕭紅生前留下的最后的一句話。
就在蕭紅第二次手術(shù)的第二天,瑪麗醫(yī)院被日軍占領(lǐng)。醫(yī)院被換上了“大日本陸軍戰(zhàn)地醫(yī)院”的牌子,蕭紅隨即被悄悄轉(zhuǎn)移到紅十字會設(shè)在圣士提區(qū)的臨時醫(yī)院。由于一路輾轉(zhuǎn)顛簸,本已虛弱不堪的蕭紅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她的身上蓋著毛毯,仰面躺著,臉色蒼白,面頰消瘦,雙眼緊閉著,頭發(fā)披散地垂在枕后。但她的心臟還維持著微弱的跳動,游絲一般的呼吸仿佛一不小心就會丟失了似的。端木蕻良和駱賓基看到蕭紅被病痛折磨的樣子都感到揪心的疼痛,他們站在蕭紅的病榻前,一刻也不離開,陪著她,望著她。兩個小時后,蕭紅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一個在中國文壇上熠熠生輝的女作家,就這樣走完了32年崎嶇的人生之路。
蕭紅最后被安葬在香港淺水灣一個依山傍水的地方。蔥蘢的林木,漫山的鮮花,婉轉(zhuǎn)的鳥語,澎湃的浪潮,碧澄的海水,這樣“使人神醉”的佳境,蕭紅的靈魂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