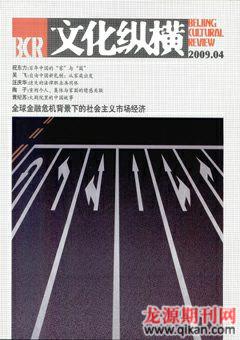在“愛的奉獻”中想象公民社會
張慧瑜

“汶川大地震”已經過去一年了。在這次突發事件中,大眾傳媒在國家動員中扮演了格外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地震不久中央電視臺舉辦的大型直播晚會“愛的奉獻”(2008年5月18日),把這次“眾志成城、抗震救災”的情感動員推向高潮。“愛的奉獻”、“人人都獻出一份愛”式的話語成為整個社會廣泛認可的共識,連同這幾年關于公益、志愿者、社會基金會的熱烈討論,社會救助、奉獻愛心已經成為一種似乎毋庸置疑的道德規范和自律。對于這次抗震救災,學者及諸多媒體多從中國公民社會的成熟角度來論述普通公民自發參與救災的熱情。這種對公民社會的呼喚,自20世紀90年代冷戰終結之后進入中國,直到今天才得以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力量;而關于公民社會的想象也由一種對體制的批判轉變為構建社會和諧的積極表述。“愛的奉獻”和“公民社會”這兩種想象,已經成為整合當下中國社會的重要話語,而這些話語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功能,值得進一步反思。
作為社會共識的“愛的奉獻”
在這次抗震救災中,我們看到了志愿者或民間(公民、市民)社會的力量和作用,民眾自發的救助是如此“強大”和自覺。這次救災的動員效應絕不僅僅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宣傳,而是城市市民或說中產階層自覺的慷慨解囊,是一種以人道主義為主體的道德自律的自覺展現。如果說超女比賽通過“拇指民主”實踐了民間社會的想象,那么這次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中產階級市民的強烈的責任感和道德感,而得以實現這種道德自律的話語是“愛的奉獻”。
“愛的奉獻”作為一個名詞性短語,如同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國企改革攻堅戰中出現的社會文化表述“分享艱難”一樣,非常巧妙地回避了主體與客體的位置。“分享艱難”并沒有說出“誰”分享“誰的”艱難,但是這個短語本身卻把市場化進程中的被剝奪者(比如下崗工人)承受國家改革代價的問題(也常常被描述為轉型期的“陣痛”)轉化為讓“人民”來分享“國家”艱難的一種有效詢喚。“愛的奉獻”也是如此,“誰的”愛奉獻給“誰”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或不需要說出的前提,“愛的奉獻”恰恰要空出這樣一個主體位置等著你、我、他來由衷地填充,恐怕很少有人把自己放在被救助者的位置上。在這種道德撫慰中,我們是作為救助者去拯救災民的,可是,“人人”都是奉獻者,這里的“人人”真的是“人人”嗎?事實上,這種中產階級道德是有邊界的,因為中產階級屬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市民階層,市場的邊界也是中產階級的邊界。在電視中我們看到的獻愛心的人大多是城市市民,農村/農民依然在這種市民空間想象之外,也就是說農村/農民已然不在捐款──愛的奉獻的想象的共同體里面(起碼媒體上很少看到這樣的報道,即使有也不是媒體和觀眾所想象中的那些要獻出愛心的人)。
這種“愛的奉獻”式的話語成為一種社會共識,其意義,還不在于作為準中產階級主體的城市市民被這種話語所整合,而在于這種意識獲得了普遍認同,使人們意識不到或者說不能馬上就意識到這是某個階層的訴求。 “愛的奉獻”的晚會本身很空洞,但能指越空洞,越具有包容性。下面我試圖從兩個方面來論述“愛的奉獻”所預留出的主體位置是如何被非中產階級的底層民眾以及作為中產階級預備軍的80后所分享的,以說明這種話語所具有的整合力。
網絡上天涯社區有一篇名為:《大災了,我流了很多淚,沒有捐一分錢,大家來鄙視我吧》的帖子,是一個工廠的工人為自己沒有捐款而感到愧疚,沒有去捐款的理由有:一是廠門口的捐款箱無人問津,作者又不愿意“露風頭”;二是要捐款就必須“坐公交車到很遠的沃爾瑪超市門口的紅十字會捐款箱”(從以工廠為單位的“集體”捐款到去沃爾瑪“自愿”獻愛心,這種空間轉換本身是兩套價值觀和生產方式的轉型,前者是生產空間,后者是消費空間,而這種“愛的奉獻”恰好與消費者的身份密切相關),考慮到距離,作者沒有去;第三個,或許也是對作者觸動最大的一個原因是,他看到災民的伙食“標準”比自己這個工廠的正式工人還要高。出于這些原因,作者沒有去捐款,因此,“我一直覺得心里很糾結,不捐錢好像欠了誰的。難道我不是一個善良的人嗎?我也曾自愿地跑到血站去獻血。我為大災流了無數的眼淚。”是什么對這樣一個帖子中的工人造成如此大的愧疚感呢?按照作者的敘述,僅從災民的伙食對比中,就可以看出他是比災民更“災”的群體。如果真是如此的話,帖子的敘述者本人應該也是被救助的對象才對,可是作者為什么偏偏沒有意識到自己是需要被幫助的人,反而為自己無法成為捐款者也就是去幫助別人而深深愧疚呢?這恰恰就是“愛的奉獻”等人道主義話語自身所建構的主體位置。也就是說,“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愛的奉獻”所強調的是“獻出”,而不是接受,作為奉獻的接受者在這種敘述中是客體的位置,而不是主體位置。因此,帖子的敘述者為自己無法填充或滿足這樣一個必須“獻出”的主體位置而深深地自責和焦慮。

如果說“非震區災民”因對這套話語的認同而自責,反而呈現了他從屬于低階層的身份,那么80后在這次抗震救災中,“終于”獲得雪恥惡名的契機。80后是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環境中長大并深受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影響,普遍存在著一種政治/社會冷漠癥。但這次抗震救災中,80后不僅踴躍參與獻血、捐錢、捐物,更以個人或志愿者組織的形式趕赴災區直接參與救災,有媒體稱“80后志愿者成為四川抗震救災志愿者的中堅力量”。在我看來,這種80后的愛國主義熱情,與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當作未來城市里的準中產階級的身份認同密不可分,因此,他們“自然”具有一種以人道主義為核心價值的中產階級道德自律。
可以說,這種建立在人性、人道主義基礎上的以捐款捐物為行動指南的意識形態性,不在于要求富人、有錢人、中產階層去獻出愛心,而是那些顯然非中產階級的人們也由衷地認同于這樣一種敘述,并把這種敘述邏輯內在化。這也可以證明這樣一套話語自身所具有的整合力和動員效果。說到這里,我們就不得不進一步追問,究竟為什么這樣一套老話語會“煥發出新顏”?這套話語形成于19世紀,30年前剛剛在中國出現的時候,其意識形態性還昭然若揭,甚至被作為異端的思想,但是此時此刻,這套話語的意識形態屬性卻已經很模糊了,這是否意味著,意識形態只有以非意識形態的方式才能有效運作,一旦露出意識形態的尾巴,也就離失效不遠了。此外,這套話語會如此有力而有效,恐怕與當下中國的社會結構的固化有關。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還處在階層極速分化的過程中,那么最近一兩年,似乎這種社會結構的分化已經完成,人們很清楚自己處在什么樣的位置上。就像帖子中的工人,他分享了這種中產階級的陳詞濫調,同時他也從“新聞”中看到了自己實際上處在比災民還要差的一種階層位置上,但是他無法也不能對這種中產階級話語提出什么異議或不同的視角,反而是把自己放在要去捐款的位置上。這種話語的有效性,不在于中國的中產階級有沒有形成,或者說人數和力量究竟有多大,而在于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成為大眾媒體(顯然,沒有市場化的農村不在這個“大眾”里面)所竭力建構的社會共識,也就是說,中國雖然沒有80%的中產階級,但并不妨礙以中國大小城市為市場邊界的社會把中產階級的價值作為社會的主流價值, “愛的奉獻”的話語也得以成為社會各個階層所分享的共識。
公民社會及其“公民想象”
——以王石捐款、范跑跑事件為例
2008年的抗震救災形成了強有力的社會共識,尤其是對于絕大多數通過電視、網絡間接“目擊”獲得“現場感”的觀眾來說,這是一次危機時刻的心靈洗禮,或者說,人們在這次地震中經歷了一次公民教育,鍛煉了人們的參與意識,預示著中國公民社會正在走向成熟。90年代初期對公民社會(也稱“民間社會”或“市民社會”)的呼喚終于結出了“碩果”,一方面民營企業踴躍捐款捐物,另一方面普通公民積極捐款獻血或以志愿者的名義奔赴災區。
但是,在這次“公民意識”的演練中,有兩個成員卻受到了批判,一個是地震發生之初,萬科掌門人王石因捐款少招致網友指責,網絡將此次事件稱為王石遭遇“捐贈門”;第二個是在媒體一次次地報道災區教師不怕犧牲自我保護學生的師德典范之時,都江堰某中學語文老師范美忠卻在天涯博客上公開發表《“那一刻地動山搖——5?12汶川地震親歷記》的博文(5月22日),“有理有據地”闡明自己為何要逃跑的合法性,引發網友一片嘩然,這就是“范跑跑事件”。把這樣兩個例子放在一起是因為他們因不適當的行為而被人們批評為不合格的“公民”,他們之間的內在連接恰恰在于為公民社會的理念提供了“反面”例證。
具體來說,王石受到批評,并非沒有捐款,而是被認為捐得不夠,并且還為他的行為辯解。這顯然不符合人們對王石以及萬科這樣一個知名并熱心公益事業的民營企業的期待。對于富人、企業家捐款的期待已經成為社會共識,而王石及其萬科企業追加捐款并無償參與災后重建,顯然也是高度認同于這種社會共識的結果,而捍衛這種社會共識的,就是充滿正義感并認同慈善是正當的網民或公民。這究竟是一種左派情結的體現,還是這些網絡上的中產或準中產階級對于企業家應該有社會責任感的監督和批評呢?伴隨著國家推進市場化改革,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醫療、勞保、教育等國家福利政策被當作包袱甩掉之后,階層分化越來越嚴重,“公益”才漸漸成為一種彌合這種市場化代價的社會修辭。這種修辭中與企業家有關的,就是成熟的企業家要關心慈善事業,網友對王石的指責,顯然不是某種階級仇恨,也不是對于資本的批判,反而是在高度認同慈善、公益事業這樣一個社會共識的前提下對資本家的一種道德約束。
如果說王石事件,重新確認了企業家/資本家在這個社會中的合理位置,那么范跑跑某種意義上被作為普通人(盡管范跑跑出身精英教育,并從事教師這個特殊的職業),他的出現使人們可以評判什么才是合格的公民/個人。在《那一刻地動山搖》的激揚文字中,范跑跑懷著一種遭受“政治迫害”的妄想,對自己為何先跑進行了辯解。其中,最為“鏗鏘有力”的是“我是一個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卻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犧牲自我的人”。這句話的有趣之處在于一個“卻”字,為什么在范跑跑這里,“自由和公正”與“先人后己勇于犧牲自我”就是相悖的或者說不兼容的呢?這恐怕與冷戰歷史及其意識形態之爭有關。在這種振振有詞的對立背后,是前者代表著“自由、公正、民主”的 “普世價值”,后者代表著“犧牲自我,匯入人民”的道德精神。在后冷戰的時代,自由、民主、人權早已成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主流,而諸如國際主義等帶有超越性的道德價值早已經被污名化(或者轉換成人道主義話語)。這樣兩種價值的對立,恰恰是冷戰時代西方陣營的邏輯在后冷戰時代的延伸。在這一點上,范跑跑與其說是思想異端,不如說是當下的主流。
一個看似毋庸置疑的前提,王石、范美忠顯然是公民社會的一分子。他們都具有市民的資質(他們不是農民工,也不是農民),因此,他們恰好是成熟而理想的資產階級主體的兩個面孔,一個是喜歡攀登、勇于挑戰的浮士德式的英雄,一個是“膽怯、自私而自負”(借用學者黃應全對范跑跑的精彩描述)的個人。這種網友們“自發地”在危機時刻對公民社會的道德規范認同,恰好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樣本。網友指責或批評王石和范跑跑的社會文化邏輯及動力,恰恰不是階級仇恨式的實踐邏輯,而是處于對中產階級或公民道德的捍衛。
意識形態的整合
在一些以監督政府為職責的“公共”媒體中,關于災后重建或者說追究地震責任的話題沒有例外地投向了地震中倒塌的學校以及如何領養孤兒身上。我想從2008年六一節前鳳凰臺的欄目《一虎一席談:他們為何讓我們如此感動(下)》說起。這期節目的前半段主要圍繞著一位嘉賓“親眼”看到北川中學的廢墟而引發的對于學校建筑質量的質疑,現場的大多數觀眾也認為應該有人來負責。后半段另一位嘉賓則說“親眼”看見20世紀70年代的建筑沒有倒,90年代新建的商品房卻出現了裂縫而引發了對于70年代和90年代兩個時代的評價。在這里,最初關于學校倒塌的問題已經發生了轉移。無論是鳳凰臺的片花,還是第一位嘉賓的發言,都集中在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建筑為什么會倒塌的問題上,也就是說在公共建筑與商業建筑之間進行對比,而第二位嘉賓卻把這個問題轉移為對社會主義中國以及市場化之后的中國的對比之中。這也就把前一個問題中所需要問責的諸如官員腐敗,建筑公司為了牟利而偷工減料的問題,轉移到了市場化改革帶來的負面效應之上。這是兩種對當下抗震救災反思的主要思路,前者偏右,后者偏左。有趣的問題在于,這樣兩種左右的論述卻“并肩作戰”,和諧地出現在同一個舞臺上。這或許是9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以來出現的新情況。這種“轉移”似乎很順暢,但問題并非如此簡單。
前者的邏輯,在地震剛剛發生之初,就成為國內被稱為自由派知識分子發言的重心,言外之意,在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設施的倒塌背后有官員腐敗、施工單位“豆腐渣工程”之嫌。這種論述在一次又一次礦難等特大安全事故中成為“陳詞濫調”,說到底,是人治的結果(權力濫用)。因此,這種批判所提供的解決方案,是法治,或者說制度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監督權力),而官僚體制往往是這種論述打擊的靶心。所以,朱大可的文章《誰殺死了我們的孩子?──關于汶川地震的反省與問責》、朱學勤的“天譴論”以及《南方周末》的報道《汶川震痛,痛出一個新中國》,選擇學校坍塌的問題來追究相關職能部門的責任都是這種邏輯的產物。后者偏左的邏輯是把學校的倒塌看成是市場化改革的負面結果,這種論述往往參照著對一種“被理想化”的毛澤東時代的眷戀。其潛臺詞是,在市場化的滾滾大潮中,追求利潤與建設學校這樣的公共設施存在著沖突,因此,出現“豆腐渣工程”是必然的。官方腐敗也來自于權錢交易和權力尋租,使人們、公司很難出于公心對公共事業付出超利益的責任,在對社會主義時代的懷舊中提出對市場化的“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式的帶有道德色彩的批評。所以說,當嘉賓舉出地震后在同樣的地勢上建設于70年代末期的仿蘇建筑赫然屹立,而90年代的建筑卻成廢墟,就成為某種隱喻,這種對毛澤東時代的懷舊或許成為90年代以來對于市場化不滿情緒的“真實”反映。許多人從抗震救災期間“人民”(而不是“公民”)積極踴躍地捐款、獻血和志愿去災區的行動中也看出許多“社會主義的遺產”,如黎陽的《抗震救災靠的是毛澤東的遺產,還是“國際接軌”?》的文章。這種對“社會主義遺產”的發現,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是市場化不徹底的明證呢?其實,朱大可的文章正好提供了一種反面的論述,“歷史學家向我們證實,這種高效率的救災運作,恰恰就是亞細亞威權政治的傳統。從大禹理水,經望帝(鱉靈)抗洪到李冰修堰,這些著名的抗災人物,都向我們提供了威權主義的效率樣本。汶川地震再度證明,自然災難和威權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關系”,在社會主義遺產的發掘與威權主義的批判之間,應該何去何從?
表面上,左與右的論述大相徑庭,其實,卻分享了相似的邏輯。只是不同的立場,使他們推論出截然相反的結論(相比“公民”的抽象性,“人民”更顯空洞)。或者說,左右兩邊都可以找到充足的論證自身邏輯的現實基礎,也就是說當下的社會機制既可以支撐公民社會成熟的論述,也可以支撐社會主義遺產的論述,左右兩邊被成功地縫合在一起,一方面是愛國主義、中國加油,另一方面是生命、人的價值得到從未有過的高揚,在這個意義上,新時期30年可以說在意識形態上已經完成了某種有效的整合。恰如鳳凰臺的節目中,從對政府的問責可以順滑地轉移對毛澤東時代的某種眷戀,這或許是這次抗震救災給我們這些試圖對現實提供某種批判性思考的人們留下的悖論,甚或尷尬之一吧。
結 語
在這次抗震救災中,以“愛的奉獻”為核心的人道主義話語,填充了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市民社會的想象,并成為社會的和諧之音,在彌合社會鴻溝或者修正妒恨政治學的同時,也印證著中國社會結構分化的固化或完成。借助抗震救災這一突發事件,得到演練的或暫時獲得想象的公民社會只展現了其溫情的一面,距離可以充當社會抗爭空間的遠景還相當遙遠。在這種未完成的狀態中,呈現公民社會的想象自身的壓抑性或遮蔽性也許并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們在災難面前并非不要獻出愛心,不要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這種政治上的人道主義是必須的,也是應該的,但這并不能否定,從理論上反思人道主義的意識形態效應及其遮蔽性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