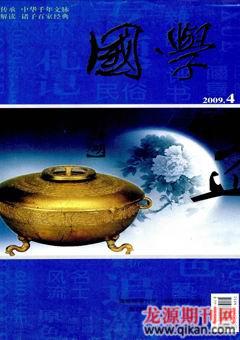馬吉芬:從美國來參戰
美國人馬吉芬,本想用加入中國海軍這段資歷,使自己進入美國海軍,最終卻把生命獻給了黃龍旗下的這個國度。
加入北洋水師
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是馬吉芬的母校,1884年他臨畢業時,美國國會突然出臺一個法案,只有當軍艦上缺員了,才能有新兵替補,這一年只有12個名額。馬吉芬不是前12名,因此他在得到1000美元安置費后,回家待業。
從小向往當海軍的馬吉芬并不想當待業青年,就在這時他聽說中國為了迎戰法國,將在福州開辦水師,為了不荒廢學業他搭了4個月的輪船,投奔中國海軍。1885年4月10日他剛到天津港就聽說戰爭已經結束了,事實上,這場戰爭根本沒能打起來,為中國建造艦艇的德國人,迫于法國的壓力,沒敢把造好的軍艦交付中國,中國海軍甚至是用土炮木船來應戰。所以在馬吉芬前往中國的途中,這場戰爭早已在法國強大政治攻勢和國際地位上不戰而勝了。
從布滿水雷的天津港登陸中國后,馬吉芬曾經請美國副領事派曲克把自己的求職信交給李鴻章,第二天他干脆直接跟著船長進了總督府。李鴻章告訴他必須通過軍械局水師學堂的多學科考試,才能受雇。第二天,在一群頂戴花翎的監督下,馬吉芬通過船舶駕駛、槍炮使用、導航、航海天文學、代數、幾何學、球面三角學、二次曲線以及積分等項目的考試,這也是中國水師學堂學生需要掌握的知識。
他覺得自己只答了所有卷子的六成,但是中方考官認為這個24歲的洋人已經令他們滿意了。從此,馬吉芬成為李鴻章創辦的天津水師學堂的外籍教習,也是唯一能教授船舶駕駛和槍炮使用的人,這位漂洋過海來到中國的美國人還負責傳授領航和航海天文學知識,同時還要訓練陸軍和炮兵的學員教他們如何筑防。這份職業帶給馬吉芬1800美元的年薪,聘期3年。因此,中日甲午海戰中有很多軍官都是他的學生。
這一時期的馬吉芬,心里一直盤桓著他的“曲線就業”夢想,他在給家人的一封信中說:“如果美國海軍部長明白,我在這里所獲得的技能上的收獲大大超過在海上服務所可能獲得的收獲,那么他也許會給我開兩年假,只發半薪或者1/4薪水,甚至不發工資,但把我繼續保留在美國海軍的軍官名冊上。”此后,他多次表達用在中國海軍工作的資歷來換取進入美國海軍的資格。
親歷黃海海戰
馬吉芬在中國度過了他一生中美好的10個年頭,他也把自己最好的年華給了中國,第10年,他34歲。
馬吉芬想回家鄉休個假,但就在他回國前夕中日宣戰。“中國和日本馬上就要開仗了,我們很可能就此永別,但我必須留在崗位上。在中國服役的10年里,他們始終以仁慈對我,如果這個時候遺棄他們,將是多么可恥。”他在戰前給父母親發回這樣一封信。
主動撤消休期的馬吉芬用行動向中國海軍及政府表示了他對這個國家的忠誠,被任命為7430噸的“鎮遠”號戰列艦的幫帶(相當于副艦長),這是一艘與提督丁汝昌旗艦“定遠”號同型的戰艦。
浴血黃海的全程是怎樣的,頭部受重創的馬吉芬曾經多次回憶過,但是一直沒有清晰有序地描述過,《洋人舊事》的作者張功臣曾經想把馬吉芬的回憶理出個頭緒。他唯一不會遺忘的就是炮戰開始那一刻,他從此刻由一名教習變成出征的戰士。
不同于馬吉芬向丁汝昌建議的先發制人,他發現中國人非常善于忍耐和等待,中方的戰略是“避敵保船”,持重防守。這一點令馬吉芬百思不解。
“鎮遠”艦12英寸炮命中日本艦艇“浪速”號時北洋水兵的歡呼聲,還時時在海軍醫院病房中被回憶起來,在接下來馬吉芬寫給《世紀》雜志的回憶錄中,“鎮遠”艦的情況急轉直下,它遭到3艘日本戰艦合圍。
馬幫帶的“鎮遠”號被日艦發來的重炮打中了前甲板,管帶林泰曾被震得當場昏死,馬吉芬在頭暈眼花中接替林泰曾指揮戰斗。打到下午兩點,日本對中國的艦只由12:12很快就變成12:8——“濟遠”和“廣甲”棄戰而逃,還有兩艘 13年前的陳舊設備“超勇”、“揚威”沉沒擱淺。丁汝昌所屬旗艦也在日艦合圍下燃起熊熊烈火。
看到旗艦受損后,馬吉芬命“鎮遠”號逼近日本艦隊以分散日軍火力,日軍旗艦“吉野”號被吸引到“鎮遠”艦的近旁。馬吉芬命4門克虜伯主炮齊發,吉野因此喪失戰斗力,并帶領兩艘艦撤退。馬吉芬隨后見證了彈盡后的鄧世昌率“致遠” 號撞沉正在逃離的日旗艦“吉野”號與倭寇同歸于盡的場面。
多處負傷幾近雙目失明的馬吉芬在昏迷中被抬進船艙,此后有些戰爭場面,他在兩年后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來。馬吉芬所在的“鎮遠”號在9月17日開戰后,千瘡百孔的軀體一直燃著大火,馬吉芬本人在戰后留下了頭裹棉紗、渾身是血的照片。
這次黃海大東溝海戰結束了,清廷表彰了7位在加入中國海軍并作戰英勇的洋人,馬吉芬得到頂帶花翎和三等第一級寶星勛章。
回國醫治內創外傷
甲午戰爭打到了乙未年,1895年2月17日,日軍攻破威海衛,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還迷失在對這場戰爭速敗陣局中的馬吉芬,突然聽到一個令他更為不解的消息,朝廷打算把戰爭的失利算到他這位勇于為中國參戰的洋人顧問頭上,他將成為這場戰爭失敗的替罪羊。
作為軍人的馬吉芬是非常機靈的人,無論是否能理解中國人的用意,他決定一走了之。比他來中國時艱難百倍地被人藏在一艘美國貨輪中,偷渡回國。
回國后,他被人稱作馬吉芬少校,一時成為同胞們關注的焦點。他對于中日海戰的講述開始是新聞,后來被當作瘋話。他本人也表示出一些瘋狂跡象,他疼痛難忍、煩躁不安、恐懼醫院,還揚言要殺人。
情緒穩定的時候,他就給自己在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的同窗——《世紀》雜志的理查德·沃森·吉爾德博士繼續寫他的戰爭回憶。
他在寫作的過程中,依然無法理清中國所發生的某些問題,他所敬重的丁提督在死前早已被摘了頂帶,革了官職,讓他繼續留在海上和陸地上作戰,只是因為無人能夠接替他。而提督死后,光緒皇帝還下了籍沒家產、不許下葬的圣旨,并令其子孫流落他鄉。至于他本人,一位想為自己祖國海軍效力的青年,在中國用盡10年韶華后倉皇出逃,并且繼續為自己的祖國所誤解。
那只傷痛不已的右眼摘除后,他就能“一目了然”了嗎?似乎還是不能。困惑的馬吉芬不再等待明天大夫來動刀子了,他親手給自己做了最后的手術。
“謹立此碑以紀念一位雖然深愛著自己的祖國,卻把生命獻給了另一面國旗的勇士。”
這是他的墓志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