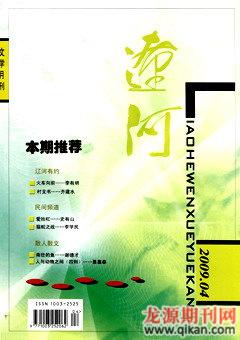人與動物之間(四則)
聶鑫森
馴鶴之趣
此生真正一睹大自然中自由自在的鶴,是在貴州威寧的草海。草海是我國三大高原淡水湖之一。那是一個冬天,但這里陽光燦爛,碧水連天,我與鄧剛、舒婷、張韌諸君,應主人之邀來此采風,乘船游于湖上。到處飛翔、棲息著水禽、水鳥。據介紹有百來種,黑頸鶴、白鶴、灰鶴、野鴨、鳧、鸛……把個草海渲染得生機盎然。因是保護區,無人敢傷害它們,它們也就不怕人。在湖中的一塊小洲上。離我們不遠的幾只黑頸鶴,曲頸黑如綢緞,羽毛潔白如雪,正在振翅起舞,婀娜多姿,真把我們看呆了。鄧剛告訴我,他在黑龍江的自然保護區看過丹頂鶴的翩翩舞姿,那頭頂上的一點朱紅,閃爍在疾快的舞影中,美得很哩!可惜草海沒有丹頂鶴。
全世界共有15種鶴,我國即有9種,丹頂鶴為此中珍品。因丹頂鶴色彩華美,體態輕靈,且壽命很長(一般能活六十多年),歷來受到人們的喜愛。
《詩經》中“鶴鳴九皋,聲聞于天”的句子,是詠鶴的最早作品。
我國很早就馴養仙鶴以作觀賞,《毛詩義疏》云:“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左傳》中記載,春秋時衛懿公好鶴,不理朝政,因而亡國。到晉時,養鶴之風盛行,《方輿勝覽》中說有名的將軍羊祜鎮守荊州時,見江陵澤中多鶴,讓人捉了來教舞以娛賓客,于是江陵澤得名鶴澤,江陵郡亦名鶴澤郡了。還有個陸機,亦好養鶴,被成都王誅殺時,“顧左右而嘆曰:‘今日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晉八王故事》)。其愛鶴之心切,遠勝于自己的生命。
“羊公鶴”是一個著名的典故:晉人羊祜喜歡養鶴,常向人夸耀他的鶴善于舞蹈,有人要求親目一睹。沒想到那只鶴羽毛松散,根本不會跳舞,令羊祜很難堪。后以“羊公鶴比喻名不符實的人。”唐人寒山《詩》之十一:“恰似羊公鶴,可憐生懵懂。”
在宋代,林逋“梅妻鶴子”的故事,更是傳頌一時。他孑然一身,隱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絕意仕途,超然物外。“……畜兩鶴,縱之則飛入云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逋揚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驗也”(《夢溪筆談》)。
在神話傳說中,仙鶴常為神仙的坐騎而翱翔于云天之上。故老人故去,在挽詩挽聯中稱之為“駕鶴西去”,以示成仙升天。“月明華表鶴歸遲”(元·虞集《挽文山丞相》;“鶴歸華表古城秋”(聶紺弩《挽畢高士》)。畫家畫鶴,最常見的構圖,是往往配以青松巨石,翠竹梅花,以喻其長壽、清高、吉祥。款識多為“松鶴延年”、“松齡鶴壽”、“梅鶴同春”、“高風亮節”等等。
歷代寫鶴之詩,數不勝數,但專寫鶴舞的卻以明人邵寶的一首七律最為精彩:“誤向丹青共羽流,多情今得此停幽。長鳴似與高人語,屢舞誰于醉客求;鳳羽九逵能抗晚,野心萬里欲橫秋;試將衣袖閑招引,轉盡花蔭意未休”(《鶴舞》)。
古人為什么喜歡馴養仙鶴呢?其一,它是群鳥中的高士,超群拔俗,飄逸絕塵;其二,是它潔白的羽毛,修長的身段,最易讓人產生美感,長空嘹唳。中庭起舞,更是令人感奮。其三,鶴被視為長壽的象征。
現在當然沒有私家養鶴的了,但全國的一些濕地保護區里,繁衍著各種鶴的種群,成為公眾觀賞的對象,正如孟子所言:“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鴿哨嘹亮鴿翅健
梅紹武在《我的父親梅蘭芳》一書中寫道:“父親年輕時因患近視,放過一陣鴿子,兩眼追隨它們在空中飛翔以糾正自己板滯的目光。這是許多內行人都知道的,殊不知這還有鍛煉身體的因素在內,那就是他為了引飛鴿,需要不斷地揮舞一根頂端系著紅綢條的、兩丈長的竹竿,從而也就增強了他的臂力。后來,他排演《霸王別姬》,私下練習劍舞又常常用一對相當沉重的鋼劍,到了臺上運用一對輕輕的木制寶劍翩翩起舞時,就沒有給人一種飄浮或吃力的感覺。”
梅蘭芳養鴿、馴鴿,既愉悅了身心,又糾正了視力,增強了臂力,使他在舞臺上更加光彩照人。
全世界的鳥類約有八千五百余種,而鴿類就占五百五十種左右。由于鴿子具有性格溫順、戀家和飼養簡便等特點,故被喻為“空中的家禽”,成為人類親密的伙伴。
鴿子,屬鴿形目,鳩鴿科,它和斑鳩在親緣上是十分相近的。人類把野鴿馴養為家鴿,已有幾千年的歷史。我國在兩千年前就開始馴養鴿子了,到唐、宋時已很盛行。宋人陶谷所著的《清異錄》記載:“豪家少年尚蓄鴿,號半天驕人;又以其蠱惑過于嬌女艷妖,呼為插羽佳人。”南宋的高宗,荒疏朝政,沉迷于斗雞養鴿。清人富察敦崇在他所著的《燕京歲時記》中,說當時北京的鴿子,尋常品種有點子、玉翅、鳳頭白、兩頭烏、小灰、皂兒等數十種,較為名貴的有短嘴、白鷺鷥、白烏牛、鐵牛、青毛等。清初詩人王漁洋在《居易錄》中,記敘他在鴿市上見過一對渾身金黃色羽毛的鴿子,價值百兩白銀。
鴿子分為三大類:用于賞玩的“觀賞鴿”、用于傳遞書信的“信鴿”、用于食用的“食用鴿(菜鴿)”。
我國的信鴿,在楚漢相爭時,即開始使用。五代時的王仁裕在《開元天寶遺事》中記錄了“飛奴傳書”的故事:“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系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為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以信鴿傳遞親朋好友之間的書信,這是何等有趣的事!
因鴿子戀家,而造成的一種“趨歸性”,所以從古到今,養鴿者喜歡進行放飛的比賽,即提著鴿籠,千里馳驅到某地,然后再放飛鴿子,看誰的鴿子最早飛回家中,以定勝負。
鴿子的眼睛,由上百萬根神經纖維密集而成,視網膜具有定向運動、鑒別顏色、辨識復雜圖像、看見紫外光和偏正光等功能,離家再遠,也能識別歸途。此外,鴿子還能觀察太陽、月亮及星辰位置的變化,從而確定正確的飛行方向。它的聽力也極敏銳,能聽到人耳無法聽到的次聲。
人們養鴿、馴鴿,主要是信鴿和觀賞鴿。
觀賞鴿,“有觀其羽色和觀其形態兩類。觀賞羽色的,有全體潔白、頭部黑色的‘雪花;全體烏黑,頭部潔白的‘緇衣;全體潔白,頭尾烏黑的‘兩頭烏;全體黑白相間的‘喜鵲等。觀其形態的,有尾羽數多于一般鴿的兩倍、尾羽經常豎立似扇面的‘扇尾鴿,胸鼓氣囊鼓起如球的‘球胸鴿,眼周特別大的‘眼鏡鴿,鼻部蠟膜特別發達的‘瘤鼻鴿,以及能在地面或空中翻筋斗的‘筋斗鴿”(《娛樂小百科》)。
在北京觀賞鴿中,還有幾種受到人們的珍視,“鐵翅鳥”(黑鳥雙翅之大羽的二分之一為黑色者)、“玉環”(全身皆黑,只頸部有一圈白羽)、“墨環”(正好與“玉環”相反)、“三塊玉”(雙翅、尾為白色,余皆黑色)、“四塊玉”(頭、雙翅、尾為白色,余皆黑色)……除注重羽色之外,鴿子的頭、眼、嘴、足,也是有講究的。頭以額方頂圓若算盤珠者為佳。眼分金眼、葡萄眼、豆眼、隔楞眼,以金眼為優,而眼皮以白蠟色者為好。嘴以短陰陽嘴(上片嘴隨羽毛的顏色,下片嘴是白色)為珍。腿以肉紅色為佳,黑色者最差。
“講究養鴿者,都不養筋斗鴿,因為在飛翔時,有鴿子翻筋斗就亂了群。但也有專門養筋斗鴿的,一群這樣的鴿子,飛到高空,紛紛翻筋斗,也很有意思”(郭子舁《北京廟會舊俗》)。
小時候在古城湘潭,鄰居一戶人家喜歡養鴿子,而且喜歡給鴿子帶上哨。鴿子翱翔云天時,鴿哨發出嘹亮清脆之聲,十分動聽。
“鴿子哨是用竹筒、葦管、葫蘆等材料黏合而成。以哨的多少大小區分,有二簡、三聯、五聯、七星、九星、十一星、十三眼、三排、五排、眾星捧月、瀛洲學士、子母鈴等名目……鴿子哨用針別在鴿尾羽的根部,戴哨的鴿子也須經過訓練。一般鴿子只能戴二簡、三聯等小型鴿子哨。像眾星捧月、十三太保這類大型鴿子哨。只有體格健壯的鴿子才能戴得動”(《北京廟會舊俗》)。
“我昔斗雞徒”
在我國的少數民族地區,至今逢喜慶節日,斗雞的娛樂活動最能牽系人心,觀者如堵,只見“群雄正翕赫,雙翅自飛揚。揮羽激清風,悍目發朱光。嘴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傷。長鳴入青云,扇翼獨翱翔”(魏·曹丕《斗雞篇》),具有一種獨有的觀賞性。
我國的斗雞活動。最遲起始于東周、西周,在《莊子·達生篇》、《戰國策·齊策》等典籍中皆有記載。在漢代的石刻和畫像磚上,都有關于斗雞場面的描繪。南北朝時,斗雞之風亦盛,梁簡文帝在《斗雞》詩中說:“王冠初警敵,齊羽忽猜儔。”北周詩人王褒在《看斗雞》中寫出了當時的盛況:“入場疑挑戰,逐浪似追兵。”
斗雞活動到了唐代,掀起更大的波瀾,以唐玄宗為首的統治階層,沉溺于聲色犬馬之中,對斗雞格外青睞,長安大明宮、興慶宮之間建起了皇家的斗雞坊,并特意從禁軍子弟中選拔了五百少年負責飼養、培育、訓練斗雞。“上之好之,民風尤盛,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幣破產市雞,以嘗雞值。都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弄假雞”(唐·陳鴻《東城父老傳》)。五百少年的首領叫賈昌,其父賈忠是唐玄宗的衛士,他養雞、訓雞、斗雞很有一套,因而十分受寵,被稱之為“神雞童”,“生兒不用識文字,斗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輿。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陳鴻《神童雞謠》)。
即便是當時的著名文人,概莫能免俗,紛紛加入斗雞的行列。李白自稱:“我昔斗雞徒,連延五陵侯”(《敘舊贈江陵宰陸調》);張籍難抑一種自矜之情:“日日斗雞都市里,贏得寶刀重刻字”(《少年行》)。在一些文章中,而往往寫進“斗雞”的內容:“截冠雄雞,客雞也。……勇且善斗,家之六雄雞勿敢獨校焉”(李翱《截冠雄雞志》);“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羅隱《說天雞》)。
宋代斗雞活動依然興盛,并出現了專門的著作,如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中有斗雞專篇,如何選種,如何訓練,都有詳細介紹。如訓練之始,讓雞久立一草墩上,使其雙足穩定有力;喂食時將米高懸雞頭上令其咬啄,使雞脖勁豎、雞喙鋒利;常用瓴羽攪入雞喉,去其涎水,疏通腸胃,等等。
明代時,斗雞徒還成立了“斗雞社”之類的民間團體,交流經驗,舉辦賽事。明人張岱在《陶庵夢憶·斗雞社》中寫道:“天啟壬戌間好斗雞,設斗雞社于龍山下,仿王勃《斗雞檄》檄同社。仲叔秦一生,日攜古董、書畫、文錦、川扇等物與余搏,余雞屢勝之。仲叔憤懣,金其距,介其羽……又不勝。……”這種斗雞完全成了一種賭博的方式,在古代卻非常盛行,為了獲勝,不惜借助裝備與藥物刺激,如在翅膀上裝鐵片、撒芥粉,無所不用其極。
在清代,出現了一種叫“九斤黃”的良種斗雞,體大力足,兇猛耐斗。有個叫李聲振的人寫詩贊道:“紅冠空解斗千場,金距誰堪冠五坊?怪道木雞都不識,近人只愛九斤黃。”
在今天,斗雞活動一掃那些陳規陋習,提倡健康向上、平等競爭的精神,并成為旅游觀光的一項內容,因而頗受歡迎。
雀兒銜旗
明人田汝成在《禽戲》中寫道:“有日靈禽演劇者,其法以蠟嘴鳥作傀儡(原指木偶,此處指經過訓練能夠表演的雀兒),唱戲曲以導之,拜跪起立,儼若人狀。或使之銜旗而舞;或寫八卦名帖,指使銜之,縱橫不差;或拋彈空中,飛騰逐取。”從中可看出,當時馴化鳥雀用于表演,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
《紅樓夢》第三十六回中,曹雪芹則描寫了“麻雀銜旗”的景狀。賈薔花了一兩八錢銀子,買了只經過馴化的“玉頂金豆”麻雀來討齡官的歡心,“說著,便拿些谷子哄得那個雀兒在戲臺上亂串,銜鬼臉(小面具)、旗幟。”
馴化雀兒串戲臺、戴小面具、銜旗,必在雛雀羽未齊還不能起飛時開始,把它從窩里掏出來,用谷粒兒反復引逗、訓練。比如教雀兒戴小面具,先在面具后那個供鳥嘴叨銜的地方放上谷粒,它要吃到谷粒必須叨銜住面具,使它造成一種條件反射所形成的印象;然后,不放谷粒了,雀兒亦會叨起面具,完成表演后,再獎以谷粒,時間長了,便能熟練地完成這個程序。訓練雀兒銜旗的原理,也與之大同小異。
清代學者李聲振在《百戲竹枝詞》里,專有一首吟詠“麻雀銜旗”:“毀穴探雛飛去難,銜旗教得向籠樊。若還王母斑龍近,道是云中朱雀幡。”第一句寫捉取窩中還不能飛的雛雀,第二句寫馴化,最后兩句寫它銜旗的美麗姿態,十分形象生動。
這種馴化飛禽的“老玩意”,在我國的漢代已經開始,《西京雜記》中記載了當時茂陵有個文固陽。善于馴化野雉。唐代馴養飛禽用于表演則已很時興,《朝野金載》:“唐魏伶為西市丞,養一赤嘴鳥,每于人中乞錢。人取一文,而銜以送伶處,日收數百錢,時人號為魏丞鳥,”
北宋的著名科學家沈括,對于如何訓練鷓鴣開斗,是這樣說的:“嘗有人善調山鷓,使之斗,莫可與敵。人有得其術者,每食則以山鷓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見其鷓,則欲搏而食之。此以所養移其性也。”南宋周密在《武林舊事》中記述當時臨安(杭州)的勾欄瓦肆(表演、娛樂場所)及街巷之中,共有百戲伎藝三十余個門類,“教飛禽”即為此中之一,最有意思的節目是“烏鴉下棋”,在藝人的口令中,烏鴉分別銜起黑、白兩色棋子,依次按格擺到棋盤上。
明、清兩朝,“教飛禽”的表演水平達到高峰,雀兒可以跪拜起立、串戲臺、銜旗、口接飛彈,還可以表演出比較大的戲劇場面。《清稗類鈔》中就有生動描述,表演的共有六只蠟嘴鳥,其中四只各銜小面具戴上,飛上小戲臺,有如生、旦、凈、丑;另外一只,隨著觀者喊出《百家姓》上的姓氏,它便會隨聲在寫了字的紙牌堆里銜出這個字來;第六只鳥可以和三個觀眾一起玩一種“斗天九”的紙牌游戲,令人嘆為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