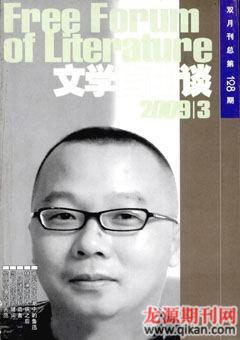令人搖頭的文壇“年度總結”
周景雷
一般來說,年終歲尾的各行各業(yè),都要做年度總結。一般的行文規(guī)范是先談成績、再談不足,找出存在的問題和指出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有時,這種年度總結雖然很有形式主義之嫌或者水分太多,但終歸有確切或不甚確切的統(tǒng)計數(shù)字,百分比、曲線圖、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一目了然。有熱鬧,也有科學,態(tài)度是頗為端正的。
不過文學是沒辦法做這種總結的,我們不能說今年出版了多少部長篇,比上一年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增加或者減少的比例是多少;也不能說今年的寫作者的平均年齡比上年減少了零點幾歲或者增加了零點幾歲。現(xiàn)在只要識字就能寫作,一夜之間就暴得大名;更不能說今年又出現(xiàn)了多少文學新面孔,或者有多少老面孔隱去,那樣容易產(chǎn)生新的矛盾。眼前就有現(xiàn)成的例子,北京大學一教授說從文學創(chuàng)作來說,2008年是個小年,一線代表作家諸如張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沒有推出作品,他們的空當期造成社會對文學界的關注不夠云云。結果一位作家就出來回應說此言大謬,并以自己當年已經(jīng)發(fā)表的作品給予反駁。
文壇上沒辦法做這種年度總結,不意味就無人做了。不知從何時起,批評家們給文壇做年度總結似乎已成風氣,而且其勢日熾。從前些年的幾個人在做,到現(xiàn)在的十幾個、幾十個人在做。這已經(jīng)成了很多文學類期刊、報紙的開年大戲。他們大都分總結某體裁一年的收獲,比如2008年短篇小說掃描、2008年長篇小說盤點、2008年散文收獲等等,大都談名家、談名作。這本無可厚非。但問題是這種具有明確工作總結意識的掃描、盤點、收獲卻是人言言殊,差別甚大。比如我最近讀到了兩篇總結2008年短篇小說的文章,里面都列舉了一大堆作品,細細讀來,發(fā)現(xiàn)兩者都提到的竟只有三兩篇。再順著這樣的線索找來其它的什么中篇小說、長篇小說、散文、詩歌等總結文章一讀,竟也都各說各話。于是我就疑惑了,實在是不知道如何通過閱讀這些文章來判斷中國的年度文壇了。
當然了,由于文學的特殊性,對它的評判標準因人而異(甚至有同一個批評家對同一個作品在不同的文章里有不同的評價),兩個人對同一文壇做年度總結出現(xiàn)差異是可以理解的,但文學的特殊性并不排斥文學的基本屬性,也就是說,差異似乎不應該超出一個專業(yè)讀者的想象。當下的批評家或者學者在做這種總結的時候,給人簡單的感覺就是,有的人在做總結的時候,本來因作品讀得不多就勉為其難,但又不能不做,于是讀過一個就算重要成果,大有隨意拈來之勢,沒準兒這里還有親朋好友的順水人情。不過也許還有另外的可能。連經(jīng)濟指標的統(tǒng)計數(shù)字都大有水分滲進,那么這種具有重大彈性空間的文壇年度總結任意拼湊就更沒什么了不起了。
一般來說,做這種年度盤點或總結一個最基本的工作是材料準備,而恰恰這又是最難做的。中國是個文學大國,近些年來,隨著各種媒體的迅速發(fā)展,越來越多的人深陷其中,用文學性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想象,并且有很多人迅速從中得到實惠,這種實惠再吸引更多人投入其中。我們不是常聽到這樣的對話嗎?我現(xiàn)在什么也干不了了,實在不行就寫小說去。可見文學創(chuàng)作是最容易從事的一種職業(yè),成本低,準備周期短,成名也較快。而且網(wǎng)絡的發(fā)達,會使這種快變得更快。龐大的創(chuàng)作隊伍和無以計數(shù)的創(chuàng)作數(shù)量使年終盤點變得越來越不可能。就紙質(zhì)媒體來說,現(xiàn)在每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有人說達到了一千五百部,有人說接近兩千部,總之還算可以估量。而那些散落在各種文學期刊、報紙上的中短篇小說、詩歌、散文,雖然最終也可能統(tǒng)計出來,但是能有人做到全部或者大部分都閱讀嗎?即使大部分都閱讀了,誰敢保證沒有遺珠之憾呢?有人說只要盯住了幾份大刊就基本能把握中國文壇。這倒是實話,只可惜幾份雜志的承載量畢竟有限,比如《人民文學》2008年全年刊發(fā)的小說是六十多篇(部),它們網(wǎng)羅的只是少數(shù)人,而且熟面孔較多。把他們看做整個當代中國文壇顯然不妥。應該說,這些人可能代表了中國文學的較高成就或者最高成就,但肯定代表不了文壇整個狀況。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在寫文章的時候,動輒從整個文壇的制高點來發(fā)表意見,說得道失,煞有介事。他們?yōu)槲膲傩牡男那槭强梢岳斫獾模麄儷@得結論的過程和依據(jù)是令人疑慮的,否則的話怎么會有評論家與作家之間的口水仗呢?這樣說來,是不是我們的文壇就不能做年度總結了?非也,我們的文壇需要潛心讀作品,靜心搞研究,誠心做總結的寫手,而不是嘩眾取寵之徒。
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文壇年度總結是在寫文學編年史論。這既不同于單純的文學編年或者像白燁先生主持的中國文情報告,也不同于對當年優(yōu)秀文學作品的個體研究,而是兩者的結合和延伸。既要關注到其中的優(yōu)秀者,也要注意到整體狀況和一般狀況。我們說魯迅等人是20世紀甚至直到今天的文學高峰,至少是基于兩種判斷,一是與世界文壇相比,二是與國內(nèi)文壇相比,正是基于這種比較,才顯出魯迅等人作為文學家的偉大。顯而易見,魯迅不代表整個中國文壇,而只是代表中國文壇的最高成就。茅盾早在七十多年前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在他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集的時候就設立了青年作家和無名作家專輯,力求以此表現(xiàn)出整個文壇狀況。不幸的是,這種精神現(xiàn)在似乎被遺忘了。遺忘的結果是,有人通過幾份年度總結就將整個文壇大而化之了,這實在是令人搖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