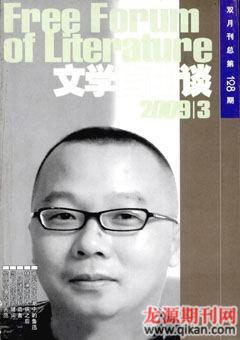批評在娛樂化之后……
譚旭東
今天,似乎沒有什么比娛樂更為理所當然,也似乎沒有什么比娛樂更為富有親和力和滲透力的了。電子媒介出現之后,娛樂成了電子文化的實質,大眾文化的狂歡與其說是自由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抬頭,不如說是娛樂主義的風行。文學藝術創作娛樂化了,學術娛樂化了,批評也娛樂化了。這讓人想起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對美國娛樂文化的嘲諷一樣,今天,“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文學創作娛樂化之后,我們看到了文學作品充斥著的是日常生活的敘事,充斥著的是小體驗、小情感、小感覺、小逗樂,文學內在的幽默和智慧也被油滑的調侃所替代,宏大敘事被解構成一堆堆支離破碎的個人小故事、小遭遇,苦難意識和悲劇色彩在作家筆下也成了一種故意渲染而騙取讀者廉價眼淚的小情節、小戲劇。而藝術娛樂化之后呢?繪畫和戲劇等似乎都變成了行為藝術,在浮淺和空泛的多元化表現之下,優美深沉的力量蕩然無存,充斥著的是混亂的色彩和無端的噱頭。于是,我們感嘆文學藝術精神的失落,我們懷念上個世紀80年代那段眾人都為美和思想而激動的歲月,我們期待又一個英雄時代的到來,期待文學藝術能再一次傳達主流的聲音,喚醒被喧嘩的市聲吵鬧得麻木的神經。學術娛樂化之后,學科的規范和學術的規范成了一紙空文,對經典的任意改編和對經典的調侃與惡搞,成了一種新的“學術行為”,學者不再是在圖書館和書房里潛心耕耘、沉思默想的思想家,而搖身一變為“電視文化名人”,大學三尺講臺已經容不下學者的欲望,“百家講壇”成了學者們趨之若鶩的舞臺,“學術超男”和“文化奶奶”今天成了很多人艷羨的對象。今天大學里的許多所謂的學者,最感興趣的不是在課堂上認真地傳道、授業、解惑。他們像過去農村里的生產隊長一樣,帶著二三十名碩士生、博士生,但他們不知道這些碩士生、博士生應該做些什么,或者說,他應該為這些學生做些什么;他們向往著出席各種學術會議,爭坐一把交椅;他們頻繁地參與各種學術事件,為各種學術交鋒演變成新聞事件而竭盡全力,甚至不擇手段;而且今天大學、研究所和社科院的學者熱心的不是學術創新,致力的不是學術的傳承,他們深知娛樂文化時代是“眼球經濟”時代,吸引眼球比吸引心靈更加能夠獲得廣泛認同,于是他們所孜孜不倦追求的是媒介的名聲和出名之后所擁有的巨大的商業利益,也就是說,學術娛樂化之后的今天,大學和研究機構熏陶的不是學術大師,而是制造學術明星,甚至是學術小丑。而學術明星們深諳布埃迪厄的社會文化理論,他們清楚地知道明星效應本身就意味著他們擁有了寶貴的“文化資本”,而且他們的“文化資本”可以隨時轉化為“商業資本”。
批評娛樂化之后呢?首先,批評的格局無疑發生了重大變化,學理性的批評,嚴肅的科學的批評已經退場,而代之以酷評、艷評和娛評,即學院批評不再是一種批評的中心力量,而媒介批評則中心化了。過去那些學院里的批評家們如今很少發出自己的聲音,一部分當然是出于無奈的心理,他們無法抵抗愈來愈娛樂化的批評形勢,只好成為學院里的縮頭烏龜,從此在批評界銷聲匿跡。這類人中有的聲稱是從“批評轉向學術”,似乎批評不是學術,而且學術比批評更為高檔,其實是批評家喪失了批評的勇氣,在真理面前失去了追求的信心,于是有意將批評“矮化”以求得心理上的自慰。還有一部分則是主動放棄批評的姿態和批評的話語,而是改變策略從事其他的所謂學術營生,比如,一些批評家改做泛文化研究,一些批評家則轉行到文學史研究,還有一些批評家轉而從事所謂跨學科研究。當然,也有一部分學院里的批評家則不甘寂寞,也勇于乘勢而上,他們抓住機遇,迅速而果斷地改變自己嚴肅的批評立場,投身于媒介娛樂化批評之列,且恨不得立刻分享到一份娛樂批評的美羹,如一些積極參與“80后”炒作的批評家和一些喜愛批名家、抖名家小料的批評家,還有一些熱衷于給作家排隊和積極參與各種小說、散文和詩歌排行榜,他們妥帖地與書商合謀在圖書市場上共享利益。從表象與聲勢來看,今天批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但仔細審視、辨別與傾聽,就不難發現與其說是批評進入到了“黃金時代”,不如說批評進入了無序時代,各種聲音可謂魚龍混雜,因為任何一種真誠的表達都可能被嘲諷為“矯情”。但有一點是清晰的,泛濫成災的是相對主義、犬儒主義和拜金主義。其次,批評的道德倫理已經岌岌可危。在批評娛樂化之后,批評已經沒有了美學標準,更沒有倫理底線,要說有標準和底線,那也是商業利益至上的標準和底線。無論是媒體批評,還是學院的批評,還是那些來自普通讀者的批評,甚至是那些職業的批評,都在試圖搶奪話語權,都在極力地謀求媒體形象和新聞效應,話語的倫理已經被市場利益所擊敗,文學理論批評不再是一群有道德教養的人的行為,而變成了一場“語言秀”,因為今天真正的文化英雄好像不再是那些孤獨的思想者,而是與市民合群的表演者。的確,翻開各種所謂的大眾文化媒介和理論批評刊物,批評和“超級女聲”一樣,變成了“想唱就唱”,“想秀就秀”,變成了“我是超女,我怕誰”。更不用說在一些學者和批評家的個人博客里,批評的言說和吐口水一樣容易而且比硫酸更具有殺傷力。
當然,批評娛樂化之后,也許會有新的聲音,也許會有另外的收獲,但批評娛樂化之后,至少在當下,批評已經變得面目全非、身份曖昧,而且失去了其應有的學術可信度和美的召喚力。文學藝術需要良性的生態環境,娛樂是文學藝術生成與發展的一個維度,但不是惟一選擇,而良性的文學生態環境意味著文學創作、文學理論批評和文學閱讀推廣等各個環節都應該是和諧推進的,而且批評在提升文學創作和引導閱讀推廣方面更要發揮自己的作用,因此診出批評娛樂化之后的種種病癥并以嚴肅的批評姿態、科學的方法和合理的范式來強化批評工作,是當下文學批評建設任務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