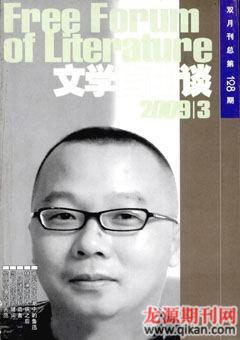警惕“朋友的新衣”
李 更 朱健國
李更:對(duì)提問者進(jìn)行提問是個(gè)困難的事,尤其是面對(duì)你這位高明的提問者,任何問題都可能顯得幼稚,我算是個(gè)了解你的人,但是越了解越不好提出問題,誰都知道朱健國是個(gè)麻煩的人,這個(gè)麻煩可以從兩個(gè)方面講,不怕遇到麻煩;喜歡找麻煩。能夠麻煩別人,就盡量麻煩別人;能夠麻煩自己,就盡量麻煩自己。因?yàn)槟愕膹?fù)雜,反而不知應(yīng)該提哪些問題,作為一個(gè)單純的采訪者,我想的就是在采訪中解釋麻煩,以便解決麻煩,同時(shí)自己要避免麻煩。不知道健國兄怎么看待自己?
朱健國:借用孟子的話,你是“善哉問也”,說得通俗而精辟,禮貌而詭異,我確乎一個(gè)極“麻煩的人”,非常挑剔。既麻煩自己,也麻煩別人,既麻煩權(quán)勢者,也麻煩弱勢者,既麻煩陌生人,也麻煩朋友。我有一句格言:將每一個(gè)朋友得罪(批評(píng))一次。其理論依據(jù)在于,既然每個(gè)人都必然有缺點(diǎn),為什么不能對(duì)每個(gè)人都童言無忌?其歷史借鑒在于魯迅先生。魯迅是得罪朋友的大師,胡適、林語堂、劉半農(nóng)都曾是他的好朋友,魯迅卻能毫無顧忌地尖銳批評(píng)他們。我覺得這是魯迅最可貴的地方。說實(shí)在話,得罪朋友比批評(píng)權(quán)勢者更需要膽識(shí)與學(xué)識(shí)。社會(huì)的病根往往在文化界,因此文化界朋友互當(dāng)諍友,是一種凈化社會(huì)的“防患于未然”。監(jiān)督社會(huì)應(yīng)該從監(jiān)督朋友開始。“朋友的新衣”比“皇帝的新衣”更難說。當(dāng)今中國,更缺少對(duì)“朋友的新衣”的警惕,許多人是寧可看著朋友裸游也不愿提醒對(duì)方的。
所以,我愿意做一個(gè)通過直言“朋友的新衣”揭露“皇帝的新衣”的“陽光小孩”。我想,如若每個(gè)人都能提醒朋友,我們的社會(huì)一定會(huì)正氣浩然。當(dāng)然,這種監(jiān)督并非包括朋友的隱私與生活,而限于與公眾利益相關(guān)的大事。
我之所以如此“麻煩”,因?yàn)槲覍?duì)自己的人生定位是:“偽現(xiàn)代化”研究發(fā)起者、“共生主義”探索者、雜文作家。前面兩個(gè)臉譜是近十年得到的,“雜文家”的帽子有20年了。一般來說,“雜文家”都是要得罪人的,但“新基調(diào)雜文家”只得罪非主流的一方,“公民寫作雜文家”只按政府解釋的憲法批評(píng)錯(cuò)誤者。魯迅風(fēng)雜文則有些“為在野黨諱”。我是以研究“偽現(xiàn)代化”和“共生主義”為基礎(chǔ)的“雜文作家”,“偽現(xiàn)代化”是一種言行背道而馳的謊言社會(huì),“共生主義”反對(duì)任何名義的暴力,主張沒有敵人,只有病人,一切違反宇宙共生規(guī)律的現(xiàn)象皆在批判之列。因此,我這個(gè)“雜文家”與傳統(tǒng)的諸多“雜文家”不一樣,我的批判范圍要更大更廣,我要通過批評(píng)一切反共生的問題而促進(jìn)人類共生,萬物共生。可以說,沒有人不在我的批評(píng)視野之內(nèi),包括我自己。我是一個(gè)“四面樹敵”(其實(shí)是四面懸壺濟(jì)世)的人。
近十年我的經(jīng)典麻煩有“四大筆仗”,這“四大筆仗”的對(duì)象,有兩個(gè)曾經(jīng)是朋友。
李更:我想,還是來談?wù)勀愕脑L談吧,從1996年開始,你把自己的文字重心很大程度上放到了訪問各種各樣文化、政要名人上,你是想代人立言呢?還是通過別人的嘴巴說自己的思想?
朱健國:我向來主張“六經(jīng)注我”,“借他人酒杯澆自身塊壘”,我手寫我心。
1995年我在任職《中華讀書報(bào)》深圳記者站站長時(shí),開始了寫作轉(zhuǎn)向:從原來寫雜文為主,轉(zhuǎn)向?qū)懭宋镌L談為主。十多年來大約采訪了三百多人,采訪對(duì)象以文化界為主,施蟄存、王元化、蔡尚思、王蒙、方方、池莉等著名學(xué)者、作家,兼及政界改革者、商界爭議人物和底層草根代表人物,如李銳、任仲夷、袁庚、牟其中、史鐵柱、楊劍昌、安子等。由于我有采訪后再沉淀一段時(shí)間的習(xí)慣,約有三分之一的采訪至今還未能定稿。
我做人物訪談,實(shí)際上是為我的“偽現(xiàn)代化”研究做系列調(diào)查和個(gè)案研究。就像黃宗羲通過做《明儒學(xué)案》——對(duì)明代學(xué)人學(xué)術(shù)歷程一個(gè)一個(gè)的梳理概括評(píng)述,根據(jù)“一本而萬殊”的學(xué)術(shù)史觀,對(duì)明代理學(xué)思想的發(fā)展歷史做了總結(jié)。我則是通過對(duì)人物當(dāng)面采訪加上事后資料搜集,力圖紀(jì)錄“偽現(xiàn)代化學(xué)案”,展示“偽現(xiàn)代化”大潮中各種文化政治商業(yè)人士的淪陷與掙扎,借此呼吁共生哲學(xué)。
李更:反正我是在對(duì)受訪者有好感時(shí)才去采訪對(duì)方的,當(dāng)然,首先是要對(duì)受訪者有極大興趣時(shí)才能有問題想問。幫助別人擴(kuò)散影響,其實(shí)就是一個(gè)普通采訪者的基本想法,既然這樣,那么肯定是要以受訪者完事以后感到高興為前提的,可我知道你不是這樣的采訪者,為什么?
朱健國:多數(shù)情況下,我也是在對(duì)受訪者有好感時(shí)才去采訪,但也有不少是因?yàn)椴稍L對(duì)象具有獨(dú)特的歷史與現(xiàn)實(shí)意義,雖然并不贊同其言行,我也仍然以極大興趣去采訪。比如1998年底我采訪牟其中,并非因?yàn)橄矚g他,而是對(duì)其獨(dú)特理念與實(shí)踐深感興趣,覺得是一個(gè)偽現(xiàn)代化的難得標(biāo)本。
這樣你就可明白,何以我的人物訪談,不能像大陸有些記者學(xué)人的人物訪談風(fēng)平浪靜?這與我獨(dú)特的人物訪談理念有關(guān),我做人物訪談?dòng)辛?xiàng)原則——
1、訪談的目的不是為了美化、頌揚(yáng)、討好受訪人,而是為了探求歷史真相、追求人間真理,因此,訪談稿是在對(duì)歷史負(fù)責(zé)的前提下尊重受訪人,如遇與對(duì)歷史負(fù)責(zé)有沖突之處,將不以受訪人及其追隨者滿意為準(zhǔn),訪談稿將竭力為存歷史真相而保留不利于受訪人和采訪者的原始材料(這一原則深受袁庚等智者的贊同,但遇到一些以為采訪者必以受訪人之是非為是非的人,就難免發(fā)生爭執(zhí))。
2、為了切實(shí)做到“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凡訪談必公開錄音、照相,甚至錄像,據(jù)此整理出訪談稿,盡力原汁原味地保持受訪人的回憶情節(jié)及語言風(fēng)格。我深信再好的記憶力,也頂不上錄音機(jī),包括受訪人,事后也須以現(xiàn)場錄音為準(zhǔn),而不能以受訪人自居而隨意否定現(xiàn)場錄音——受訪人可以事后改變意見,但不能否認(rèn)曾有的現(xiàn)場錄音之真實(shí)性。
3、依據(jù)國際新聞采訪慣例,“新聞采訪稿無須經(jīng)受訪人審閱,文責(zé)自負(fù)”,對(duì)于受訪人沒有要求事后須審閱的訪談稿,或本人沒有承諾送受訪人審查的訪談稿,一般不給受訪人審讀。經(jīng)驗(yàn)證明,訪談稿送受訪人審訂,雖可以避免極個(gè)別的詞語誤聽誤會(huì),或進(jìn)一步擴(kuò)展意見之便,但卻可能使受訪人刪除一些非常重要的歷史真相和深刻而敏感的思想閃光。因?yàn)樵賯ゴ蟮娜嗽诮邮懿稍L時(shí),也總有一種趨利避諱美化自己宣揚(yáng)自己的潛意識(shí),這一“自我保護(hù)”在訪談時(shí)會(huì)因情緒高漲有所放松,情不自禁流露出許多常態(tài)下掩飾著的真情和潛意識(shí),而到審稿時(shí),則在高度“理性”下加倍強(qiáng)化“自我保護(hù)”,不惜刪改一些真相真情真思想。
4、我的人物訪談一律是對(duì)話互動(dòng),不是只紀(jì)錄受訪人一人之說的“單口歷史”(因此與純粹的“口述歷史”采訪規(guī)則有所不同)。雖然訪談稿中多是受訪人主講,但主導(dǎo)訪談的是采訪者——不同的采訪者訪問同一個(gè)受訪人,因訪談目標(biāo)不同、問題不同、傾向不同而會(huì)得到不同的訪談稿——所以,訪談稿具有采訪者深刻的個(gè)性,其版權(quán)完全屬于采訪者——受訪人接受采訪者的采訪,就是將自己的談話授權(quán)給采訪者傳播。須知,沒有經(jīng)過錄音或文字紀(jì)錄的談話,是沒有版權(quán)的。
5、因訪談稿版權(quán)完全屬于采訪者,特殊情況下(如因時(shí)間緊張采訪者在現(xiàn)場將時(shí)間讓與受訪人多說話),采訪者有權(quán)在事后整理文字時(shí),對(duì)自己的某些“縮寫對(duì)話”酌情作一些不改變意思、語氣和語境的精確恢復(fù)或延伸,以便讓受訪人的話語得到更清晰的解讀或注釋。
6、除特殊情況,我的訪談稿一般不及時(shí)公布,多在數(shù)年后選擇時(shí)機(jī)傳播。這樣有兩個(gè)好處,一是有充足的時(shí)間反復(fù)核對(duì)原始資料,查證相關(guān)背景;二是“好鋼用在刀刃上”,讓對(duì)歷史負(fù)責(zé)的訪談稿在最具影響力的時(shí)機(jī)“以一當(dāng)十”;同時(shí)也可在時(shí)間檢驗(yàn)中淘汰一些歷史價(jià)值不大的訪談稿。所以,我至今仍有許多已有十來年歷史的訪談稿未發(fā)表,如關(guān)于蔡尚思先生的三十萬字長篇訪談。
以上六條“人物訪談原則”,并非隨心所欲而定,而是依據(jù)法拉奇、唐德剛和國際文化界關(guān)于人物訪談及人物傳記的寫作通例而形成。特別是存在主義哲學(xué)大師薩特和親密五十年的女友波伏娃相互爭議采訪者文章的故事,更令我堅(jiān)信自己的人物訪談原則。薩特晚年時(shí),其秘書本尼·列維(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領(lǐng)袖)將與他的對(duì)話寫成人物訪談《今天的希望》,薩特和波伏娃的朋友紛紛試圖阻止該文發(fā)表,因?yàn)槠渲姓鎸?shí)地透露,薩特對(duì)自己的哲學(xué)令人心碎的自我批評(píng)。作者堅(jiān)持將文章面世后,波伏娃憤怒地哭泣,四處指責(zé)本尼·列維是在利用薩特老年的思維衰退進(jìn)行欺騙。反過來,波伏娃在薩特死后出版了《告別儀式》一書,講述她的“靈魂伴侶”薩特身體上的衰弱,但遭到薩特的晚年情人阿萊特的刺骨批評(píng),說薩特曾批評(píng)波伏娃回憶薩特的文章是“像對(duì)待一個(gè)死人那樣,對(duì)待一個(gè)不方便自我表達(dá)的人”。由此可見,真實(shí)的人物訪談常常會(huì)因敏感問題引起包括受訪者在內(nèi)的不滿。
李更:你的采訪,影響越來越大,正面的影響自然是越大越好,負(fù)面的呢?對(duì)你的訪談,反映是兩個(gè)極端,贊揚(yáng)者說超好,詆毀者說惡毒,甚至有些被采訪者覺得很生氣,后果當(dāng)然很嚴(yán)重了。你是不是特別喜歡哪壺不開提哪壺?如果有記者對(duì)你也這樣,你會(huì)高興嗎?
朱健國:我在寫人物訪談時(shí),追求的不是影響,不是外界的評(píng)價(jià),而是自己的快樂。選擇采訪對(duì)象都是自己有興趣的人,所以我在寫作中得到極大的快樂。外界的贊揚(yáng)和詆毀,包括受訪者的評(píng)價(jià),對(duì)我都影響不大。我從來不認(rèn)為真理的標(biāo)準(zhǔn)都在受訪者那里。由于“偽現(xiàn)代化”研究是我發(fā)起獨(dú)創(chuàng),“共生主義”理論研究雖然有幾個(gè)人在做,但真正密切聯(lián)系實(shí)際研究“共生問題”,我是第一個(gè)探索者,所以我認(rèn)為最能評(píng)判我的人物訪談的,只有歷史。它的真正價(jià)值,要等到幾十年后才能為大眾所接受。
我的一些人物訪談之所以有些影響力,可能因?yàn)樗x人物多與歷史重大事件相關(guān),我又比較善于挖掘受訪者不太愿說的一些敏感問題。如采訪任仲夷時(shí),我挖出了他開始不想說的一些內(nèi)容。但后來他還是稱贊了我。能夠讓受訪者說出只對(duì)你一人說的話,這是一種采訪技巧。
至于有人對(duì)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會(huì)像任仲夷老人一樣,始而遮掩,繼而贊揚(yáng)。
李更:你聯(lián)系訪談對(duì)象時(shí)被拒絕的時(shí)候多嗎?訪問以后成為朋友的多嗎?
朱健國:還沒有遇到拒絕的情況。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在采訪后成為朋友或相安無事。只有極少數(shù)以為采訪者必須歌頌受訪者或必須以受訪者之是非為是非的人,才會(huì)對(duì)我的訪問有極大意見。但我相信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他們最終還是會(huì)感謝我如實(shí)地紀(jì)錄了他們的思想狀態(tài)。
像袁庚,十一年來我多次采訪他,前幾年發(fā)表他批評(píng)巴老的直言時(shí),使他受到強(qiáng)大攻擊,有人為此專門在書中用一章節(jié)反諷袁庚,可以說給他帶來很大麻煩。但袁老仍然樂意再接受我的采訪,前幾天又同意我再去訪談。每年春節(jié),袁老還主動(dòng)打電話問候。任仲夷讀了我寫他的訪談后,稱為是最有深度的訪談,又推薦我去采訪他的朋友黃大夫。其孫子任意去年還在美國請(qǐng)我吃飯,代表家庭謝我。還有雷宇、嚴(yán)秀、牧惠、余杰等,都是多次接受我訪問。從目前來看,贊揚(yáng)者和認(rèn)可者居多。
再比如你,我們是朋友,但在關(guān)于你父親(責(zé)編注:李更的父親李建綱系原湖北作家協(xié)會(huì)負(fù)責(zé)人)和你朋友的文學(xué)評(píng)述上,我就因堅(jiān)持己見而讓你難受。好在你像許多真正有境界的朋友一樣,最終還是能理解我、寬容我。我對(duì)一些為尊者諱,為朋友諱的人是很擔(dān)憂的,他既然能“為朋友諱”,那惡人就可通過其朋友來讓他“為惡人諱”。這種只對(duì)陌生者鐵面無私的人,必然不可能事事公正,堅(jiān)持正義。
李更:我有個(gè)觀點(diǎn),只要對(duì)世界具有挑剔的眼光,你就可以當(dāng)雜文家了,挑剔得越厲害,你的名氣就越大。在中國雜文界,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你的,你是個(gè)過于挑剔的人嗎?
朱健國:不挑剔的人是當(dāng)不了雜文家的。《雜文選刊》主編劉成信評(píng)論我說:“魯迅之后有聶紺弩,聶紺弩之后有邵燕祥,邵燕祥之后是朱健國。”這可能就是說我屬于善于“挑剔”的一家之言,意在鞭策鼓勵(lì)我。但我自信,在當(dāng)代中青年雜文家中,我顯然是一個(gè)另類:我有自己獨(dú)立的思想,既非傳統(tǒng)內(nèi)容,又不是時(shí)髦的貨色,而是以研究“偽現(xiàn)代化”中的“共生問題”為獨(dú)特視角。特別是我的通過直言“朋友的新衣”揭露“皇帝的新衣”的批評(píng)路徑,這是一般人不會(huì)選擇的路。
李更:雜文家是不是思想家?雜文的性質(zhì)是“雜”還是“罵”?
朱健國:真正的雜文大家必須是思想家和文學(xué)家的完美結(jié)合。缺一不可。
我曾在《文學(xué)自由談》上發(fā)表過《20世紀(jì)中國雜文真相隨想》,其中對(duì)雜文的定義是——
雜文的本質(zhì)是反代圣人立言,我手寫我心的獨(dú)立思想。這種獨(dú)立思想,純粹是一種對(duì)人性、對(duì)社會(huì)的獨(dú)立思考。而這種獨(dú)立思想又以短小精悍、文采斐然、生動(dòng)活潑而區(qū)別于學(xué)術(shù)與文學(xué)的其它體裁。
在和顯學(xué)之外獨(dú)立自由地思想、批判(并非一定就是正確就是真理),沖破一切壓制、阻礙,曲折隱晦勇敢藝術(shù)地表達(dá)發(fā)表,這就是中國現(xiàn)代雜文的本質(zhì)和標(biāo)準(zhǔn)。
李更:一個(gè)人寫一篇雜文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寫雜文,而雜文總是要批評(píng)的,沒有誰會(huì)心甘情愿地接受批評(píng)。你批評(píng)的對(duì)象越多,朋友就越少,你會(huì)因此感覺生存的空間越來越小嗎?會(huì)不會(huì)由此而影響自己的生活質(zhì)量?你的雜文有多少篇多少字了?
朱健國:在沒有網(wǎng)絡(luò)之前,最好的雜文和最差的雜文都發(fā)表不了。有了網(wǎng)絡(luò)以后,最差的雜文都可以發(fā)表了,但最好的雜文仍然很難發(fā)表。因此,我的最好的雜文,一直關(guān)在電腦和柜子中,但我仍然每年要寫一些只供自己高興的雜文。因?yàn)槲业碾s文的第一功能和目的是讓自己快樂。盡管這種快樂常常是“痛并快樂著”。
我沒有統(tǒng)計(jì)過自己寫了多少篇雜文。一個(gè)雜文家,如果能有一篇好雜文真正流傳后世,就是天大的幸運(yùn)了。我爭取能給后世留下一篇雜文。這是我的雜文努力目標(biāo)。目前我的雜文有《改寫葉喬波》比較受歡迎。
我不以雜文發(fā)表多少為快樂,也不以為朋友多就是成功的標(biāo)志。我以為一個(gè)人思維空間和影響空間大于他人,一個(gè)人的歷史影響長于他人,這才是成功的標(biāo)志。人與人的高低在于思想影響的時(shí)空大小長短。
從歷史上看,好像思想影響的時(shí)空大而長的人,通常都是特別孤獨(dú)的。
李更:隨便問個(gè)問題,因?yàn)槟恪⑽液哇沉疑蕉际俏錆h來廣東的,都是寫雜文的,大家都是老朋友,你和老鄢還是幾十年的交情,你們兩位交惡,我和朋友們非常痛心,希望你們停止上演《投名狀》,你認(rèn)為有和解的可能嗎?
朱健國:我和鄢烈山的分裂與論戰(zhàn),是時(shí)代變化的縮影。詳情你都曉得,就不講了吧。
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雙方意氣平靜,理性地回到學(xué)術(shù)爭鳴上,我想是可以求同存異的。人間沒有什么化解不了的誤會(huì)與冤仇,何況我還是個(gè)“共生主義”者。
我常常提醒“朋友沒有穿新衣”,是真誠地希望朋友真有新衣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