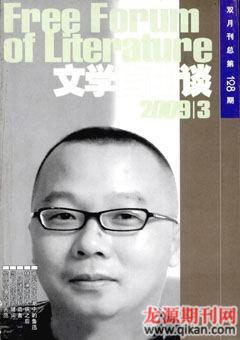五十年前的一次“欺騙”
高 深
《天津文學(xué)》在上個(gè)世紀(jì)50年代叫《新港》。
1958年我與這個(gè)刊物打過一次交道,記憶中留下了某種“欺騙”的嫌疑,其實(shí)我主觀上并沒有欺騙的意圖,只是想打個(gè)“馬虎眼”,不料陰差陽錯(cuò),弄成了一種事實(shí)上的“欺騙”。為此,我?guī)缀踉诎雮€(gè)世紀(jì)里慚愧不已。
1952年我開始發(fā)表詩歌習(xí)作,1956年出席了全國第一次青年創(chuàng)作者大會(huì)。像后來文壇上的一些風(fēng)云人物王蒙、鄧友梅、流沙河、劉紹裳、從維熙、白樺等,都是那次會(huì)議的代表。我從“青創(chuàng)會(huì)”歸來,出現(xiàn)過一個(gè)寫作的“高峰期”,詩歌、小說、特寫(即現(xiàn)在的報(bào)告文學(xué))、散文、雜文,什么都寫。尤其又長了“第三只眼”,學(xué)會(huì)了觀察與比較,多了一些作家的社會(huì)責(zé)任感,寫過一些干預(yù)生活的作品。
1957年黨內(nèi)開展整風(fēng)運(yùn)動(dòng),可是剛剛整了一個(gè)頭,大概是有些人的意見太認(rèn)真、太動(dòng)情,因此顯出了恨鐵不成鋼的激烈,用有些人的話來說,不夠“和風(fēng)細(xì)雨”,或是缺了一點(diǎn)拐彎抹角,太直白了,于是整個(gè)中國在“一篇社論”的引領(lǐng)下,億萬人民心領(lǐng)神會(huì),使整風(fēng)運(yùn)動(dòng)順其自然地轉(zhuǎn)向了反擊右派的斗爭。
在整風(fēng)階段里,我參加過幾次文學(xué)界的鳴放會(huì)議,也在《沈陽日報(bào)》等報(bào)刊上寫過幾篇鳴放文章。說老實(shí)話,我那時(shí)候的思想是偏“左”的,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視為“文藝憲法”,發(fā)言、寫文章從不跑調(diào)兒,更不會(huì)發(fā)表可以拼成“右派言論”的意見,反右斗爭開始時(shí),我還寫了若干首斗爭鋒芒很強(qiáng)的“反擊右派”的詩歌、散文。
我出身革命干部家庭,11歲(l946年)就參加了東北民主聯(lián)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zhàn)軍的前身),反右之初還是積極分子。所以我的親人、戰(zhàn)友、朋友,誰也不曾想到我會(huì)被打成右派。但是我與單位的一把手走得不近,處得不是很和諧,其實(shí)也沒有什么實(shí)質(zhì)性的分歧,只是我給他提過兩次意見,僅僅是意見而已,連批評都夠不上,加上我寫過一些批評官僚主義、溜須拍馬和“風(fēng)派”的諷刺詩,那年頭,只這兩點(diǎn),給你扣一個(gè)“反黨、反社會(huì)主義”的帽子已經(jīng)綽綽有余了。簡而言之,我在反右運(yùn)動(dòng)后期被打成“右派分子”。
戴帽以后,把我下放到沈陽第三機(jī)床廠翻砂車間勞動(dòng)改造。翻砂車間最苦最累最臟的活是打箱、除砂。這活不需要什么技術(shù),有力氣就行。那年我才23歲,年輕,身體好,有力氣,加上人家工人也沒覺著干這種活就是改造,就是懲罰,所以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屈辱。只是工資拿掉了大半,無權(quán)寫作也沒有稿費(fèi)收入,一時(shí)“經(jīng)濟(jì)形勢”有些危機(jī)。
曾經(jīng)有幾個(gè)來往密切的詩友,一度還成立了一個(gè)“竹園詩社”,幾個(gè)人經(jīng)常在一起切磋詩歌創(chuàng)作,也議論家事、國事、天下事,可以說彼此無話不談。我一向以“老革命”自居,動(dòng)不動(dòng)就批評他們的“錯(cuò)誤思想”,他們嘲諷我是“竹園詩社”的“指導(dǎo)員”、“政委”。我被打成右派后,他們吃驚之余誰也不曾認(rèn)同。組織上勸告他們要與我劃清界線,最好不要來往。他們說,我們相處這么多年,無話不談,從沒聽他說過不利于黨的話,他倒是時(shí)不時(shí)地批評我們的“自由主義”,“無組織無紀(jì)律”等。有一個(gè)詩友就因?yàn)椴徽J(rèn)同我是右派,竟然被下放到沈陽郊區(qū)豬耳屯勞動(dòng)一年。
我被打成右派以后,幾位詩友不但沒有離我而去,反而越發(fā)親近,跟我來往得更勤了。他們說:“你現(xiàn)在更需要友誼,更需要精神上的理解與支持。”我反右前寫的一些尚未發(fā)表的詩,已經(jīng)無法發(fā)表了,詩友們就用他們的名字發(fā)表,有一首長詩《伏在云端的巖石上——寫給母親的信》,還在1958年第三期的《北方》上發(fā)了頭條。
詩友們對我的理解與關(guān)愛,使我雖身陷敵我矛盾的邊緣,心中卻仍有一線同志的光明與溫暖。有一個(gè)星期天與詩友們分手后,激動(dòng)不已,信手寫了一首《忠實(shí)的朋友》。我在詩中假托一個(gè)有了“過失”的青年,不但沒有遭到朋友們的拋棄,反倒獲得更多的友誼與關(guān)愛。過了幾天,我把《忠實(shí)的朋友》與另外兩首詩寄給了《新港》,不敢署“高深”這個(gè)名字,署了一個(gè)假名“竹人”,意思是“兩個(gè)人”。信箋上只寫了“寄上組詩《忠實(shí)的朋友》,請編輯同志不吝指正!”信封下方總要寫上寄信人的地址,我未加思考就寫上“沈陽市鐵西區(qū)沈陽第三機(jī)床廠翻砂車間”。當(dāng)我把裝著稿件的信封投進(jìn)郵筒的那一瞬間,比我1952年2月有生第一次投稿時(shí)還膽戰(zhàn)心驚,好像是做了賊似的。
三月的沈陽,春意并不怎么濃郁,北墻根還有成堆成片未融化的殘雪。我猜不出這組詩歌的命運(yùn),也不知道它將給我?guī)淼氖堑溸€是福,往日投稿的快樂與自信已蕩然無存。
稿子寄出去一個(gè)多月了,常去廠收發(fā)室看信,結(jié)果是“詩”沉大海,音信杳無,看來十有八九是不會(huì)采用了。其實(shí)詩寄出后我就有些后悔,怕有人說不老老實(shí)實(shí)接受改造,成名成家的資產(chǎn)階級思想還沒有批倒批臭。所以安慰自己:不發(fā)表也好,免得露了餡,再挨批斗。
大約在5月中旬,我意外地收到兩本當(dāng)月的《新港》,《忠實(shí)的朋友》發(fā)表了,還是詩歌欄的頭題。令我大吃一驚、出了一身冷汗的是,在作者“竹人”的前面,居然署了“工人”二字。右派分子用假名發(fā)表作品,還冒充工人,這可是非同小可。可是我沒有勇氣給《新港》編輯寫信說明真相。有十來天,每天我都提心吊膽,惟恐什么人找我談話。總有一種“做賊心虛”的感覺,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寢食不安。
整個(gè)5月和6月,每一天都像一年那么漫長,我真正嘗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不過好像沒有人發(fā)現(xiàn)什么,《新港》編輯部一定是根據(jù)投稿人的地址才加上“工人”的,刊出后并沒有什么人提出異議,因?yàn)椴痪梦揖驮趥鬟_(dá)室“截獲”了寄給“竹人”的稿酬。顯然廠子里并沒有人發(fā)覺“竹人”就是右派分子高深。
沒有發(fā)生曾經(jīng)預(yù)料的不幸,竟成了一種無形的鼓勵(lì),過了兩個(gè)月,我蠢蠢欲動(dòng),又想化名竹人再給《新港》寄一組詩歌。就在這時(shí),我在一位詩友那兒看見了1958年第三期的《文學(xué)研究》(即雙月刊《文學(xué)評論》的前身),這本權(quán)威性的評論刊物刊載了老詩人力揚(yáng)的一篇文章:《生氣蓬勃的工人詩歌創(chuàng)作》,文中用很長一段文字評論了“工人竹人”的詩《忠實(shí)的朋友》,不僅給予很高的評價(jià),還幾乎引了詩的全文。讀了力揚(yáng)的文章,我立馬又嚇出一身冷汗,這一回“右派分子冒充工人詩人”已成了鐵案,使我又回到那些惴惴不安打發(fā)光陰的日子,走在路上,總覺著有人在背后戳我的脊梁:他就是冒充‘工人詩人的右派分子!惶惶不可終日,比剛戴上“右派”帽子時(shí)還恐懼。
從此在摘帽之前,我再也沒有膽量化名投稿了。今天想起這件事情,覺得當(dāng)時(shí)的《新港》編輯既有眼力又很正派,一個(gè)文壇無名的“竹人”,不經(jīng)任何人介紹,也沒有任何關(guān)系,不但采用了稿子,且置于頭題地位發(fā)表。力揚(yáng)是我崇拜的為數(shù)不多的老詩人之一,他的長詩《射虎者及其家族》,我曾反復(fù)拜讀,不失為新詩的經(jīng)典。他給予《忠實(shí)的朋友》那么高的贊譽(yù),足以說明《新港》編者的慧眼。時(shí)隔50多年后的今天,想起此事,仍然對《新港》編輯部肅然起敬,欽佩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