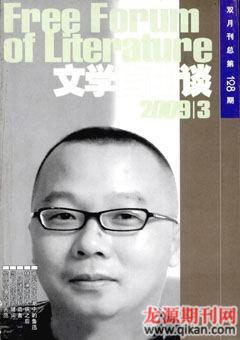浮詞艷句滿江湖
程耀愷
《百城賦》是北京一家報紙推出的新欄目,開初的幾篇,雖有雕章琢句之嫌,還算是珠玉紛呈,尚能一時娛人之耳目。于是,仿制之作排闥而來,一時間,浮詞艷句滿江湖。
幾年前,我曾漂泊于長城內(nèi)外,大江南北,最大的收獲,便是閱城無數(shù)。按理,經(jīng)多應當見廣才是,其實并非如此。經(jīng)過大拆大建之后,無論哪座城,無非政務區(qū)、開發(fā)區(qū)、CBD、會展中心、大學城,無非主題公園、景觀大道、人文廣場,無非一環(huán)、二環(huán)、三環(huán)、內(nèi)環(huán)、外環(huán),無非高架橋、高樓廣廈、歐風美雨。并美齊肩的同時,千城一面也。
千城一面既成事實,所缺者,千篇一律也。
現(xiàn)在有了:東城賦、西城賦、南城賦、北城賦……
短短一年之中,那么多的“城賦”聯(lián)袂而出,自然引人注目,《散文選刊》曾一舉推出六篇,我也另外找來十幾篇,認真研讀,但愈讀愈激動不起來,愈讀愈覺得茫然。這批大賦,擺家譜,晾舊衣,爭三皇,奪五帝,歌功德,頌政績,售華辭,呈才氣,在玄虛繁冗中,輾轉(zhuǎn)盤旋,于浮光掠影間,極盡大吹大擂之能事,什么“臨廣場而懷古,撫地標而抒懷”;什么“天公獨眷,四美俱全”,不一而足。夸飾倒不是大礙,致命的一點,便是缺失穿透堂奧之目光、指歸縱深之睿智。雖然也有人說這批《城賦》“今人之文采,時代之氣象,盡顯其中”,但我的總體印象卻是:沒有生活,沒有細節(jié),沒有激情,沒有思辨,沒有萬家哀樂,沒有心智的成熟和精神的超脫,只有語詞的堆砌,只有文字的狂歡,一言以蔽之: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賦是一種介于詩文之間、以夸張鋪陳為特征、以狀物為主功能的文體,曾是漢代文學的主流與正宗。無疑,漢賦是中國文學一塊閃光的里程碑,但它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像《子虛賦》、《上林賦》這樣的傳世名作,也難免帶有夸張失實、文字艱深、羅列過度、呆板滯重的胎記。漢賦之末流,漸漸失去文學性,淪為一種文字游戲。蘇軾雖然對賦有再造之功,也不過在他多樣化風格的文體之中,聊為一格而已。
賦這一古老的文體,能不能為今人所用?對此,前人有言:文章之事,不特籍山川之助,亦賴一時人物之玉成也。當今天下,如果能有突破賦體散文呆滯的形式與結(jié)構(gòu),寫出《前赤壁賦》的蘇軾那樣的人物,當然是好事,如果沒有,反不如老老實實寫一點現(xiàn)代人喜聞樂見的文章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