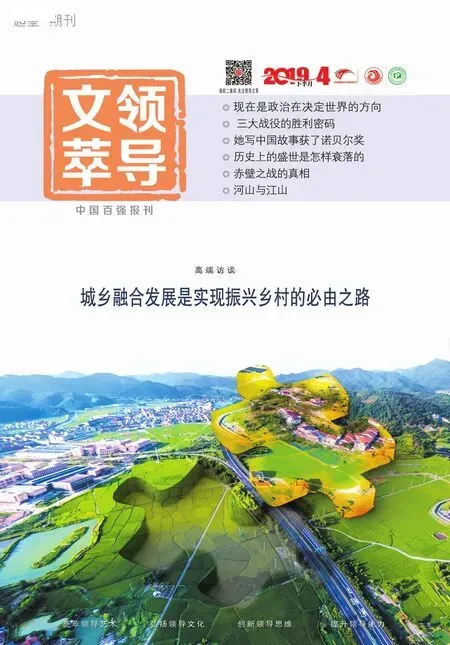科學認識和發展可再生能源
馮 冰
可再生能源——老事物、新話題
從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來看,到目前為止,人類所依賴的主導能源經歷了從可再生能源(以薪柴為主)向煤炭替換,然后又向石油、天然氣替換的三個階段。一般而言,可再生能源包括多種能源產品,如水力、風能、太陽能(熱和光電)、生物質能、潮汐和地熱等,是人類利用最早也是利用時間最長的能源。“鉆木取火”使人類先祖擺脫了“茹毛飲血”的蒙頓,開啟了人類的文明。在隨后漫長的歲月里,人類砍柴、燒灶煮飯、燒柴取暖,成為人類社會經濟存在和發展所賴以為生的主導能源,維持了人類社會幾千年的農業文明。人們借“風”揚帆、漂洋過海,擴大了世界交流;太陽光更是孕育了萬物眾生;“水”車也早已用在了我國農田灌溉和早期的英國紡織業。在化石能源大規模開發利用前的漫長歲月中,可再生能源一直是絕對的主導能源。
隨著第一次產業革命的興起,世界開始進入工業化為主導的社會。在工業大生產條件下,傳統利用方式上的森林能源無論是在能量密集度,還是熱值上都難以適應工業大生產所需要的能量要求。與傳統利用方式上的森林能源相比,常規化石能源能夠大規模開采和集中供應,其價格也相對低廉,能夠更有效地支撐工業大生產以及與之相伴生的現代消費方式。除了一些水電項目得以發展外,絕大部分可再生能源逐漸失去競爭力,常規化石能源開始替代可再生能源,成為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的主導能源。
當前,常規化石能源正日益耗竭,刺激其價格不斷攀升;常規化石能源的利用還給自然環境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國家已經或開始制訂其新的能源發展戰略,以可再生能源(包括森林能源)來替代常規化石能源是其中的重要內容。我國也于2005年2月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并且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對可再生能源發展提出了具體目標。可再生能源這個伴隨人類社會漫長發展歷程的傳統能源,又擺上世界當前和未來能源發展的重要議程,被賦予了新的歷史使命。
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意義
可再生能源的資源潛力是非常巨大的,僅據太陽能、風能、水能和生物質能粗略估計,在現有科學技術水平下,一年可以獲得的資源量即達87億噸標準煤,完全可以滿足人類社會的需要。據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等國際機構預測,到本世紀下半葉,可再生能源將逐漸取代傳統化石能源而占據主導地位。
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等各個領域發展速度的加快,能源需求正逐年增加。到2020年我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國內生產總值(GDP)比2000年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即使在充分考慮技術進步、經濟結構調整、采取多種政策措施實現有效節能的前提下,能源需求量也將達到25億-33億噸標準煤,我國面臨能源緊張與儲量不足的壓力。因此,發展可再生能源,實現可再生能源的永續利用將會全面提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能力。其意義在于:
一是我國緩解資源瓶頸性約束的根本出路。預計2050年我國能源需求也將超過50億噸標準煤,而國內常規化石能源的供應能力只有30億左右噸標準煤,能源供需矛盾缺口達20億噸標準煤。由于石油的進口依存度將超過50%,能源供應安全也將面臨極大的挑戰。而我國可再生能源不僅資源儲量豐富,而且大多屬于低碳或非碳能源,具有可再生性,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是緩解我國資源瓶頸性約束、保障能源安全的必由之路。
二是我國減少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的重要途徑。我國能源消費結構中的70%來自煤炭,而煤炭燃燒所產生的粉塵、SO2、NOx等污染物又占到其總量的70%~90%,造成了嚴重的大氣污染。大氣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已相當于GDP的2%~3%,每年超過1000億元;化石燃料消費形成的CO2排放,還是造成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可再生能源對環境的污染要小得多。水電、風電、太陽能等幾乎沒有污染物的排放。生物質能利用不會增加大氣中的碳排放量,粉塵、SO2、NOx等地方和區域大氣污染物的排放也很少。沼氣不但可以解決農村能源短缺,保護生態環境,而且可以減少農藥、化肥的污染,促進農業生態環境。因此,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是從根本上解決地方、區域和全球大氣環境污染問題,改善生態環境的必然選擇。
三是為我國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農業生產力的提高、農村的全面發展以及農民的增收一直是我國在“三農”領域高度關注的問題。近些年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愈來愈受到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的制約。發展可再生能源將成為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進步和環境改善的有效手段。首先,開發和利用再生能源是解決農村基本用電和基本用能的重要途徑。例如,利用小型光伏發電系統以及離網發電系統供電是解決常規電網難以覆蓋的邊遠農村地區用電問題的主要方式。農村被動式太陽房、沼氣池等成為解決農村生活用能的重要手段。其次,在農村地區發展生物質發電技術,積極推廣能源、環境、經濟效益相結合的農村可再生能源綜合利用模式,是提高農業生產力、增加農民收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保護農村生態環境的有效途徑。
四是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選擇。我國西部地區不僅常規能源資源豐富,而且可再生能源資源如太陽能、風能、地熱等也非常豐富。有效挖掘西部地區的資源優勢,發展可再生能源將成為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性途徑。它不僅可以緩解西部邊遠地區能源短缺,而且還將改變西部地區的傳統能源消費模式和生活習慣,改善生態環境,提高生活質量,促進西部地區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
五是有利于我國發展循環經濟,建立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循環經濟是一種最大限度地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經濟發展模式。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主要目標,實現資源的多次合理利用和對環境的有效保護,成為建設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根本途徑。可再生能源是資源消耗和廢物排放非常少的清潔能源,符合循環經濟這種“資源獲取——生產——消費——再生”的生態學規律,因此,建立以可再生能源為資源載體的循環經濟模式以發展可持續能源體系,將是我國未來在“經濟和環境”雙重約束下的最佳選擇。
六是有助于提高我國的國際能源地位和綜合競爭力。一方面,我國能源總量的資源稟賦在國際上位居前列,但是能源的人均資源稟賦卻不占優勢。另一方面,我國是CO2排放的大國,隨著發達國家減排承諾的履行,我國在未來國際談判中也將會面臨更大壓力。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在產業鏈低端的出口產品仍占較高比例。同時,盡管國際關稅壁壘逐步降低,但包括產品能效和環境標準、標識、廢棄物回收、包裝等“綠色壁壘”的非關稅壁壘日益凸顯。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我國的綜合競爭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將有力提高我國的總體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費強度和出口產品成本,確立我國的能源國際地位,對全面提升我國的綜合競爭力更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把握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時代特征
可再生能源盡管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和巨大的意義,但是,可再生能源的現代化利用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要再次變成世界主導能源,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目前,我國理論界和實踐界對發展可再生能源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混亂。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既要反對常規化石能源主導的慣性思維,對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持簡單否定的態度;又要反對盲目樂觀,認為可再生能源會輕易地、一勞永逸地解決人類社會發展所面臨的能源問題,更不能借“吹捧”可再生能源之名行獲取某種特殊政策之實。從歷史與邏輯相統一來看,可再生能源利用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這意味著當前和未來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會展現鮮明的時代特征,我們要科學、理性地認識和發展可再生能源。
當前,相對常規化石能源而言,可再生能源往往被認為是新能源,但水能、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長久以來就被人類利用,又何新之有呢? “新”總是相對“舊”、相對傳統而言的。要將可再生能源與新能源相聯系,必須從“體”和“用”兩個層次上理解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產品構成了新能源的“體”,是新能源的主要實體對象,利用方式則構成了新能源的“用”。可再生能源產品作為自然界天然存在的物質,并不存在新與舊的問題,而利用方式才存在新與舊之分。因此,“用”的“新”才是新能源的本質規定,當前的所謂新能源無非是“新鍋煮老湯”。傳統農耕社會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方式,往往是零散、隨機、不連續和低效率的,也不考慮環境問題,而作為新能源的可再生能源,其利用是建立在工業化大生產的基礎上。
工業化大生產的特點是規模化、技術化、裝備化、市場化和集中化,當前和未來時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也必須體現工業化大生產上述基本特點。與傳統意義上的零星燃燒相對比,規模化意味著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需要大規模、大批量的加工處理;與傳統意義上的簡單、粗放相比,技術化意味著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要依靠技術進步和相對復雜的工藝過程進行深加工處理;與傳統意義上的直接利用相比,裝備化意味著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需要借助比較復雜的,能夠進行各種物理、化學處理的機器設備;與傳統意義上的自給自足為主導相比,市場化意味著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需要更多地借助市場力量,出現可再生能源生產的細化分工,其收集、加工、配送、使用等環節主要借助市場交換來實現;與傳統意義上的分散利用相比,集中化意味著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往往是在比較集中的地點、時間,連續地進行加工和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