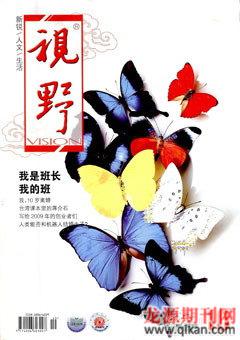達爾文不務正業的大學生活
王道還
今年是達爾文誕辰200周年,也是他的《物種起源》出版150周年。在西方,這本書不但是現代演化生物學的開山之作,還因為涉及認識“人性”的基本觀點,而產生了巨大的人文沖擊。難怪達爾文大概是西方科學史家研究得最透徹的一個人物。
不過,我們聽熟了“不要輸在起跑點上”,即使對達爾文的科學成就與影響不感興趣,翻閱他的傳記也會感到耳目一新。原來達爾文在27歲之前,并無志向。他家境好,父親雖是醫師,真正的賺錢本領卻是投資與放貸。達爾文遵父命入愛丁堡大學習醫,卻因為知道自己會繼承豐厚的遺產,無意在學業上下苦功。混了兩年后,父親怕他沒出息,送他到劍橋大學念神學,好將來當英國國教的牧師。三年后,他通過考試畢業,但成績并不出眾。那時他已22歲了。
達爾文晚年,在為子女寫的自傳中,回顧自己接受的學校教育,完全沒有好話:劍橋那三年,我在課業上花的時間完全浪費了。與在愛丁堡大學、中學的情況完全一樣。
其實,這不只是達爾文一個人的看法;到了現在,這句話仍能引起不少人共鳴。然而,達爾文對大學里的正式課業失望,并不表示他上大學的那五年全自費了。例如達爾文在大學里參加了學術性社團,他第一篇生物研究報告,就是在愛丁堡大學的學生社團中宣讀的。他還在愛丁堡花錢學會了剝制鳥類標本的技術。到了劍橋,達爾文結識了植物學教授韓斯洛。韓斯洛學識廣博,地質學、田野生物學都有造詣;每星期五晚上邀請教師與學生到家里分享見聞,達爾文是常客。而植物學與他的學位考試毫無關系。達爾文畢業后,通過韓斯洛的推薦,隨著英國海軍小獵犬號到南美洲測量海岸,歷時近五年。繞地球一周。他一路搜集的生物標本,以及地質學觀察,由韓斯洛安排發表,為他贏得了英倫科學界的尊敬。達爾文因而確定了一生的志向:研究自然史的核心問題,即生物演化。父親這才放心,不再擔心他沒出患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上大學是對人生的重大投資。只有少數人畢業后依賴上課時記下來的知識謀生,大部分人的謀生本領必須到職場現學現賣。大學提供的是機會,有各種課程讓人磨煉學習能力,建立信心;有各色人等,磨煉社交能力,建立人脈。
達爾文充分利用了上大學得到的機會。他對在劍橋的日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當年那股搜集甲蟲的狂熱。他挑出34只甲蟲與一只蛾寄給倫敦一位昆蟲學家。那位專家將其中幾種登在《不列顛昆蟲圖錄》中,注明“由達爾文君采集”。達爾文終于承認:我在劍橋那三年,可以說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日子。那時的我身體好,總是朝氣蓬勃。
愿人人都有這么美好的大學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