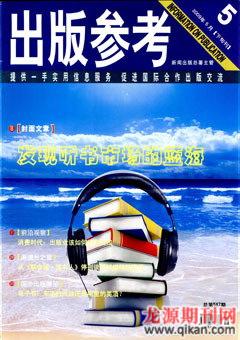消費時代:出版業該如何紀念五四
孟紹勇
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滄桑之后,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個倡導“文化消費”的時代,出版紀念五四,一方面要穿越歷史的風塵,引導人們觸摸五四真正的精神內核,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只有回到當下的社會語境,五四才能在人們的閱讀中復活,并凸顯出它本應有的意義。
無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五四愛國民主運動,都不是孤立的歷史事件,它們與晚清維新運動所提供的思想資源和文化資源息息相關。在先進的政治思想和科學文化知識傳播的過程中,出版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原富》、《法意》等西洋學術名著,林譯小說,周氏兄弟合譯的《域外小說集》等作品的出版,讓中國知識界第一次看到了西方學術,文學的真實面目,傳統的觀念就此被打破,社會改良和變革的呼聲也越發強烈。
之后的十余年中,圍繞啟蒙與救亡的主題,出版責無旁貸地承擔了思想先鋒的重任。一方面,《新青年》、《新潮》、《國民》、《每周評論》、《晨報》、《星期評論》、《少年中國》、《覺悟》、《建設》等一大批進步報刊集中出現,成為五四期間宣傳“德先生”和“賽先生”的重要陣地,直接推動了五四運動的發生、發展,另一方面,先進的知識分子與進步的出版機構合作,不斷推出足以影響一個時代的書籍。如在新文學領域,胡適的《嘗試集》(1920)由東亞圖書館出版,郭沫若的《女神》(1921)、郁達夫的《沉淪》(1921)、聞一多的《紅燭》(1923)由泰東書局出版,周作人的《自己的園地》(1923)由晨報社出版,冰心的《繁星》(1923)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外,文學研究會出版了“文學研究會叢書”、“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文學周報叢書”,創造社出版了“創造叢書”,新文學的成果得以被及時總結和鞏固。
五四的影響還在繼續,出版界也會源源不斷地推出與五四有關的書籍。但和上世紀建國后的多數時期不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出版對于五四的關注也必然出現新的變化。概括起來,當下出版關注五四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繼續挖掘五四在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意義,探討五四的豐富性和多側面性,其目的在于豐富學術界對于五四的研究,真實地展示五四對于中國知識界的符號意義;二是發揮出版的文化傳承功能,總結和研究五四倡導民主和科學的理念,古為今用,進而探討從“賽先生”到“科教興國”的可能性,并從中尋找可資借鑒的啟示;三是承續五四的思想啟蒙任務,在新的時期進一步發揮出版“開啟民智”的巨大功能,進行新一輪的思想解放,為全面提高國民素質、民族文化振興貢獻力量;四是在文化消費時代,面對眾多消費文化的沖擊,倡導嚴肅的、純正的民族文化,警惕和抵御文化游戲主義傾向,為民族進步確立全新的核心價值標尺。
應該說,這四個方面代表了今天出版關注五四的主要目的。尤其是后兩個方面,對當下中國社會的發展顯得尤為重要。中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的發展中國家,思想啟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五四的思想啟蒙僅僅是完成了一個階段的任務,對于一個欲走向世界的大國來說,從五四一代思想啟蒙的努力中吸取養分并提高全民族的素質,是出版的核心任務之一。而在當代文化格局中,警惕和抵御文化消費主義傾向,倡導純正的民族文化,對出版而言不僅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更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以文學出版為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些出版社受市場風氣的影響,開始推出一批以倡導大眾文化為核心的作品,這些作品貌似貼近當下生活,尤其以描寫燈紅酒綠的城市青年人生活而被人關注,然而在當代中國,這些作品中反映的生活不僅不具有普遍性,更有夸大和戲謔化之嫌,在它們出版之初就受到了讀者的質疑。更為嚴重的是,近幾年在文化消費主義的沖擊下,一些文學經典也遭遇了被解構的命運,“戲說”或者“新說”正在成為一種時髦的創作手段。
在理想主義被一代人無情放逐的時候,出版顯然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要追問的是,到底出版在無處不在的市場面前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是否從一開始出版就充當了某種思想傾向的導演?因此,出版紀念五四,要更多地著眼于當下的社會現實。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五四的精神依然彌足珍貴,但同時正越來越受到消費化傾向的威脅。出版只有自覺地提高警惕,才可能正確地面對自身的生存困境,并進而面對整個民族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