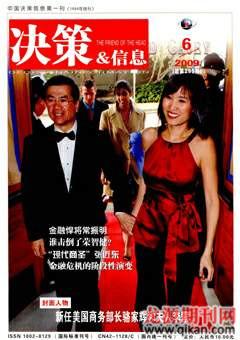政府“減副”面面觀
紀 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機構改革已進行了多次,但各地領導職數配備,特別是地方政府副市長、助理、副秘書長的職數配備,卻一直反反復復,有的嚴重超標,長期得不到解決。
終頒“減副令”
今年1月12日中組部、中編辦下發《關于規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書長配備問題的通知》,這個《通知》就是中央對官場發出的“減副令”。
中央“減副令”的主要內容是:一、省級政府原則上不配備省長(主席、市長)助理,省級以下政府不配備助理。今后,個別省級政府因工作特殊,需要配備助理的,有關省(區、市)黨委須事先報中央組織部統一研究同意后,再按有關程序辦理。二、省級、副省級、地市級政府副秘書長應根據工作需要明確職數,并嚴格按規定職數配備,配備職級要按有關規定執行。縣級政府不設秘書長、副秘書長職位。三、地方政府已配備助理的,配備副秘書長過多的,有關省(區、市)應妥善調整,在2年內予以消化,其中已達到退休年齡的應盡快辦理免職手續。中組部和中編辦將對落實情況適時督促檢查。
冗員密集
今年4月21日,吉林省政府在全國第一個履行“減副”,免去6位省政府副秘書長的職務。
對于中央這道“減副令”,地方政府不情愿,也并不積極。比如,吉林省政府這次的“瘦身”行動,首先是“根據中央巡視組意見”,也就是說,盡管中央下達了“減副令”,倘若不是及時的下去督促檢查,也不會這么快見到行動。從中央文件到地方執行等待了3個多月,個別地方對中央“減副令”置之不理,仍然我行我素。
雖然吉林省率先一次免去6位省政府副秘書長的職務,但仍有10名副秘書長在職,原來,一個省竟然可以同時擁有16位省政府副秘書長!然而,更有甚者,河南省新鄉市有11個副市長、16個副秘書長和6個調研員;只有300多萬人口的遼寧鐵嶺市,有9個副市長、20個副秘書長;河南鄲城縣公安局領導班子多達16人,超過了公安部,鄲城縣政府辦公室有主任1名,副主任9名,主任科員8名,副主任科員3名,從一把手一直排到21把手,該縣副職達到6名以上的單位,至少有8個;湖南省石門縣委常委16名,副縣長11名;湖南省平江縣有10個副縣長、4個縣長助理。這么多的正官與副官開起會來都不易,如何分工更加難。
“副職”為何多?
一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不少地方,黨政“一把手”輪換猶如“走馬燈”,新官上任后總要任用一批自己信得過的人,在班子編制足額或者已經超編的情況下,往往采取“先進后出”的辦法,增加副職職數,可原來的副職又沒有足夠理由讓他們下去,久而久之便導致本級政府副職積壓。而且,一些主政官員為了將個人權力發揮到極致,控制要害部門,還采取明升暗降的辦法,讓那些自己信不過的部門“一把手”到本級黨委、政府擔任副秘書長什么的,清理門戶,安插親信,從而導致下屬機關副職“聚堆”。君不聞,“要想富,動干部”,“萬里江山萬里塵,一朝天子一朝臣”,對干部過度頻繁調整,不但導致冗員增多,還會滋生吏治腐敗。
二是“唯官是貴,因人設事”。中國自古“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許多人都把獲取權力看成個人成就的重要標識,在唯官是貴的怪圈內,權力被資本化、利益化,提拔被當成調動干部積極因素的不二法門,一些黨委、政府習慣于把副職當作福利待遇,用來安撫干部,于是便因人設事、因人置官。按照黨的干部路線,本應能上庸下,優勝劣汰,能官能民,能進能出,但在一些地方卻很難做到,干部提拔往往論資排輩,“胡子拉碴排隊等提拔”的現象屢見不鮮。一些冗員為了顯示自身工作的重要性,搞出各種各樣的評比、檢查、攤派活動,助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大行其道,人民負擔加重,形成“魚大水淺”的不和諧狀況。
三是“管事太多,庸人自擾”。現在一些地方政府職能太廣,事無巨細,管事太多,由于政府自身改革不到位,?很多應該還給社會組織的權力依然掌控在手中。在許多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的確忙得不亦樂乎,但由于“公共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個人化?”,這些地方并不愿分解和下放權力,盡管中央三令五申強調“減副”,但那些干部所負擔的職責并沒有減掉,很難達到預期目標。
四是“頻繁調動,助長買官賣官”。近年來,一些地方官員調動過于頻繁、任職難以屆滿的現象比較普遍。主要官員隨意無序的流動,不僅誘發了執政理念短期化、執政行為浮躁化、執政政績泡沫化等問題,也破壞了正常的職務晉升規則,助長了“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現象的蔓延。在北京一些基層,不少民眾反映,現在有的官員到一個地方任職,基本“一年看,二年干,三年等著換”,甚至有的一上任就活動著如何離開,沒把多少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更不管冗員排成隊,有事沒事干。
五是“機構編制缺乏剛性約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主要領導的一句話、一個招呼、一個條子,就可以把有關政策法規拋到一邊,以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使黨的許多好政策在一些地方發揮不了作用。實際情況正如中組部原部長張全景所說:“事實上,由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構筑的制度基本上是健全的,但如果束之高閣,就成了一紙空文。”按照科學的方法應該是制度管人,任何人都沒有超越法律法規的特權。但在一些地方的實踐中卻是本末倒置、權大于法,不是制度管人,而是人管制度。
危害無窮
政令不暢。中央對基層黨政機關領導班子的職數配備,有著具體而明確的規定,地方黨委政府擅自超規模配備領導職數,明顯違反了中央規定。這種現象長期存在,說明黨政機關陽逢陰違、政令不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很嚴重,損害了中央權威。
人浮于事。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形象地說明人浮于事的嚴重性。領導職數配置過多,必然導致崗位職責不明、工作效率低下的機關病滋生蔓延,背離了精干高效的原則。“月亮比星星多”造成的后果是:指手劃腳、發號施令的人多了,腳踏實地、埋頭苦干的人少了,無事生非多了,扯皮拉筋多了。河南省鄲城縣直某單位開會時因主席臺位置有限,領導的座位牌沒有全部擺上,結果引起某領導不滿,當場拂袖而去,會議不歡而散。
增加負擔。領導班子職數超規模配備,必然帶來相應的經濟待遇和其他諸如公車配備等福利待遇的問題,而且相互攀比、爭權奪利在所難免,政府財政支出因此增加,加重了公眾的負擔。
滋生腐敗。超編配備領導職數,為一些心術不正的領導干部“批發紗帽”創造了條件。諸如招商引資獎勵等都可以成為超職數配備的因素,就增加了領導干部配備上的隨意性,洞開了賣官鬻爵、滋生腐敗的方便之門。有多少領導干部就是藉著“照顧”的名義,而進入了官員序列。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甚至一些地方的學校里也出現了“副校級領導干部”這一讓人前所未聞、啼笑皆非的官位。
中組部啟動“減副”,減的只是官位職數、頭銜而不是官員人數,無助于裁減庸官冗員及機構精簡瘦身。被減者只消改個官銜,譬如“副省級巡視員”、“正廳級調查員”,仍可繼續為官一方,或者“轉跑道”由人大政協安排消化。欲加官職,何患無名,副秘少了,助理沒了,其他名目的職位就應運而生,一雞死,一雞鳴。
如何“瘦身”
“副職”膨脹使近年機構改革成效付之東流,衙門瘦身打回原形,皇糧愈吃愈多,財政不堪負荷。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在今年政協大會透露,1979年內地在編官員約為290萬人,近年吃財政飯的總人數已高達4500多萬人。另有數據顯示,中國的官民比例在唐朝時為1比3900,明朝為1比2900,近年的官民比例已達到1比26。
據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王健介紹,判定公務員適度規模的經濟指標應該是——公務員人數與本國GDP的比例。公務員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了多大的作用,需要以單位GDP的公務員人數來衡量。雖然現在我國財政供養人員占總人口的“官民比例”只有1比2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從經濟視角考察,財政供養人員與GDP之比看,我國為39人/百萬美元,大大高于發達國家,目前美國為2.31人/百萬美元,日本為1.38人/百萬美元。我國公務員“超標”近20倍。
這是同“發達”國家比較的倍數,那么,我們同發展中國家相比又若何?就拿印度來說,他們全國公務員才八千多人,他們的一個鄉級政府公務員才1—2人……我們呢?據2005年網上調查,中國最基層的鄉鎮黨政機關包括黨政辦、財政所、經管站、農業辦、計生辦、招商辦、土地所、林業站、農技站、司法所、統計站、水利站、農機站、文化廣播站、民政辦、社會保障所、司法調解中心、團委、婦聯、武裝部、信訪辦等等,鄉鎮工作人員達到上百人,平均每個縣財政供養人口1.5萬人。那么要是“逐級”往上統計呢?
自中組部和中編辦發出《通知》后,今年4月,貴州全省就已經開始規范市、縣、鄉三級政府副職問題,明文規定“市級政府副秘書長的配備不得超過同級政府副職職數限額,縣級政府辦公室副主任的配備嚴格控制在規定職數范圍內”。廣東省政府機構改革方案規定,全省將在2010年實行機構編制實名制,已經得到黨中央、國務院批準。4月23日,湖北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機構改革動員大會,全省將通過2個月左右的時間,順利完成新老機構的工作職責交替、領導班子組建、人員流轉。武漢市政府機構改革與省政府機構改革基本同步進行。在全省原有的52個省直機構中,7個部門不再保留。經過改革后,共設置工作部門42個,重點加強了信息化與工業化的結合。在推行大部門的同時,還將推進大處室機制,原則上處室人員一般不少于6人。
在中組部的堅決要求下,全國兩年內會完成“減副”任務,但減副不減員,政府怎能“瘦身”?精簡機構,減副又減員,肯定觸犯某些官員利益,產生阻力。然而,這是建立廉潔高效政府,深化改革,加快發展所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