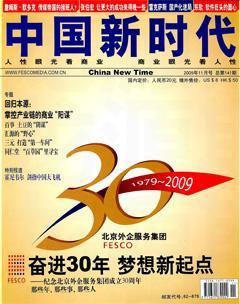趙群“兩種制度”下的外企人
總有一些人的命運是和歷史的發條捆在一起的。在FESCO麾下成長的老員工,他們的經歷不單與FESCO的命運與共,同時也印記著中國對外開放這段歷史的軌跡
80年代的中國,北京某玻璃廠。
辦公室里,幾個工程師模樣的人正背著手來回徘徊,時不時地停下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卻仍是相顧無言,一籌莫展。
事情源于幾個月前,廠里要購買一批燒玻璃的耐火磚。相對于普通的磚,這種磚使用的材質必須能耐住幾千度的高溫,并且需保證永久不變形、無氣味。而在當時,這種制作工藝國內還生產不了,必須進口。玻璃廠便向國外的廠家下了訂單,訂了幾集裝箱的一級耐火磚。沒過多長時間,貨到了,可打開集裝箱一看,拉來的卻是三級耐火磚,一下子就降低了好幾個檔次。
這讓玻璃廠的人可傻眼了——想退貨,可國內連生產能力都沒有,哪來的檢測標準。沒有檢測標準,又如何去證明貨不對板呢?外商也知道,中國當時沒有能力做平板玻璃,三級耐火磚也夠用了。
如何不讓外商鉆這個空子?這可難壞了玻璃廠的工程師們。
不退貨?白白浪費了幾十萬美金,在80年代的中國,幾十萬美金可以說是“天價”啊:退貨?合同上白紙黑字地寫明,發現不合格。要在多少天內進行索賠,而且索賠標準包括對不合格的貨品必須出具具體數據來證明。“如何寫這個數據呢?”工程師們為此在辦公室里急得團團轉。
這時候,門悄悄地開了,一個小伙子大步流星地走了進來,扒在其中一個工程師的耳邊輕聲說了幾句,工程師頓時茅塞頓開,喜上眉梢。
“別在這兒耽誤工夫了。隨便寫一個數據,先報上去,反正外貿人員也看不懂,還需要時間來找他們的技術人員鑒定,到時候具體事宜再商量。咱先把時間趕上,如果過了索賠期,再想爭得權利就沒辦法了。”
剛剛進來的這個小伙子就是當時被北京外國企業服務總公司(前FESCO)外派到日本三菱集團明和產業株式會社的首席代表——趙群。
結緣FESCO
明和產業株式會社是日本三菱集團屬下的商社,一開始以化工產品為中心。“明和產業是比較民主的公司,1949年解放前就和三一企業有著貿易往來。”趙群告訴記者, “之前,被派去的幾個員工和外商關系搞得都不是很好,不能很好的完成公司的期待值。”這時候,時任北京外企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代總經理孫揚先找到了正在北京外事辦做秘書工作的趙群,希望他能夠加入FESCO,接替這個工作。
1984年5月,趙群被正式外派到明和產業株式會社。在到崗之前,他常常在心底悄悄地叮囑自己:不要忘記孫總的囑托:“你去那里作為一個契機,雙方關系一定要搞好。”果然,由于趙群的踏實肯干,日方對他很滿意。在明和產業,趙群起初擔任化工科科長,接觸了很多藥品以及生物科學方面的知識,而這也為他日后的職業發展奠定了基礎;之后他又升為北京事務所的首席代表,秘書長、重慶事務所的首席代表,最后干脆去了日本總公司做顧問,從被日本人管理到后來管理日本人,他這一干就是15年。
說起趙群和FESCO的淵源,代總經理孫揚先是個不得不提的人物。
1982年的《北京科技報》上有篇報道,講述的就是他與孫揚先之間的不解之緣。
當時的趙群還是北京職工大學的學生,在這期間,他又上了北京科技進修學院,一邊學習科技一邊學習日語,每天的學習生活緊張而又忙碌。這天,他照例拿著寫滿日語單詞的小紙條在路上全神貫注地背著。這時候迎面過來一騎自行車的人,連叫了幾聲他都沒有聽見,趙群被撞倒后,騎車人連忙起身,查看他有沒有受傷,哪想到,被撞倒在路邊的趙群連動都沒有動,手里拿著小紙條干脆躺在那里,嘴里振振有詞地繼續讀著,這讓騎車人很是驚奇。而這位騎車人,就是孫揚先。
現在看來,雙方是否真是因此結緣還有待考證,不過,趙群勤奮好學的事跡確是千真萬確的,這點從當年的《北京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其他報道中便可見一斑。
進入明和產業之后,對趙群來說是個很大的鍛煉。按照常理推斷,一個有志氣的青年,是不愿意被束縛的,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他卻甘愿被“束縛”,并且被“束縛”了15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怪的現象。
“因為我看到了這種‘束縛’對自己,對前途,對國家都有幫助、有好處。”趙群侃侃而談,“當時接觸到日本人的工作方式,覺得它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我們應該學習的。那時候給我的感觸很深,我覺得應該忍耐這個過程,然后把日本人對待工作的這種精神變成一種實在的機制,從而來改變當時中國企業散亂的管理現狀。”
1984年年底,進入明和產業半年后的趙群被派往日本研修,回來以后,他上交了一份長達27頁的匯報,內容涵蓋了日本當時的社會環境、機制、法律、企業管理等方方面面。“里面說的都是自己的心里話。”這份報告,讓他覺得很自豪。“我作為FESCO的一員,能夠和日本人在一起工作,把有價值的東西提供給國家,還是很高興的。”
在“兩種制度”下生活
80年代中期,有上百家外國商社落戶北京,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公司。當時不少中國人是在尚未放下“8年抗日”這個情感重負的情況下,不得不面對日本商人的。
30年后的今天我們可以說,1979年FESCO的適時誕生,為國家改革開放助了一臂之力,而且是特殊的一臂之力。這一點肯定是“功不可沒”的,但是當初人們卻沒有這么明確的認識,也來不及形成這樣明確的認識。
“在當時的背景下。擺在員工面前的有很多問題,我們不像在國營企業,僅僅考慮到好好工作,如何晉升就完了,還要在兩個不同的社會背景。不同的機制下,找到平衡、找到生存點。”趙群語重心長地說。
當時被外派到外國商社的這些員工,有人稱他們是“中方雇員”,也有人調侃他們是一幫專門為“老外”干活的“洋買辦”。中方雇員一腳踏入外國商社也跟外國商人一腳踏入中國土地一樣,雙方都是“腳踏兩只船”,社會制度的不同,價值觀念的不同,“計劃”與“市場”不同,“主人翁”與“受雇者”身份不同……這一系列的不同,一方面帶給中方雇員的是行為做法上的不習慣,另外一方面,更沉重的是內心的矛盾與痛苦。
“端著‘老外’的飯碗就應該為‘老外’奔走。每次在談判桌上,當雙方的利益得不到平衡時,作為一名中國人,出于血緣因素,自然偏心于自己的同胞。而作為外國公司的雇員。此時又必須為自己公司的利益盡力拼爭。最殘忍的是,有時在談判桌上,我們要坐在自己的同胞對面,看著同胞出于某種更急需的考慮,不得不向外商低頭的時候,而自己卻幫不上忙。”
生意場上買賣成交的先決條件是雙方達到共贏。可是誰獲利大,誰獲利小,這里還是有差別的。趙群感嘆:“我們沒辦法做到在一筆買賣中,只讓中國人獲利或者保證使中方獲大利。在當時,有時候中國人吃了虧還不知道,有時候明明知道吃了虧也沒辦法。”
每一份的得失都在這些中國雇員的心中秤來秤去。一方面自己是中國人,當然不能胳膊肘往外拐,但同時又是外國公司的雇員,不維護公司利益也無異于缺少職業道德。“改革開放的初期,幾乎每個中國雇員的心中都有著這樣一桿秤,有人曾經形象地說,中國雇員是在兩種體制下生活。”但求平衡
盡管有萬般無奈,但中國經濟要擺脫自己游離于國際經濟傳統與現代秩序的鄉俗鄉習,就必須克服這些無奈,從起步的時候就規范自己的一言一行,才能逐漸與世界對話。
這種自我修煉式的約束是痛苦的,可必須有人承擔和垂范。趙群說,“當時FESCO給我的教育是,要注意平衡,既要維護外商的利益,也要維護國家的基本利益。不要為了區區幾美金的報價差,就因小失大,要站在兩者的宏觀利益上看問題。”
懷念起當年,趙群感嘆,“看著國家蒙受損失,我心疼,但是作為長遠來看,這點小痛必須要忍耐。外國人來中國是做生意的,而中國就是要通過這種生意往來,來提高我們自己的能力,素質,提高貿易往來中對問題的控制能力。作為FESCO的成員,在當時的背景下,我們不應該沒有原則地追求貿易平衡。純粹的貿易平衡,在還沒有加入WTO的情況下,無疑是實現不了的。”
事實上,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這些外國商社的中方雇員恰恰是在不斷克服自己習慣,行為、觀念上的諸多不適應,才恰如其分地扮演了中外貿易合作的橋梁與紐帶的角色,為改革開放出了一份力。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中方雇員又應該感到滿足,因為進入商社的這幾十年來,他們為外國老板提供服務,有付出、也有犧牲,但更有獲得和進取。每一個商社都像是一所“免費大學”,每一個雇員都是不交學費的學員。趙群告訴記者:“當時,FESCO讓我們去學習,鼓勵我們去學習。每周六的例會,除了談感想之外,我們談的最多的就是今后的貿易走向。”
30年前。中國很少有人懂得什么是國際貿易,什么是國際慣例。不到20年的時間,僅在北京,在這些外國商社老板的手上,經過嚴格甚至殘酷的訓練,就已經有成千上萬人做了首席代表。“這批人才在90年代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外貿公司的里面,中方的中層領導中就有一大批是從FESCO出來的。直到現在也是如此,處處能看到FESCO的人才活躍在各個商務領域中。”趙群深有感觸地說。
1998年,趙群正式脫離了明和產業。
在明和產業的這十幾年里,他幫助運行北京市場,協調各個科室,拓展重慶市場,使貿易額有了相當可觀的提升,又因在藥品的合成方式上貢獻突出,兩次獲得一等功。這也是當時FESCO里面唯一一個被記兩次一等功的員工。
對于這段經歷,趙群謙虛地說,“改革開放以后的那個時期,需要人們將自己的生存本能和社會的要求結合起來,從中抓住機會。而FESCO就像是我的‘搖籃’,培養我用一種思想來看社會,包括對待事物基本的洞察力、行動力和思想力。沒有FSECO的培養,沒有經過外企生活的磨練,我對機會的捕捉也就沒那么精準。”
對于趙群這些“老外企”們來說,他們是特殊的一個社會層面,是隨著改革開放應運而生的一支特殊的先頭部隊,在當時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這些人去了外國商社,就等于“深入敵營”,他們所傳遞的信息,對于當時中國走向市場的作用非常大。這個與國家利益與共的特殊群體的經歷,不單與FESCO的命運相連,同時也印記著中國對外開放這段歷史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