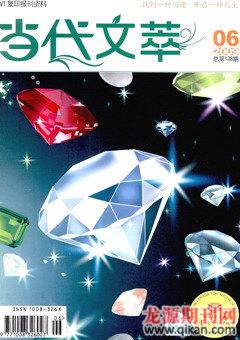心靈的獨舞
信 風
漢語詞典權威的解釋是:孤獨就是獨自一個人。
紀伯倫用詩人的視角這樣看:孤獨是憂愁的伴侶,也是精神活動的密友。
我的理解是:孤獨是一個人的狂歡,是心靈的獨舞。
能夠忍受孤獨,敢于享受孤獨的人并不多,在孤獨中有大成者就更少。面對孤獨,尤其是長時間的孤獨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所以孤獨是勇敢者的專利。小說家赫胥黎說,越偉大、越有獨創精神的人越喜歡孤獨。因為人可以在社會中學習,靈感卻只有在孤獨的時候,才會涌現出來。
事實也正是如此。
英年早逝的路遙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他在創作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巨著《平凡的世界》的時候,從準備到成稿六年的時間里,他告別《人生》的成功帶來的鮮花和掌聲,告別城市的喧囂和紅塵的紛擾,幾乎與世隔絕。尤其是創作的那八九個月,把自己封閉在陜北深山老林里的一個煤礦里,在極度的孤獨寂寞中進行高強度的創作苦役,做伴的只有一只老鼠。寫到深更半夜,聽到遠處傳來火車的鳴叫,便忍不住停下來陷入遐想之中,臆想某個人會坐著火車來看自己。可見當時他的心里是怎樣的一種蒼涼和孤寂。正是有了這樣堅強的意志,忍受著了常人難以忍受的孤獨,才成就了這部百萬字的鴻篇巨制。他在后來的創作筆記《早晨從中午開始》中對孤獨有著獨到的體味:“獨享歡樂是一種愉快,獨自憂傷也是一種愉快。孤獨的時候,精神不會是一片純粹的空白,它仍然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情緒上的大歡樂和大悲痛往往都在孤獨中產生。”“孤獨中,思維可以不照邏輯進行,可以使人的思想向更深遠更深邃的地方伸展,也能使你對自己或環境做更透徹的認識和檢討。”“孤獨常常叫人感到無以名狀的憂傷,而這種憂傷有時又是很美麗的……”
大孤獨帶來大收獲。面壁九年的達摩也是直面孤獨的勇者。梁武帝是篤信佛教的天子,迭摩以為梁武帝“堪稱法器”,就使出了禪家的機鋒,與梁武帝說法。不想梁武帝根本領悟不了達摩的禪機。達摩很失望,化葦為舟,渡江北去,到嵩山少林傳播禪法。他選擇五乳峰高臨山頂的一個天然石洞,面壁而坐,這一坐就是九年。坐禪入定時,連小鳥在他的肩頭筑巢都沒覺察,可見思想是怎樣的一種空靈。我始終對達摩這個面壁的動機持懷疑態度,僅僅因為梁武帝不能頓悟自己的禪機,就把自己扔進寂寞的深淵了嗎?佛法度不了梁武帝他可以去教化別人啊,干嗎那么一根筋呢。不過,且不說這九年達摩悟出了怎樣的禪機佛理,能在孤境中坐上九年,禁絕世俗雜念侵入,達到心虛靈空的無我境地,已非常人所能為,已是高不可攀的壯舉,可謂孤獨的最高境界。
名人們的孤獨驚世駭俗,他們的境界我們無法企及。但普通人的孤獨也別有一番滋味。
我喜歡獨處。還在上學的時候,下了夜自習,別人早早的回寢室休息了,我一個人在操場漫步,這是我學生時代一天中感覺最好的時光。喧囂一天的校園歸于寂靜,少了課本沒了提問,不想功課不思未來,卸下所有的重負讓心徹底放松。從那時起獨處成為習慣。人到中年,一個人沉思默想的時候就更多。夜深人靜時,天上一輪清月,地下幾縷微風,一個人一支煙坐在庭院,看輕煙飄散望樹影搖曳。抬頭望天,目光甚至可以穿透蒼穹,看到月宮。那砍伐月桂的吳剛依然在揮汗如雨,怎奈斧起傷愈,那棵不死之樹卻茂盛依舊,數千年如一日地做著無用功,不氣不餒,吳剛的堅韌和堅持實在可嘉;還有那嫦娥抱在懷里的玉兔,作為仙子的寵物,美人如玉,閨懷香馨,多么幸福。
孤獨就像一杯剛剛沖出的咖啡,大口地喝是沒什么味道的,需要小口小口地慢慢品味。甜味中帶著淡淡的苦澀,苦澀里又含著悠遠的馨香。我不太喜歡旅游,不得不游的時候,也很少和如織的游人爭看熱鬧的風景,更喜歡一個人沿著山澗小徑慢慢行走。沒有爭拉拍照的你來我往,沒有高掛的瀑布,只有涓涓小溪,細流翻越小石塊,卷起水花的聲音,因幽靜而顯得空靈悅耳;清風拂過,樹葉相碰發出的沙沙聲清晰可聞,偶有不知名的昆蟲輕聲吹著悠揚的笛子,小鳥和著節拍小唱,心里的那種愜意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孤獨也一樣。孤獨不是性格的自閉,思想的禁錮,更不是與世隔絕,孤獨需要把握好度,見好就收。如果任孤獨蔓延,就會像古人說的那樣,變成一種深入骨髓的寂寞,一種令你發狂的空虛。縱然在歡呼聲中,也會感到內心的惆悵與沮喪,進而發展成為憂郁。尤其對于處在逆境中的人,對這種孤獨更加敏感。所以法國文學家狄德羅說,忍受孤寂或者比忍受貧困需要更大的毅力,貧困可能會降低人的身價,但是孤寂卻可能敗壞人的性格。
那么,我們張弛有度的駕馭孤獨,給心一個舞臺,讓思想盡情地狂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