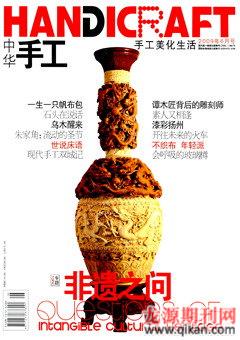一生一只帆布包
三 三
很多到京都旅游的人,費盡周折排隊也要買一款“一澤帆布”布包。一個數百元的簡單帆布包能聚集如此高的人氣,靠的是老工匠們技藝的傳承、一針一線的手工制作及一生保用的品質承諾……百年老店雖蜚聲海外,卻從不在京都以外的地方設銷售點,全世界僅此一家。在當地人心中,它的地位就等同LV,人人都會有個帆布包。
“一澤信三郎布包”的專賣店就在日本京都東山區知恩院附近,由店子信步不到百米,便會來到一澤恒三郎的家。一澤恒三郎是店主一澤信三郎的叔叔,今年已經力十歲了,但每天仍在這個由他的木屋變身而成的小型工作室干活。架著老花鏡的恒三郎,動作不徐不疾,雖然牙齒脫落了許多,但老花鏡后的眼睛卻目光炯炯。他專注地操控著手中的木槌子,準確地在帆布片上捶出布包底部的形狀和線條。雖在布包店已工作了75年,但老人不肯停下來退休。他臉上的神色,是現代人暌違已久的篤定。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和滿足,可能只是造出一只完美的帆布包。
和恒三郎一起工作的,還有老少四個工匠。他們相距五六十歲的光景,卻同擠在一個家居工作室里,為了一個個布包而忙碌。這幅畫面,叫人明白了一個粗樸的布包背后并不簡單,它意味著上一輩的辛勤刻苦以及下一代人對這種精神的延續。一個布包,是手藝和傳統的結合,也是上下兩代人之間的聯系。
一個家族兩個布包
多年前第一次到京都旅行,慕名前往“一渾帆布”的專賣店,店子位于知恩院附近的東大路通上。這一帶雖然遠離京都車站,卻是京都最有靈氣的地區之一。

公路兩旁盡是低矮的舊式木房子。“一澤帆布”的專賣店和這些出售書法用品、陶瓷、玩具、日用刀剪的雜貨店,毫不張揚且相安無事地挨在一起,安靜而低調。
“一澤帆布”早在1853年便開始營業,主人一澤常次郎的父親一澤喜兵衛原來經營西式洗衣店,到了常次郎一代,也就是大正年代左右,才開始制作帆布包,主要是供應給一些酒館或牛奶店。帆布包上會以楷書端端正正地寫上“一澤帆布京都東山知恩院前”。店子也不賣什么別的,只有各種原色調的帆布包,但質地和手工的堅實耐用一望而知,款式設計亦毫不花哨。為了便于買家長久使用,帆布袋不但可以用清水和肥皂自行清洗,店家還不忘送上“售后服務”——客人可以把破損的布包送回來維修或更換殘舊的部件,循環再用,只需付材料工本費就可以了。
多年后再次造訪“一澤帆布”,卻發現在它的專賣店的不遠處,竟多了一家“一澤信三郎布包”,而且經常門庭若市,把原來的百年老店映襯得有點清冷。這個景象后面,原來藏著一段令人不勝唏噓的家族恩仇,而分水嶺則是家族第四代主人一澤信夫在2001年的逝世。按其生前立下的遺囑,帆布包的家族生意本打算交給跟隨他打理店子逾25年的三子信三郎,但原本從事銀行業的長子忽然找出另一張遺囑,表示父親在生前已將生意交托給他。法院最終判長子勝訴,輸掉官司的信三郎必須交出布包工場及店子。然而長子贏了官司卻輸了人心,工場的數十位工匠決定集體辭職,與信三郎共進退,而“一澤帆布”的長期客戶——知恩院內的和尚和長老也都決定支持信三郎在東山區內另行開業,延續布包的百年傳統。新開的布包店,和老店就隔著兩個鋪位。即使另起爐灶,信三郎對祖業發祥地知恩院的依戀,不言自明。因法院將“一澤帆布”這個名字判予長子而令信三郎不能再用,信三郎索性將店子命名為“一澤信三郎布包”,并設計出“信三郎帆布”及“信三郎布包”兩個商標。
據說,新店開業時,店外圍了兩千多人,即使工匠連日加班開工,而顧客每人也只限購兩個,15000個布包在兩小時內也全部售罄。目前,新店開業已近三年,生意仍然十分可觀,平日每天銷售量約500個,到了周末則會增加至1000個。全世界僅此一家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有些狐疑:不過是一個帆布包,雖說是全手工制的,又何至于掀起這樣的轟動?此外,帆布包的產銷一向只在京都,又不是跨國大品牌,為何如此受到擁戴甚至蜚聲海外?目信不會只是因“歷史悠久”或主人一徉信三郎個人的魅力所致。當你手提著一個帆布包,當你有機會走進他們的工場,答案自會迎刃而解——“一澤信三郎布包”賣的就是制作嚴謹的傳統手工,也貫穿了不同年代的人,對于生活態度的取舍和執著
要體會布包制造者的精神,首先要了解整個布包從用料到手工所經歷的各個過程。所有布包用的原材料——防水帆布皆來自岡山,然后再運到大阪的工廠采用天然染料染色加工,目前所提供的顏色共有15種,至于店內那些印上了彩色花朵圖案的,則是在京都進行加工印染的,耗時要比普通純色帆布多上7倍。帆布質料的厚實不在話下,也經得起時間的磨洗,而且,經過日照和洗滌之后,顏色會變得更加自然,甚至比全新的更有韻味。布包所用的線也比一般棉線要堅固很多,再配合銅制的窩釘。然而要制成一個布包,最少也得經過十至十二道工序。工匠用的縫紉機并非那種速度飛快的電動款式,很多都是逾六十年的老式手動款式,需手腳并用,互相配合。節奏雖慢,卻能縫出不同的線條和款式。

除了縫紉機,制作布包的另一個重要工具就是不同材料所制的槌子——較重的鐵槌便于出布包的形狀,較輕軟的木槌則落在其他更細膩的部位上,使布包更加服帖——這道工序且不可小覷,要達至純熟不出錯,最少也要干上一年。至于操作縫紉機的“上崗證”,至少要有八至十年工作經驗才能領到。
布包的設計多年來也沒有大的改變,“簡單就是永恒,我們又不是要做時裝。”一澤信三郎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說。無論“一澤帆布”或‘一澤信三郎布包”,都從沒在別處設立銷售點。“現在全世界都在大量制造產品,但生產商與顧客的關系卻愈來愈薄弱。而維持兩者間的密切關系,則是我們的重點,所以我們不會在京都以外的地方設銷售點,要買的話,就來京都吧!”信三郎此話并非刻意強調布包的矜貴,在他的祖父一代,一個布包售出之后,他們跟客戶的關系并沒有就此終結,反而會每隔一段時間就去拜訪客戶,檢視布包的使用情況,看看如何改進。雖然這種面對面服務方式現在已隨著客戶越來越多而不能兼顧,但工場內仍能看到把用舊了的布包拿回來維修的客戶,以人為本的承諾始終貫徹著。
做出快樂的包
除了由恒三郎的家居改造而成的工作室,更大規模的生產工場其實位于京都大學附近,一共有三十位工匠在那里干活。有異于恒三郎工作室的是,工場內所見的“工匠”、或日語所稱的“職人”,平均年齡只有35歲。他們都被分成兩人一小組,合作完成一個布包,一個負責縫紉機縫制,另一個則揮動槌子塑形,每天最多可完成20個。
對于“職人”如何挑選,店主一澤信三郎說,他傾向選擇那些熱衷于手制物品的年輕人,學歷或其他資歷反而不重要:“我要他們可以由一數到五十(因為并不需要大量生產,只要可以由一數到五十或一百即可)。要做出快樂的布包,他們本身也要干得快樂。我也不會為他們定下什么目標指數,因為他們喜歡自己的工作,對自己會有要求。”
望著低頭努力干活的叔叔恒三郎,店主夫人說,店子其實不設退休制度,只要他愿意。可以一直干到老死。亦因如此,小工場里的另外兩位工匠田(火田)弘光和山口滿信,一個69歲,另一個也有64歲,前者從前是木匠,7年前才加入,后者則在店里工作了20年。工場也采用師徒制度,年長資深者要負責教授年輕資淺的,借以把手藝一代代傳承下去。每一天,職人們剛完成的布包就像新鮮出爐的面包一般被送到店里出售,每天只制500個,售罄即止,向隅者明日請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