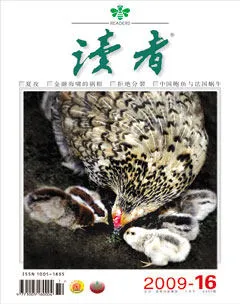平淡的雋永
陳四益
不設(shè)靈堂,不作告別,平淡得好像什么也沒有發(fā)生過(guò)。但就是這平淡,才顯出了雋永。大音希聲,大象無(wú)形。活在親人們、朋友們、讀者們心底的,才是真壽者。
靜靜地離去
丁聰先生去世的消息,毫不令我感到意外。他靜靜地躺在醫(yī)院里已經(jīng)一個(gè)多月了。十天前,丁太太打來(lái)電話,說(shuō)這一次恐怕比較“麻煩”。我懂她的意思。多少回,他大難不死,雖有兇險(xiǎn),最終都化險(xiǎn)為夷。但這次,他一直高燒不退,結(jié)果實(shí)難逆料。
丁先生和丁太太都是實(shí)實(shí)在在的人,從不愿麻煩別人,也從不肯做勞師動(dòng)眾的事情。丁太太說(shuō),如果丁先生這次在劫難逃,也不打算舉行追悼會(huì)或遺體告別儀式。懷念他,就請(qǐng)好其書,好其畫,從而想見其人。老朋友大多已屆高齡,大熱天往返勞頓,于生者有傷,于死者何益?一動(dòng)不如一靜,或可寫一些文字,留下他生活的痕跡,留下一片情誼。至于一群不相干的人,行禮如儀,了無(wú)意趣。
人生如寄。赤條條來(lái),赤條條去。存留在這個(gè)世上的,不過(guò)是短暫的過(guò)客。誰(shuí)都會(huì)有歸去的時(shí)辰,即便現(xiàn)在烈火烹油,勢(shì)焰熏天。就算留下一座巨大的墳塋,一處高聳的墓碑,甚至營(yíng)造起宏偉的殿堂,也并不能為他的生命再添輝煌。我活過(guò),我做了,我無(wú)愧——這就夠了。這是人的睿智,也是經(jīng)歷了曲折人生的徹悟。
命運(yùn)的捉弄
丁聰出生于畫家之家。他從小喜歡畫畫,可是,父親丁悚卻堅(jiān)決反對(duì)他走上繪畫的道路。沒想到父親的堅(jiān)決反對(duì),反倒促成了丁聰學(xué)畫的決心。
丁聰提著畫筆走上了抗日的戰(zhàn)場(chǎng),提著畫筆參加了反獨(dú)裁、爭(zhēng)民主的斗爭(zhēng),他甚至進(jìn)了被通緝的黑名單,不得不逃亡到香港。可是他萬(wàn)萬(wàn)沒有料到的是,當(dāng)他歡天喜地慶祝“解放”,熱情洋溢地投入新社會(huì)的建設(shè)時(shí),卻忽然變成了“人民的敵人”,他被發(fā)往北大荒,丟下了結(jié)婚一年、剛剛生下“小小丁”的太太。他到老也不曾明白憑什么落下這個(gè)罪名,但是他不曾頹唐,他說(shuō):“我還是要畫!”
戴在他頭上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他回到了北京。他滿以為從此就“回到”了人民的隊(duì)伍。但他很快發(fā)現(xiàn),無(wú)形的帽子仍高懸在他頭上。果然,一到“文革”,他又被一頓“橫掃”,勞動(dòng)改造去了。他在“干校”養(yǎng)豬,以為不再有重操畫筆的希望。可他萬(wàn)萬(wàn)不曾料到,竟會(huì)有那一聲驚雷,刺破長(zhǎng)空。他終于放下了喂豬的料勺,又拿起了畫筆。他還是要畫,只要一息尚存。
犀利與寬厚
丁聰是和氣人,平日里對(duì)人總是笑臉相迎,但骨子里卻剛直不阿。
“反右”的時(shí)候,要他檢舉一位朋友的“反動(dòng)言行”,他不能無(wú)中生有,也不能落井下石,于是,他自己成了“右派”。“文革”之時(shí),又有人強(qiáng)逼他交代一位朋友的“罪行”,并列舉此人種種“劣跡”進(jìn)行“誘導(dǎo)”。丁先生聽后慢悠悠地說(shuō):“我同他相交那么多年,他做了那么多的壞事,居然一點(diǎn)也不告訴我。天底下竟有這么壞的人!”為此,他挨了一頓鐵棍,被打得頭破血流。在鼓勵(lì)告密的年代,他仍堅(jiān)守著做人的底線。
丁先生生命的最后兩年,最遺憾也最痛苦的,是他已無(wú)法作畫。常坐輪椅,反應(yīng)也不如先前敏捷,但他謙和仁厚風(fēng)趣之性不改。
每次見到他,都能感覺到他拳拳的情意,也總是嘆息自己的無(wú)力,既不能緩解他的病痛,也不能給他什么寬慰。幸好我同他合作的全部作品四卷五冊(cè),已在他生前結(jié)集印出,書名都是他親筆題寫的。
開作品研討會(huì)的那天,正值丁先生大病之后,他仍興致不減地為每位到會(huì)的朋友在書上簽名。丁聰先生的去世,使我背負(fù)了沉重的、無(wú)法償還的感情債務(wù)。
(除 菲摘自《齊魯晚報(bào)》2009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