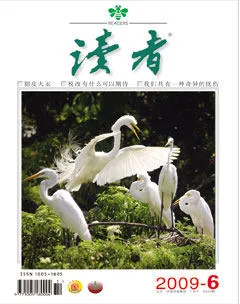決定命運的成績單
格非
1980年夏天,我參加了第一次高考,毫無意外地,我落榜了——化學和物理都沒有超過40分。母親決意讓我去當木匠。
當時木匠還是個很讓人羨慕的職業。我們當地有很多有名的木匠,但我母親請不到,她請了家里的一個親戚。這個木匠因著自己是學手藝的,覺得自己特別牛,很是兇悍。他對我母親說:“這個孩子笨手笨腳的,學不出來的,我要是打他你會舍得嗎?”母親只得說:“你打吧。”“我很不喜歡這個蹺著腿坐在木椅上的人——我和他無冤無仇,他為什么要打我?”我就對母親說,“我要考大學,而且要考重點大學。”母親睜大了眼睛:“孩子,你怎么能說這樣的話呢?你連門都沒有摸到呢,你要是考上大學,我們都要笑死了。”
就在我灰了心、要去當木匠學徒的時候,一個鎮上的小學老師,姓翟,敲開了我家的門。他與我非親非故,素不相識。我至今仍然不知他是如何挨家挨戶尋訪到我們村的。我依然清晰地記得,當時夜已經很深了,大家都睡了。他戴著草帽,站在門外,把我母親嚇了一跳。他劈頭就說:“你想不想讀諫壁中學?”那是我們當地最好的中學,我當然是很愿意的。他說可以把我引薦給他那里的一位朋友。
當我拿著翟老師的親筆信到了諫壁中學,他的那位朋友卻告訴我,語文、數學必須拿到60分,不然無法進入補習班。他說:“讓我看看你的高考成績單。”
在決定命運的時候,我的腦子還算比較清醒。我知道我的成績根本不能進入這個補習班,我也知道無論如何都不能夠把口袋里的成績單給他看。于是我說:“我把成績單弄丟了。”
“你可以去丹徒縣的文教局,你去查一查,把分數抄回來。”他說,然后給了我一個地址。
縣文教局在鎮江,青云門六號。在馬路邊上,我只要隨便跳上一輛公共汽車,就可以回到家,永遠地做一個木匠的學徒。可是如果我去鎮江的文教局呢?結果是一樣的,我還是會得到一個一模一樣的成績單,還是無法進入諫壁中學,還是要返回家鄉,做一個學徒,為我的師傅搓好熱毛巾,聽任他打罵。
我徘徊了兩個小時。以我的性格而言,我其實是一個很保守的人,不會輕易冒險,不會去做一些我覺得非分的事情。我覺得我90%是要回家的。我根本沒有去過鎮江。它對于我的家鄉而言,是一個大城市,太遠了,而且去了我也不知道那個地方在哪里。這些對我都是無法逾越的理由。但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鬼使神差地登上了去鎮江的過路車。
到了縣文教局,正好是下班時間,傳達室的老頭冷冷地說:“現在下班了,你不能進去。”
我想,也罷,我進去又有什么用呢?在我打算掉頭離開的時候,有人叫住了我:“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見兩個人,一男一女,往外面走。我說我的高考成績單丟了,能不能幫我補一下。
男的說:“下班了,明天再來吧。”
女的則說:“我們還是幫他補辦一下吧,反正也不耽誤時間。”
他們把我帶回辦公室,幫我查找檔案,又問我辦這樣的成績單有什么用處。
我沉默了一下,突然說:“我的成績單沒有丟。”
“那你來這里干什么?”他們顯然有些生氣了。
我于是講了高考的落榜,講了自己很想去諫壁中學補習,但是沒有達到他們要求的分數線。我說:“我一定要讀這個補習班,去考大學。”
那個女的說:“這怎么行!”男的不吭氣兒,他抽著煙,盤算了好一會兒。他讓我出去等回話。十分鐘后,他說:“唉,幫他辦了。”
我那時很小,16歲,穿的衣服很破舊。大概他是因此萌發了幫助之心。
他們問我:“需要多少分?”我說:“語文70分,數學80分。”說完了很后悔,因為這個分數已經可以考上大學了。我又把分數改了過來,語文68分,數學70分。寫完了之后要蓋章,但在這個節骨眼上,公章突然找不到了。
他們翻遍了抽屜,打開又合上。這對于一個小孩子來說,可能是最緊張的時候。沒有公章不是完了嗎?事實上公章就在他們手邊,大概是當時大家都太緊張了吧。
女的蓋完了章,輕輕說了一句:“茍富貴,勿相忘。”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流出來了。那是我迄今為止見過的最美麗的女性。我的感激出于如下理由:她竟然還會假設我將來有出息。
我似乎沒有說什么感激的話,拿著成績單,飛跑著離開了。我一天都沒有吃飯,等回到家的時候,人已經都快虛脫了。
第二年我再次參加高考,考入上海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開始了在大學的求學之路。
對我而言,生活實在是太奇妙了,它是由無數的偶然構成的。你永遠無法想象,會有什么人出現,前來幫助你。
(紫陌紅塵摘自中信出版社《追尋80年代》一書,霍俊其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