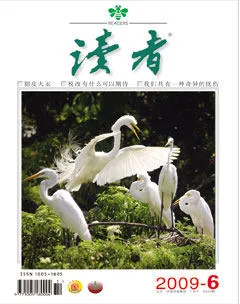萬里君獨行
馮驥才
誰肯一個人拿出全部積蓄買一條船,抱著一臺相機在長江上漂流整整二十年,并爬遍長江兩岸大大小小所有的山,拍攝下這偉大的自然和人文生命里每一個動人的細節?鄭云峰肯。他為了什么?為了在長江截流蓄水前留下這條養育了中華民族的母親河真正的容顏,為了給李白杜甫等歷代詩人曾經謳歌過的這條大江留下一份完整的視覺備忘錄。多瘋狂的想法,但鄭云峰實實在在地完成了。他以幾十萬張照片挽留住長江亙古以來的生命形象。為此,我在他的“擁抱母親河”攝影展開幕式上講道:“這原本不是個人的事,卻叫他一個人默默地、心甘情愿地承擔了。我們天天叫嚷著要張揚自我,那么誰來張揚我們的山河、我們民族的文化?”
提起鄭云峰,自然還會聯想到最早發現“老房子”之美的李玉祥。他也是一位攝影家,是三聯書店的特聘編輯。20世紀90年代初,他推出一系列攝影圖書時,全國正在進行翻天覆地的舊城改造。李玉祥卻執拗地叫人們向那些正在被掃蕩的城市遺產投以依戀的目光。21世紀初,鳳凰電視臺要拍一部電視片《追尋遠去的家園》,計劃從南到北穿過數百個最具經典意義的古村落。鳳凰電視臺想請我做“向導”,可是我當時正忙著啟動多項民間文化遺產的普查,便推薦李玉祥。我說:“跑過中國古村落最多的人是李玉祥。”
記得那陣子我的手機上常常出現一些陌生地區的電話號碼,都是李玉祥在給電視劇組做向導時一路打來的。這些古村落都曾令李玉祥如癡如醉,這一次卻不斷聽到他在話筒中驚呼:“怎么那個村子沒了?十年前明明有一個特棒的古村落在這里呀!”“怎么變成這樣,全毀得七零八落啦!”聽得出他的惋惜、痛苦、焦急和空茫。正因為如此,多年來李玉祥一直爭分奪秒地在為這些難逃厄運、轉瞬即逝的古村落爭搶時間。他要把這些經過千百年創造的歷史遺容留在他相機的暗盒里。他是一介書生,他最多只能做到這樣,然而他把攝影的記錄價值發揮到了極致。這些價值在被野蠻而狂躁的城市改造見證著。許多照片已成為一些城市與鄉鎮歷史個性的最直觀的見證。李玉祥至今沒有停止他的自我使命,依然揣著沉重的相機,在天南海北的村落間踽踽獨行。古來的文人崇尚“甘守寂寞”和“不求聞達”,并視其為至高的境界。然而在市場經濟兼媒體霸權的時代,寂寞似與貧困相伴,聞達則與發達共榮,有幾人還肯埋頭于被鬧市遠遠撇在一邊的冰冷角落?
前些天在北京見到李玉祥。他說他已經把江浙閩贛晉豫冀魯一帶跑遍。他想再把西北諸省細致深入地過一下。我忽然發現站在我面前的李玉祥有點變樣,十多年前那種血氣方剛的青年人的氣息不見了,儼然一個帶著些疲憊的中年漢子。心中暗暗一算,他已年過四十五歲。他把生命中最具光彩的青春歲月全交付給那些優美而緘默著的古村落了。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因為他并不想叫人知道,只想讓人們留心和留住那些珍貴的歷史精華。
由此,又聯想起郭雨橋——這位專事調查草原民居的學者,多年來為了盤清游牧時代的文化遺存,也幾乎傾盡囊中所有。背著相機、筆記本、雨衣、干糧和各種藥瓶藥盒,從內蒙古到寧夏到新疆,全是孤身一人。他和鄭云峰、李玉祥一樣,已經與他們所探索的文化生命融為一體。記得他只身穿過賀蘭山時,早晨鉆出蒙古包,在清冽沁人的空氣里,他被從遼闊大地的邊緣升起的太陽感動得流淚。他想用手機把他的感受告訴我,但地遠天偏,信號極差。他一連打了多次,那些由手機傳來的一些片斷的聲音最終才聯結成他難以抑制的激情。上個月我到呼和浩特,他正在東蒙考察,聽說我到了,連夜坐著硬座列車趕了幾百公里路來看我,使我感動不已。雨橋不善言辭,說話不多,但有幾句話他說了幾遍,就是他打算還要用三年時間,爭取七十歲前把草原跑完。
他為什么非要把草原跑完?并沒人叫他非這么做不可,再說也沒有人支持他、答理他。那些“把文化做大做強”的口號,都是在豐盛的酒席上叫喊出來的。他只是一心想把為之獻身的事做細做精。
然而,這一次我發現雨橋的身體差多了。他的腿因勞損而變得笨重遲緩。我對他說:“再出遠門,得找一個年輕人做伴。能不能在大學找一個民俗學的研究生給你做幫手?”他對我只是苦笑而不言。是啊,誰肯隨他付出這樣的辛苦?這種辛苦幾乎是沒有任何回報和一丁點實惠的。我們分手后的第三天,他又赴東蒙。草原天氣已經變涼,一年來出行在外的時間已然不多,他必須抓緊每一天。
隨后一日,我的手機收到他發來的一首詩:“蕭蕭秋風起,悠悠數千里。年老感負重,腿僵知路遲。玉人送甘果,蒙語開心扉。古俗動心處,陶然膠片飛。”感動之中,我當即發去一詩:“草原空寥卻有情,伴君萬里一身行。志大男兒不道苦,天下幾人敢爭鋒?”
上邊說到三個不凡的人:一個在萬里大江中,一個在大地的深處,一個在茫茫草原上。當然還有些同樣了不起的人,至今還在那里默默而孤單地工作著。
(李建海摘自《河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