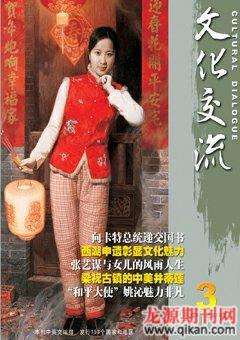探尋楚文明的歷史記憶
梅子滿

2008年4月2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文物保護工作領導小組確定了2008年度考古發掘任務,
并與包括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內的17家項目承擔單位正式簽訂工作協議。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輸水線路從荊楚文化遺存富集的丹江口庫區向北穿越夏商文化鼎盛的中原沃土、燕趙文化繁榮豐茂的京畿大地。這是一個穿越中華文明腹地的浩大工程,是繼三峽之后又一次大規模的全國性考古會戰。寧波考古工作隊所在的丹江工地是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文化融合的過渡地帶,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就擁有高度發達的文明,是研究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的“重鎮”。至2005年12月,丹江庫區確定實施保護的文物點共159處,其中地下文物點137處,考古發掘工作量33.3萬平方米。
2008年9月2日,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水北調考古工作隊正式從寧波出發,前往湖北省丹江口市習家店鎮龍口村,參與南水北調全國性工程考古大會戰。這是寧波考古工作者第一次走出浙江,現身國家級考古工程發掘現場。
找不到寶 夜不能寐
一棟裸露著水泥墻面的兩層小樓,孤零零地立在湖北省丹江市習家店鎮龍口村的山坡上。前面幾十米處,就是飄著一層薄霧的丹江口水庫——南水北調工程中線的起點。這棟房子,就是寧波市考古工作隊在龍口村的大本營。
2008年12月12日上午,我們一行驅車從丹江口到達這里,花了兩個半小時。如果從武漢出發,則驅車大概需要7個半小時左右,而走水路就說不準了。
這真是一個荒涼的所在。一路上,風景越來越好,路卻越來越窄,路況也越來越差——先是人煙稠密之地的二級公路,再就是鄉間一般的水泥路,最后就是崇山峻嶺之間,建在山脊上的一條盤山公路。車行其上,盡管風景這邊獨好,卻幾乎不敢往窗外看,因為實在太陡了。而路邊的人煙也隨著車子的前行而日漸稀少,到最后,長長的公路上,除了偶爾有幾輛裝滿當地特產橘子的三輪車擦肩而過外,就只有我們一行兩輛車了。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真是越走越心涼。回到寧波,一想到要在這里工作好幾個月,我連著18天沒說話。”李永寧告訴筆者。在9月2日正式進駐之前,他曾經來龍口村考察過一次。2007年才從甘肅調到寧波的他曾經在新疆和中蒙邊界做過考古發掘工作,也算個老“考古”了,但這次卻是他有生以來最艱苦的一次野外考古工作。
剛來的時候,條件的艱苦讓他感到心煩,但更多的時候他是在發愁,“我擔心寧波考古好不容易爭取到一次走出浙江的機會,結果卻兩手空空地回去”。這樣的事情不是沒有發生過。從2006年開始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考古會戰,在他們之前,已經有數支考古隊因為沒有發現有發掘價值的墓葬而被迫打道回府。
前20多天,這樣的命運似乎很有可能降臨到寧波考古工作隊身上。按照合同,他們的勘探面積是龍口村周圍15平方公里范圍內的土地。在上世紀50年代丹江大壩蓄水前,現在的龍口村是均縣古城所在。剛開始幾天,李永寧和隊員們不停地挨家挨戶找線索。有點頭緒后,立馬鉆進因為封山育林而草木茂密的山坡上勘測,但1萬多平方米勘測下來,一無所獲。“那時,我天天發愁,壓力大得睡不著覺。”

天道酬勤 碩果累累
艱苦,仿佛就是野外考古工作的代名詞。而在龍口村,這份艱苦體現得特別實在。龍口村遠離鄉鎮,吃不上鮮菜,有時候只得挖野菜度日。那次,他們好不容易從當地一個老農民那里買了兩個大冬瓜過來,整整吃了10天。
而在剛到的時候,比吃菜難更難受的是當地肆虐的各種小蟲子。“晚上根本沒法睡個安生覺。”
每到晚上一開燈,屋外就撲進來大量的飛蛾、蚊子和瓢蟲等昆蟲。睡覺時,人在床上翻個身,早晨醒來就會發現身下壓死了黑壓壓一層昆蟲。考古隊員點蚊香,插上電子蚊香都不管用,每個人胳膊、腿上都被叮咬得疙瘩成堆。
由于交通不便,生了病也是一件頭疼的事情。隊里技術員老朱上次得急性腸炎就被好好折騰了一回。讓隊員覺得不便的,還有洗澡問題。許超告訴筆者,他4個多月來,也就洗了5次澡,“不是不想洗,而是沒條件洗”。盡管“大本營”是村里最好的房子了,又靠著這么好的水庫,“不過隊里有紀律,不準我們到水庫里洗澡的”。

即使在如此艱苦的生活環境中,寧波考古隊員們還是牢記自己的使命和任務。他們在艱難困苦中不懈地勘察探尋,努力勤奮地工作著。
好在機會垂青勤奮的人。到最后,他們不僅自己吃了個“飽”,還把地盤讓給了同樣為找不到合適的發掘墓葬而發愁的成都市考古研究所和黑龍江省考古研究所,“一個村有三支考古隊已經算難得了,更難得的是,這兩支考古隊的領隊還都是我的同班同學呢!”李永寧笑著說道。
發掘的地方選定了,就在萬家溝,但李永寧很快又愁上了。龍口村交通不便,經濟不發達,道路崎嶇,不通汽車,由于當地村民對墓葬發掘持有的傳統觀念,加之此處地廣人稀,又正逢柑橘采摘農忙時節,考古隊很長一段時間請不到民工。“那幾天,我又愁得天天蹲在水庫邊想解決的辦法。”
李永寧和隊員嘗試從鄖縣、河南甚至陜西、甘肅等外地邀請工人。不過,他最終采用做思想工作的方式,跑到村民家中,用拉家常、談心等方式獲得當地村民的理解,通過多次工作,終于聘請到了足夠的人手。
在“大本營”對面,隔著一道灣就是考古發掘現場。盡管目測距離不過四五百米,但沿著一條被寧波考古隊員踩出來的小路,穿過橘林繞彎走過去,卻需要15分鐘時間。考古現場,探方整齊地將面水的坡地分隔成一格一格的漂亮長方形,裸露的紅色土壤已經龜裂。四周用彩旗帶拉著,兩條紅色橫幅非常醒目,一條是“寧波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水北調考古工作隊龍口墓葬群發掘現場”,一條是“歡迎各級領導、專家蒞臨現場指導”。
“來參觀的領導和專家實在太多了,所以我們干脆就一直掛著,不取下來了。”陪同的許超站在紅色的土地上自豪地告訴筆者,“我們在參加這次南水北調考古大會戰的17支考古隊里的表現,絕對上乘!”
在考古工地2900平方米的發掘面積內,有不少比較深的坑,“那就是墓葬,我們共發現了43處,其中戰國墓葬21座、漢代墓葬5座、宋代磚室墓2座、清代墓葬13座、近現代墓葬2座;灰坑3座;近現代擾溝9條。”李永寧如數家珍地向筆者介紹道。初步統計共發掘出各個歷史時期文物150余件,包括有青銅器、鉛器、陶器、鐵器、石器等,時代縱跨戰國至明清,尤其是戰國墓葬中出土的陶器組合,對于研究整個鄂西北地區的楚文化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此外,本次發掘的5座漢墓還提供了丹江地區漢代早期墓葬研究新的資料。專家們認為,寧波考古隊“進場到位,管理規范,發掘質量較高,資料完善”。

現在,考古隊的技術人員正在緊張地對挖出來的寶貝進行修復和登記備案。在這棟算是龍口村最好的房子的樓前一片面積在40平方米左右的水泥平地上,一堆一堆地擺滿了這次考古發掘的碎陶瓷片。而在樓左側一間防盜門關著的小屋里,則是考古隊存放器物的庫房。“好東西不少呢!”隊員許衛紅笑著告訴記者,“我們在幾座戰國墓葬里找到了不少隨葬品。主要包括兩種類型,一是日用陶器,鬲、盂、罐;一是陶禮器,鼎、敦、壺、豆、盤、匜等。陶器的整體風格雖然屬于典型楚文化系列,但有些器物具有當地特色,比如淺盤斜直腹細柄豆、雙耳罐等,而出土的淺盤斜弧腹細柄豆則為典型的楚式器物。某些器物也具有中原文化的風格。這與丹江地區地處兩種文化交融地帶有關,個別墓葬中隨葬的青銅武器則表明了墓主生前的地位。她推測,墓地擁有類似周禮所言的墓地管理制度,從綜合隨葬品以及棺槨使用情況看,墓主的身份多數屬于“士”一級。
“寧波考古人首次‘出征,可謂大有收獲。”已經4次來到考古工地慰問的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王結華興奮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