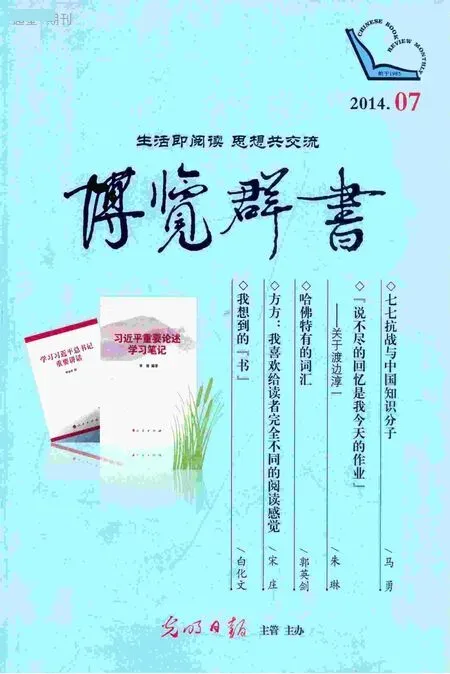胡適的失察
吳心海
胡適憑一面之詞斷言:何家槐“不是偷人家的東西的人”
1934年3月13日,胡適給吳奔星寫了一封回信。全信如下——
吳先生:
此種問題,你若沒有新證據(jù),最好不要參加。何家槐君是我認得的,他不是偷人家的東西的人。韓君所說,文理都不通,其中所舉事實也不近情理。(海按:應指侍桁1934年3月7日發(fā)表在《申報·自由談》的文章《徐家槐的創(chuàng)作問題》。此文是侍桁從徐轉(zhuǎn)蓬處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撰寫并發(fā)表的。從胡適信的內(nèi)容和時間推斷,吳奔星把此文寄給了胡適)如說:“我(轉(zhuǎn)蓬)有一篇文章先拿給從文修改,改了很多,而發(fā)表出來則變了何家槐的名字。”
誰“拿給從文”呢,誰“發(fā)表”呢?難道從文幫家槐“偷”嗎?又如:“也有先投給《現(xiàn)代》和《新月》的文章,寫著是我的名字,而既經(jīng)拿回來,在另外雜志上發(fā)表,又變了名。”這又是誰“拿回來”,誰“在另外雜志上發(fā)表”呢?
你若要“燭照奸邪”,最好先去做一番“訪案”的工夫。若隨口亂說,誣蔑阮元、張之洞、丁福保諸人,你自己就犯了“道聽途說”的毛病,那配“燭照奸邪”?
胡適,廿三,三,十三
此信應該是對吳奔星還可能存在的一封來信的回復(海按:朱洪在2001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適大傳》中指出,胡適覺得沈從文應該給何家槐說說話,于是把吳奔星的信轉(zhuǎn)寄給了沈從文。此說應該有據(jù),這也是胡適因吳信已轉(zhuǎn)沈而沒有保存吳奔星這封信的原因)。它所涉及的,是1934年中國文壇圍繞何家槐和徐轉(zhuǎn)蓬著作歸屬權(quán)問題展開的一場紛爭,史稱“徐何創(chuàng)作之爭”。1949年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該事件被上綱上線為“第三種人”配合國民黨反革命文化圍剿,對左聯(lián)作家進行打擊的反動行徑。牽涉在內(nèi)的作家,有的未能得到善終(如楊邨人1955年跳樓自盡,徐轉(zhuǎn)蓬1966年跳水自殺),有的即便茍活到“文革”結(jié)束,仍被一些研究者歸類為“叛徒”、“攻擊左聯(lián)”、“第三種人”,長期得不到公正的對待和評價。近年來,隨著思想解放的深入,一些論者在談及“徐何創(chuàng)作之爭”事件時,能夠直面歷史和更加客觀地評論事件本身。就我所看到的材料,有潘頌德撰寫的《何家槐》(《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聯(lián)”作家·下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劉小清的《徐、何創(chuàng)作之爭》(《紅色狂大飆——左聯(lián)實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雖然有些關鍵問題還在模棱兩可之中,但沒有回避何家槐的錯誤,不再完全根據(jù)政治需要來詮釋一件主旨還是文學范疇上的紛爭。
不過,姚辛編著的《左聯(lián)畫史》(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及《左聯(lián)史》(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年),在對“徐、何事件”的描述時,仍然老調(diào)重彈,還在使用“群魔圍攻何家槐”、“別有用心、惟恐天下不亂的人”、“肆無忌憚地四處鼓噪起來”、“掀起攻擊左翼文壇的陣陣惡浪”、“一場有組織的‘陰謀”、“鬼魅們的真面目也更加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之類的文字,不禁讓人倒抽一口冷氣。而且,姚辛在對“徐何創(chuàng)作之爭”的描述中,對并非革命營壘中的胡適的態(tài)度深表“感動”與“崇敬”——
正當何家槐遭受“圍剿”之時,著名學者、中國公學校長(何家槐曾是該校國文系高材生)胡適力排眾議、仗義執(zhí)言,3月13日,他致函作家沈從文,信中說:“你是認得何家槐的。現(xiàn)在有人說他偷別人的作品……如果你認為家槐是受了冤枉,我很盼望你為他說一句公道的話。這個世界太沒有人仗義說話了。”(《左聯(lián)畫史》,P336)
這時,大約胡適又聽到吳奔星要介入此事,也是3月13日,胡適又給吳奔星去信,信中勸說道:“此種問題,你若沒有新證據(jù),最好不要參加。何家槐君是我認得的,他不是偷人家的東西的人。”這封信以肯定的結(jié)論駁斥了侍桁之流對何家槐的誣蔑,勸阻吳奔星。雖然我們不知道沈從文究竟說了“公道話”沒有,也不了解他對吳奔星的勸阻結(jié)果如何。(海按:吳奔星當時為《申報·自由談》讀者兼作者,從中了解到“徐何創(chuàng)作之爭”的肇端十分正常。胡適復信后不久,何家槐就在《申報·自由談》發(fā)表《我的自白》,承認改寫、擴寫徐轉(zhuǎn)蓬小說一事,一場持續(xù)2個月的風波就此偃旗息鼓,吳奔星沒有再介入。上個世紀80年代初,吳奔星讀到中華書局出版的《胡適來往書信選》中胡適就此事給沈從文和他的信件,曾恍然大悟:難怪胡適先生當時那么說,原來他和何家槐關系非同一般啊)但這兩封信卻讓我們深受感動,也使我們認識了這位著名學者令人崇敬的另一面。(《左聯(lián)史》,P273)
事實上,胡適這里所言,并非“肯定的結(jié)論”,而是憑一面之詞而斷言的失察。
何家槐和胡適師生之誼濃厚
胡適確實是“認得”何家槐的,因為前者擔任過中國公學校長,而后者曾是中國公學學生。(姚辛在《左聯(lián)史》中稱,“徐、何事件”發(fā)生時,胡適“任中國公學校長,何家槐是該校文學系高材生”,實為大謬。因為胡適1930年即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一職。而何家槐則于1931年轉(zhuǎn)入上海暨南大學)但是,如果僅僅只是“認得”的人,以胡適之身份,以胡適“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的主張,他如何能夠肯定何家槐“不是偷人家的東西的人”,甚至認為“這個世界太沒有人仗義說話了”呢?甚至,為什么在胡適“力排眾議、仗義執(zhí)言”之后,最接近事實真相的沈從文(何家槐在上海中國公學讀書時,曾發(fā)起組織文藝社團,請徐志摩、沈從文等人為顧問。沈曾為何家槐修改文章,其中包括何家槐所拿的徐轉(zhuǎn)蓬的文章)卻沒有如胡適之愿跟進呢?我試圖從過去已有及最新發(fā)現(xiàn)的各類相關材料中去尋找線索及答案,卻沒有看到沈從文在“徐何創(chuàng)作之爭”問題上說過“公道話”,甚至連他是如何回答胡適請求的,也不得而知。《沈從文全集》中沒有,《胡適日記全編》中沒有,《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中也沒有,著實令人遺憾。
好在,我并非一無所獲。事實表明,胡適和何家槐不只是“認得”那樣簡單,而是具有相當?shù)膸熒x。《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黃山書社,1995年)中有何家槐寫給胡適的信、片5通。
第一通,何家槐當時還是中國公學社會科學院一年級學生,以“家境貧寒”為由,向身為中國公學的校長胡適申請“工讀”機會,并希望免除“學宿費”或“半費”,信的抬頭稱“胡校長”。信的署名后沒有年月,只有“15日”。從何家槐1929年秋考入中國公學及信中最后對胡適“敬祝冬安”的字樣推斷,此信應當寫于1929年至1930年之交的冬季。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一些材料或稱何家槐1930年秋考入中國公學(如姚辛編著的《左聯(lián)詞典》,P122),或語焉不詳,只說他高中畢業(yè)后考入中國公學。根據(jù)何家槐家鄉(xiāng)編撰的《義烏縣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浙江省義烏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所編《義烏文史資料第2輯》的相關介紹,何家槐
應為1929年6月從金華省立7中師范科畢業(yè)后考入上海中國公學。
第二通,何家槐已經(jīng)在上海“辣斐坊”和胡適見過面,胡適并為他題寫過《小說集》封面,抬頭不再是“胡校長”,而改稱“適之先生”,第三通和第四通的抬頭也是如此。因為信中談到要抄寫徐志摩寫給他的信,聯(lián)系后文徐志摩的信件在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期間被毀,寫于2月16日的此信應當在1930年或1931年。
第三通,匯報中國公學在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期間遭到日軍炮火時自己的損失——“可惜53封志摩哥寫把我的信,已付之一炬”;寄宣紙給胡適,請他為自己“寫幾個字,給我不時看看,過過我敬慕你的癮。不消說,存這心已是幾年了”,“先生念我真誠,看我可憐,竟許一有空閑,就替我動筆”。時間是1932年5月2日,當時何家槐因中國公學被炸離開上海到了浙江,通信處也是浙江。
第四通,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寫信的時間——1932年6月21日。他繼續(xù)向胡適索字,并請胡適替“我友徐轉(zhuǎn)蓬”(兩人是同鄉(xiāng)加中學同學,一度為密友)也寫兩張字,“叫他快活”,證明那個時候徐、何之間的關系還是十分和睦的。這一材料,此前論者無一提及。
第五通,何家槐準備去胡適家去談談關于“校史”以及其他的事,抬頭是“我敬愛的校長先生”。寫信時間為5月4日,如果按照書中排列順序,當是1933年。不過,何家槐1932年就已經(jīng)轉(zhuǎn)入上海暨南大學讀書,并在1933年初春加入左聯(lián),而胡適此時也辭去中國公學校長多年,因此此信寫于1933年的可能性不大。聯(lián)系到信中何家槐以“親愛的校長”稱呼胡適,又自稱“學生家槐謹上”,以及要談的事情有關《校史》,而這個《校史》應指胡適1929年3月17日所撰寫的《中國公學校史》一文,那么此信最有可能是1930年所寫。當然,這還需要其他證據(jù)來落實。
這幾封表明師生深厚情誼的信,均發(fā)生于“徐何創(chuàng)作之爭”之前。
至于胡適,在1934年2月14日的日記中曾提到何家槐,而其時正在“徐何創(chuàng)作之爭”前夕——
偶檢北歸路上所記紙片,有中公學生丘良任談的中公學生近年常作文藝的人,有甘祠森(署名永柏,或雨紋),有何家槐、何德明、李輝英、何嘉、鐘靈(番蘋)、孫佳汛、劉字等。此風氣皆是陸侃如、馮沅君、沈從文、白薇諸人所開。(《胡適日記全編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即便只是從何家槐前前后后給胡適的5封信、片中,已經(jīng)能夠看出,他們之間的師生情誼頗為濃厚。胡適對何家槐的愛護,顯然源自何家槐在胡適面前表現(xiàn)出來的謙恭和乖巧。不過,愛屋及烏之心也應該有之,畢竟,一直提攜何家槐的“志摩哥”和胡適交情匪淺!
恪守“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不易
陳漱渝曾在《“但見奔星勁有聲”——胡適和吳奔星二三事》一文中指出——
1934年2月,上海文壇發(fā)生了“徐何創(chuàng)作問題之爭”。……當時,吳奔星先生也想?yún)⒓佑懻摚盃T照奸邪”,特去函征詢胡適的意見(海按:吳奔星就此事致胡適原信不存,只能推斷如此),胡適在同年3月13日復信中明確告訴他:“此種問題,你若沒有新證據(jù),最好不要參加……你若要‘燭照奸邪,最好先去做一番‘訪案工作。若隨口亂說……你自己就犯了‘道聽途說的毛病,哪配‘燭照奸邪?”胡適的這種態(tài)度,跟他“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的一貫主張是完全一致的。……吳奔星先生當時血氣方剛,嫉惡如仇,又富詩人氣質(zhì),但在處世上畢竟不如文壇前輩沉穩(wěn)(海按:這里似乎不存在“沉穩(wěn)”與“成熟”之類的泛泛而談,而應是胡與吳對待事實真相,究竟誰“失察”,錯了;誰“燭照”,對了)。人,總是要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如能得到前輩適時的指引,實為人生一大幸事。(《人民政協(xié)報》,2004年9月23日)
“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是胡適一貫的主張,不過,正式行諸文字,應該出自1936年胡適致羅爾綱的一封信,信中說——
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話:“有幾分證據(jù),說幾分話”。有一分證據(jù)只可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jù),然后可說三分活。治史者可以作大膽的假設,然而決不可作無證據(jù)的概論也。
可惜,在“徐何創(chuàng)作之爭”中,胡適并沒有能夠恪守“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的原則。雖然他提醒吳奔星對“此種問題,你若沒有新證據(jù),最好不要參加”,不無道理;但他接下來的表示“何家槐君是我認得的,他不是偷人家的東西的人”,卻失之武斷。胡在這里沒有拿出他的“新證據(jù)”,或者說他的證據(jù)便是何家槐的一面之詞,甚或想從沈從文處找尋“新證據(jù)”而不可得。那么,胡在回吳之信中所言,豈不正是他所反對的“無證據(jù)的概論”?!
胡適的失察,或者說他“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原則的失守,一是因為他和何家槐師生情誼頗厚,二是何家槐在“剽竊”事件曝露之后,矢口否認把徐轉(zhuǎn)蓬的小說署自己的名字發(fā)表的事實,稱:“我寫作一向老實,茍且偷巧的事,從來不愿嘗試。”(見《關于我的創(chuàng)作》,《申報·自由談》,1934年2月26日)“鄙人雖缺乏學識修養(yǎng),但對創(chuàng)作素取慎重態(tài)度,既不敢草率從事,亦從未倩人代作。此有具體事實,可以證明,非信口雌黃之輩所能毀謗中傷。”(《文化列車》第10期,1934年3月1日)胡適認同了何家槐的一面之詞的辯白,輕信了他的清白,在嚴詞阻止吳奔星去參與對何的“揭露”的同時,還鄭重其事地吁請“認得何家槐”的沈從文站出來“仗義說話”。顯然,胡適是出自愛護學生的善良愿望,但客觀上卻成為失去原則的“護短”行為。
何家槐的辯白很快遭遇到來自“受害者”及其友人們更猛烈的抨擊。在大量無可辯駁的證據(jù)面前,何家槐終于抵擋不住,敗下陣來,這時偏袒者胡適所不希望見到的事情終于發(fā)生了——何家槐于同年3月22日和23日(即胡適3月13日致吳奔星信后的10天)連續(xù)在《申報·自由談》發(fā)表《我的自白》,承認曾改寫、擴寫徐轉(zhuǎn)蓬小說并發(fā)表的情況。盡管他說“很誠實地自己審判了自己”,其實仍有不少自我辯護之辭,甚至倒打一耙,希望徐轉(zhuǎn)蓬“能很誠懇的改正跟我差不多的行為”,結(jié)果再次遭到徐轉(zhuǎn)蓬的反擊(見徐轉(zhuǎn)蓬3月31日在《申報·自由談》發(fā)表的《答何家槐誣害的自白》),導致昔日的同窗好友徹底反目。
何家槐的《我的自白》,想必胡適先生是看過或聽說過的。從此以后,他再也沒有對“徐何創(chuàng)作之爭”發(fā)表過意見。對于自己的失察,他后來是否再說過什么或做過什么,囿于材料,我們無從知曉。不過,他后來對同樣也是學生的吳奔星的態(tài)度,倒是十分和藹,之后有過多次見面機會,再也沒有提及在信中嚴厲苛責他“道聽途說”的事情。1934年12月,胡適到北師大作題為《中國禪學之發(fā)展》的演講,欣然同意北師大文學院院長黎錦熙提出的由吳奔星及同學何貽焜為他的演講做記錄。吳奔星何貽妮記錄的演講稿經(jīng)胡適潤色,于1935年4月30日發(fā)表于《師大月
刊》第18期。1954年,剛剛恢復禪學史研究工作的胡適,專門請人影印了這篇演講;后來出版時,胡適還特注明“吳奔星何貽焜記錄”。而該文在大陸出版時,記錄者的名字長期被抹掉。
倒是魯迅,雖然曾經(jīng)說“徐何創(chuàng)作問題之爭,其中似尚有曲折,不如表面上之簡單”(1934年4月12日致姚克信),但對于“剽竊”這樣有失人格的事,還是表示了自己的嚴正立場:“何家槐竊文,其人可恥”(1934年5月1日致婁如暎信)。
奇怪的是,這來自革命營壘中的聲音,卻沒有得到姚辛的“感動”或“崇敬”,甚至,他對此只字不提,和他在《左聯(lián)史》中描寫“徐何創(chuàng)作之爭”時以“胡適仗義執(zhí)言”為題專列一小節(jié),形成鮮明對比!
如何看待徐何創(chuàng)作之爭
徐何創(chuàng)作之爭,迄今已75年了。在雙方當事人均歸隱道山的今天,如果能夠撇開政治上的考量,且摒除文學上的派性之爭、意氣之爭,只就事論事,那么,是非曲直的辨識還是容易得多。
何家槐和徐轉(zhuǎn)蓬作為愛好文學的同窗好友,相互交流作品,如果只是為了發(fā)表起來容易一點,或者因為經(jīng)濟拮據(jù)而需要稿費救急,把修改過的好友作品拿出去以自己的名字刊布,偶一為之,只要彼此同意,倒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如此這般養(yǎng)成習慣,一而再,再而三,毫不顧及他人的感受,就無論如何也不妥當了。
很顯然,何家槐事先是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的。1933年4月,何家槐的小說集《竹布衫》出版,一共收有小說5篇,其中就包括徐轉(zhuǎn)蓬的小說《一個兵士的妻子》(何家槐后來在《我的自白》中表示,這篇小說“原長4000多字,我把它增加到9000多字”)。發(fā)人深思的是,何家槐在《后記》中表示:“3月前,轉(zhuǎn)蓬答應替我寫序,現(xiàn)在竟不見踐約,實在是件憾事。”他不曾想,徐轉(zhuǎn)蓬如果為收有自己小說卻署著別人名字的集子寫序,又是件怎樣的憾事呢!此前論者談到“徐何創(chuàng)作之爭”時,都沒有提及這個事實,不知道是沒有看到過原書,還是疏忽之故。何家槐在暨南大學的同學溫梓川在“徐何創(chuàng)作之爭”發(fā)生20多年寫作的《“徐何事件”的內(nèi)幕》(見《文人的另一面》,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中仍然表示,“在這場風波發(fā)生之前,家槐曾先后出版了兩本小說集,一本是《曖昧》,一本是《竹布衫》,可是這兩本小說集都沒有收進徐轉(zhuǎn)蓬的作品。”把想當然當作事實,并稱為“內(nèi)幕”,如不糾正,以訛傳訛,難免誤為“定論”。
至于“偷稿”一事曝光后,何家槐不去反省自己的錯誤,反而心存僥幸,相當一段時間里無視事實,且文過飾非,堅稱“文章私相授受的勾當,卻是絕對沒有的”,導致一件本來簡單的文字糾紛復雜化,甚至超越“海派”、“京派”的分歧,演變成一場泛政治化的攻訐,難免遭遇借題發(fā)揮之人在其中火上澆油。試想,如果何家槐事發(fā)之后立即坦陳錯誤,不授人以柄,又會是如何一個局面?
(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現(xiàn)代文學研究學者周正章先生的指點,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