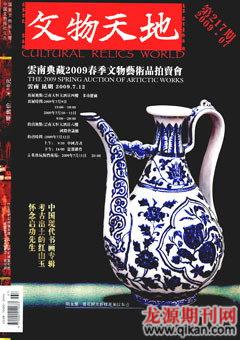手校丹黃八千卷 書香縈繞思藏園
董 蕊 趙 前
“海內外之言目錄者,靡不以先生為宗。”(倫明撰《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誠如斯言,傅增湘先生為近代國內藏書大家之一,一生勤于訪求,收藏宏富。與其他藏書家不同的是,傅增湘先生不但藏書,且精于校書,并以校勘與傳播為己任,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堪稱一代宗師。
訪書不計代價,“雙
鑒”得之不易
傅增湘(1872—1949),字潤沅,號沅叔,別署雙鑒樓主人、藏園居士、藏園老人、姜弁、書潛、清泉逸叟、長春室主人等。四川扛安縣人。十六歲時應順天鄉試為舉人。二十六歲時中戊戌(即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科二甲第六名進士,選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曾人王士珍內閣任教育總長。1927年擔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解放之初,周恩來曾派人持函探望重病中的傅增湘,遺憾的是未及相見,傅先生就去世了。
傅增湘先生一生與書有著不解之緣,訪書、收書、校書、印書幾乎構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內容,他這份愛書的執著之情令人崇敬。
辛亥革命爆發后,傅增湘受袁世凱的委任,參加唐紹儀領導的議和代表團南下議和,其間,他曾用百金買到了一部宋版書《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這是他生平所購第一部宋版書,十分珍惜。然而經張元濟先生鑒定,此書為清朝皇家編修《四庫全書》時所用的底本,經編修館臣篡改刪落,不具原貌。傅增湘深感痛惜,于是便更加發憤購書。
“五四運動”期間,北洋政府主張解散北京大學,欲追究北大校長蔡元培策動、包庇學生的責任,逼蔡離職。傅增湘辭職以示抗議,后定居北京,專心于收藏圖書,校勘典籍。取蘇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詩意,將其藏書處命名為“藏園”,自號“藏園居士”。傅增湘一生勤于訪書收書,往往不辭辛苦,不計代價。得知某地有善本,即使長途跋涉,也必求一得。其薪金大部分都用來買書,資金不足時不惜借債,也要將好書收回,有時不得不賣舊換新。
民國十七年(1928年),傅增湘賣掉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鮮古刻本三篋,購得曾為盛昱藏書之冠的《洪范政鑒》(圖二)。此書為南宋淳熙十三年宮廷寫本,內容是記天人感應之事,以警示統治者,是南宋內廷遺留下來的一部完整的寫本書。七百多年間,它一直在內府保存,民國初年才流落民間。其書筆法清勁,玉楮朱欄,有內府璽印,確實為罕見珍寶。在此之前,傅增湘還購得一部南宋紹興二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刊本《資治通鑒》(圖三),該書為前清鄂撫端方的舊藏。傅增湘將這部《資治通鑒》與祖傳的元刊本《資治通鑒音注》相配,把自己的藏書之所命名為“雙鑒樓”。自從《洪范政鑒》入藏之后,便代替了元本《資治通鑒音注》,成為雙鑒樓的“雙鑒”之一。
民國初年新舊鼎革之際,不少滿族權貴、藏書故家的藏書紛紛散出。如端方“訇齋”、盛昱“郁華閣”、景廉“半畝園”、楊氏“海源閣”以及徐坊、吳重熹、楊守敬、繆荃孫、費念慈等藏書家的藏書先后源源不斷地歸人“雙鑒樓”。傅增湘不僅勤于在各書肆訪求善本古籍,而且常與其他藏書家以書易書。在傳世可見的傅氏書信中,就真實地反映了這一點。傅增湘與當時的許多藏書家有著廣泛的交往,他們當中有曹元忠、王雪澄、繆荃孫、吳昌綬、徐乃昌、劉承斡、葉德輝、鄧邦述、蔣孟蘋、袁克文、董授經、陶蘭泉、張鈞衡、章式之、周叔等。他們之間經常互通有無,或相互饋贈,或代為搜求。經過數十年孜孜不倦的苦心經營和辛勤積累,傅增湘的藏書總計達二十萬卷以上。書目載人《雙鑒樓善本書目》《雙鑒樓藏書續記》以及四十年代編成待刊的《藏園續收善本書目》中。雙鑒樓的藏書無論數量之多,還是質量之高,都堪稱一時冠冕。由此,成為繼陸氏百百宋樓、丁氏八千卷樓、楊氏海源閣、瞿氏鐵琴銅劍樓清末四大家之后全國最大的藏書家之一。
以校讎古籍、傳播文化為己任
傅增湘坐擁書城,是出于對古籍的摯愛。他每得一書,就撰寫題跋一篇,無法得到的也要借來校對一次。他規定自己每天校書三十葉,白天時間不夠用,就熬到深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與古籍有特殊的緣分,校讎之功似與生俱來,“如寒之索衣,饑之思食,如無一日之可離”(見《文苑英華》校本書后)。到了晚年,傅增湘仍日日伏案校書,有時通宵不眠。即使在嚴寒的冬天和炎熱的暑夏,他也堅持工作,不肯間斷。七十歲以后,還堅持校完《文苑英華》這部千卷巨著。傅增湘綜計平生所校群書八千余卷,是民國以來校勘古書最多的人。
傅增湘在校勘的同時,還對版本源流、優劣加以探討。先生曾遍訪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江南圖書館(原丁氏八千卷樓)、故宮圖書館、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經常流連于北京的琉璃廠、隆福寺書肆;還曾東渡滄海,遍觀日本宮內省圖書寮、內閣文庫、東洋文庫、巖崎氏靜嘉堂、內藤氏恭仁山莊、前田氏尊經閣和西京諸古剎所藏的珍貴的宋元善本。他訪書時必攜筆記及一部莫友芝撰《(呂耳)亭知見傳本書目》,并將各書行款、序跋、碑記等記于《鄙亭知見傳本書目》上,以便檢校核對,題名為《雙鑒樓主人補記鄙亭知見傳本書目》。另外,他還將所見善本,撮其大要,詳記于筆記簿上,題名《藏園瞥錄》。數十年中,《藏園瞥錄》集至40余冊,《(呂耳)亭書目》也批注殆滿。他閱覽了日本公私各家所藏的善本之后,撰寫了《藏園東游別錄》,將所見善本加以甄別,并對一些刊刻年代晚而誤為宋元刻本的古籍,以及個別宋元珍籍,誤認為后來刊刻的,——加以訂正。當時的日本學者,對他的這些意見都很重視。先生對自藏或所見善本,撰寫長跋,詳論版本源流、文字得失、流傳經過,共500余篇,50多萬言。編為三集,題名《藏園群書題記》。先生學識既精且博,再加上多年博覽,對版本的時代源流、鑒別真偽極為精審,往往發人所未發,詳人所不能。
傅增湘關于目錄學、版本學方面的著述頗多。其中著名的有《雙鑒樓善本書目》四卷,1929年刊刻,著錄傅氏自藏善本一千二百多種;《雙鑒樓藏書續記》二卷,1930年刊刻,著錄善本五十一種;《藏園群書題記》初、續集連同未刊的第三集,經傅熹年整理,匯為一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傅增湘的另外兩部重要著作《藏園群書經眼錄》和《藏園訂補亭知見傳本書目》生前均未能出版,都是近年來經先生文孫傅熹年整理,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的。其中《藏園群書經眼錄》一書系由《藏園校書錄》、《藏園瞥錄》、藏園日記、雜稿等匯為十九卷,收書四千五百多種,共計百余萬言。《藏園訂補郜亭知見傳本書目》共補入書目八千九百五十余條。這兩部書是近百年來目錄學、版本學方面集大成的著作。
傅增湘不僅藏書、校書,而且還樂于刊布古書,使之化身千百,流傳于世,供學人研究使用。先生藏書多為珍
本秘籍,但他并沒有秘不示人,相反認為典籍與文化應流傳后世,發揚光大。先生自藏古籍“傳播者十居四五”,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上無負于古人,而下亦自慰其辛苦”。基于這種信念,他為涵芬樓先后提供過古籍善本數十種供其影印出版,以廣流傳。其中《四部叢刊》初編、續編影印時,就曾向他借用善本書數十種;《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也有多種取自“雙鑒樓”。此外,先生還為同時代的學者朱祖謀、徐乃昌、董康、陶湘、吳昌綬等人刊布古籍提供過底本。
傅增湘自己也刊印過大量古籍善本:1916年收得宋版《資治通鑒》后,便立即影印流傳;1934年借貸一萬三千元巨款,購得著名紹興監本《周易正義》(圖四),此書曾為臨清徐氏所藏,秘不示人,更無論借印,先生將其影印行世,而后售去原書抵債;此外,還有《方言》、《劉賓客文集》、元本《困學紀聞》以及明本《永樂大典-臺字韻》等。不僅如此,先生出于思鄉之情,對故鄉文獻和先賢著述也勤加搜尋。他花了十多年的時間,輯印成《宋代蜀文輯存》一百卷,收錄四百五十位四川鄉賢的文章二千六百余篇。
晚年,先生雖已無力校勘與刊印古籍時,但仍堅守將古籍與文化流傳于世、發揚光大的信念,不僅籽手校群書捐贈給北京圖書館,而且囑咐后人把珍藏的“雙鑒”也獻給國家。又因祖籍是四川,他的家人秉承遺志,將其外庫書籍三萬四千余冊捐贈給四川,現藏于重慶圖書館與四川大學。
緣為書來——傅增湘與圖書館
出于對書的深厚感情,傅增湘先生與圖書館也有著緊密聯系和特殊的情誼。
早在傅增湘出任直隸提學使時,他就認識到“興學為立國根本之圖,普通、專門既具設矣,益不得不為保存國粹之舉,則圖書館尚焉”(引《天津直隸圖書館書目》傅增湘自序)。當時的直隸省圖書館,建館時間不長,除嚴范孫等人捐贈的藏書外,藏書尚不豐富。于是傅增湘四處籌資,用巨款收購北京琉璃廠書估李寶泉南下江浙訪求到的一大批善本書,包括李氏小李山房、丁氏八千卷樓和劉氏嘉業堂等名家珍藏,總計多達12萬余卷。他還為館購得英文圖書300余冊。傅增湘在竭力訪求各類圖書以補充館藏的同時,還著手將館藏圖書編成目錄。他說:是館“經營締搏,遂以有成。顧卷帙浩繁,編目匪易”。他先后組織譚新嘉和韓梯云編目,書目告成后興奮不已,為書目撰寫一篇序文,說此目“義例翔明,區分有法,雖不能企七閣四庫之類備,以例夫新編之《江寧圖書館書目》,固以南北遙相輝映矣”。這是天津圖書館第一部古籍書目,收書12755種,其中明版書1000余部,抄本逾500部,尤以史、集兩部書居多。
這段經歷可以算作是傅增湘與圖書館結緣之始,此后,他在訪書過程中,曾遍訪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江南圖書館(原丁氏八千卷樓)、故宮圖書館等地,始終沒有中斷與圖書館的聯系。到了晚年,他自知不能再行校勘,而且深切感到私人收藏書籍不利于長期保護,于是決定將其藏書捐贈于北京圖書館。據傅熹年《記先祖藏園老人與北京圖書館的淵源》一文中介紹,傅增湘于1947年將生平所校群書捐贈北京圖書館,“除早年流散和零星校在大型叢書中者外,家中只留三數種傳示子孫,其余全部在內。據當時點交清冊為337種,3581冊。”1948年,傅增湘又一次向北京圖書館捐讓明刊本及名家鈔校本約79種。他辭世后,長子傅忠謨先生秉承遺志,先后幾次將285種宋元鈔校善本讓歸北京圖書館。其中包括被視為傳家之寶的“雙鑒”——宋內府寫本《洪范政鑒》和宋刻本《資治通鑒》。在捐贈“雙鑒”時,家人把他用過的寫字臺、椅子、鎮紙、香爐、文房四寶、畫像(徐悲鴻作)(圖一)等一并捐給了國家圖書館。
提到徐悲鴻為傅增湘所作的畫像,就不得不提二人的一段友誼。傅增湘從事教育多年,一貫憐才愛士。他出任教育總長時,徐悲鴻曾帶著自己的作品去拜訪他,希望能爭取到公費留學法國的機會。傅增湘看了徐的作品后,大加欣賞,表示一定幫忙。然而,第一批公費留法的名額被人從中篡改,徐悲鴻無緣此次留法。徐悲鴻認為自己受了愚弄,寫信詰問傅增湘。先生也為擠占名額一事氣憤不已,承諾第二批一定努力幫助他。徐悲鴻本以為第一次名額被權勢擠占,又以如此惡劣的態度對待傅先生,肯定再無希望。沒想到在不久公布的第二批公費留法名單中,他榜上有名,這時才明白傅先生的一片苦心,于是親自前往致謝。此后,二人成了摯友。徐悲鴻學成歸國,又去拜訪傅增湘,提出要為其畫像,以表心意,先生慨然允諾。這幅畫像是徐悲鴻油畫肖像中的得意之作,流傳至今,見證了二位先生之間的深厚友誼。
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十分珍視傅增湘先生的遺物,專辟一處用來擺放。每當有幸在此處駐足停留片刻,都不禁感慨萬千,仿佛依稀可見先生坐擁書城、勤奮校書的情景,也仿佛能感受到先生沐浴焚香方能讀書的那份對書的敬意。
書乃傅增湘先生畢生摯愛之物,選擇了國家圖書館作為其最終歸宿,可謂是書緣使然。其實,先生與國家圖書館的緣分可以追溯到更早。可以說,先生與國家圖書館四大專藏中的《四庫全書》和《永樂大典》都有著緊密的聯系。《四庫全書》是乾隆時期編修的一部大叢書,當時共抄寫了七部,分別存放于南北方的七閣中,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是文津閣《四庫全書》(圖五)。當時的七部流傳至今只剩下三部半,其中當屬這套原藏于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最為完整,原架、原函、原書三位一體,完好無損,難能可貴。傳播與保存這部卷帙浩繁的文化珍品,一直是近代有識之士的心愿。張元濟倡議印行《四庫全書》,但付印之事屢遭中輟,此間,張元濟曾致函好友傅增湘吐露心聲說:如此一大事因緣,自然不能不有許多魔障,但使吾輩力行不懈,終當有登彼岸之時。
筆者曾求教于傅先生的文孫傅熹年先生,據傅熹年回憶,傅增湘當年曾打算影印《四庫全書》,但在此之前,先將自己手中的一冊《永樂大典》影印流傳,作為影印《四庫全書》前的一次準備和嘗試。《永樂大典》(圖六)是明永樂元年至六年(1403-1408)太子少師姚廣孝和翰林學士解縉等奉敕組織3000多人歷時四年編纂成的大型類書。永樂十九年,朱棣遷都北京,《永樂大典》也隨之運到北京,存放于宮城內的文樓。嘉靖三十六年(1557),宮中發生火災,三殿和文、武兩樓等主要建筑均被焚毀。幸虧搶運及時,《永樂大典》才逃過一場浩劫。之后,嘉靖皇帝命人將《永樂大典》摹錄了一套副本,單獨保存,以備不測。副本與正本的格式、裝幀都完全一致。明亡之后,正本下落不明。副本也屢遭厄運,因為官吏的竊取、英法聯軍的劫掠、八國聯軍的焚毀,最后散佚甚巨。宣統元年(1909)籌建京師圖書館時,只剩下64冊了。《永樂大典》是一部杰出的大百科全書,匯集了先秦至明初七八千種圖書,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文獻資料。傅增湘深知其價值巨大,首部《永樂大典》的仿真影印本就出自于先生之手,這可以算作是影印《永樂大典》的先河。當時的影印本現今存放在國家圖書館。
雖影印《四庫全書》未果,但欲影印這部古代大書,已是氣魄和精神可嘉了。《永樂大典》影印本質地精良,書后還有先生當時寫的題記,可見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這些都無不傾注著先生的心血。1960年,中華書局將收集到的《永樂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1986年,又將征集到的近八百卷縮印精裝出版。傅增湘曾收藏的那本《大典》內容也被收錄其中。
傅增湘先生傾注畢生精力,收藏校勘古籍,研究版本目錄學。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先生從不將藏書秘不示人,而是致力于推廣流傳。先生不辭辛勞、執著訪求、勤于校勘的愛書之情令人欽佩;致力于將古籍與文化流傳于世,發揚光大的博大胸懷更令人崇敬。正是先生的這份對書籍對文化的執著,才留下了澤被萬代的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