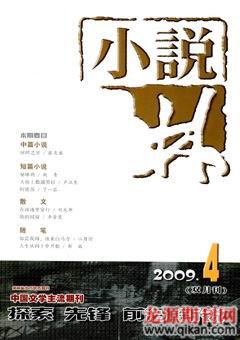在雨地里穿行
在雨地里穿行
那是什么?又白又亮,像落著滿地的蝴蝶一樣。不是蝴蝶吧?蝴蝶會飛呀,那些趴在淺淺草地上的東西怎么一動都不動呢!我走進草地,俯身細看,哦,真的不是蝴蝶,原來是一朵朵白色的花。那是一種奇特的花,它沒有綠葉扶持,從地里一長出來就是花朵盈盈的樣子。花瓣是蝶白色,花蕊處才有一絲絲嫩綠,真像是粉蝶展開的翅膀呢!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花朵閃閃爍爍,又宛如夜空中滿天的星子。
我們去的地方是肯尼亞馬賽馬拉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護區的面積大約是四百平方公里。在保護區的邊緣地帶,我注意到了那種大面積的野花,并引起了我的好奇。在陽光普照的時候,那種野花的亮麗自不待言。讓人稱奇和難以忘懷的是,在天低云暗、雨水淅瀝之時,數不盡的白色花朵似乎才更加顯示出其奪目的光彩。花朵的表面仿佛生有一層熒光,而熒光只有見水才能顯示,雨水越潑灑,花朵的明亮度就越高。我禁不住贊嘆:哎呀,真美!
北京已進入初冬,樹上的葉子幾乎落光了。地處熱帶的肯尼亞卻剛剛迎來初夏的雨季。我們出行時,都遵囑在旅行箱里帶了雨傘。熱帶草原的雨水是夠多的。我們驅車向草原深處進發時,一會兒就下一陣雨。有時雨下得還挺大,大雨點子打得汽車前面的風擋玻璃砰砰作響,雨刷子刷得手忙腳亂都刷不及。這么說吧,好像每一塊云彩都是帶雨的,只要有云彩移過來,雨跟著就下來了。
透過車窗望過去,我發現當地的黑人都不打雨傘。煙雨朦朧之中,一個身著紅袍子的人從遠處走過來了,乍看像一株移動的海棠花樹。待“花樹”離得稍近些,我才看清了,那是一位雙腿細長的赤腳男人。他沒打雨傘,也沒穿雨衣,就那么光著烏木雕塑一樣的頭顱,自由自在地在雨地里穿行,任天賜的雨水灑滿他的全身。草地里有一個牧羊人,手里只拿著一根趕羊的棍子,也沒帶任何遮雨的東西。羊群往前走走,他也往前跟跟。羊群停下來吃草,他便在雨中靜靜站立著。當然,那些羊也沒有打傘。天下著雨,對羊吃草好像沒造成任何影響,它們吃得專注而安詳。那個牧羊人穿的也是紅袍子。
我說他們穿的是袍子,其實并沒有袍袖,也沒有袍帶,只不過是一塊長方形的單子。他們把單子往身上一披,兩角往脖子里一系,下面往腰間一裹,就算穿了衣服,簡單得很,也易行得很。他們選擇的單子,多是以紅色基調為主,再配以金黃或寶藍色的方格,都是鮮艷明亮的色彩。臨行前,有人告誡我們,不要穿紅色的衣服,以免引起野生動物的不安,受到野生動物的攻擊。我們穿的都是暗淡的衣服。到了馬賽馬拉草原,我看到的情景恰恰相反,當地的土著穿的多是色彩艷麗的衣服,不知這是為什么。在我看來,在草原和灌木的深色背景襯托下,穿一件紅衣服的確出色,每個人都有著萬綠叢中一點紅的意思。
我們乘坐的裝有鐵柵欄的觀光車在某個站點停下,馬上會有一些人跑過來,向我們推銷他們的木雕工藝品。那些人有男有女,有年輕人,也有上歲數的老人。他們都在車窗外的雨地里站著,連一個打傘的都沒有。潔凈的雨滴從高空灑下來,淋濕了他們絨絨的頭發,淋濕了他們黑緞子一樣的皮膚,也淋濕了他們的衣服,他們從從容容,似乎一點兒都不介意。我想,他們大概還保留著先民的習慣,作為自然的子民,仍和雨水保持著親密的關系,而不愿與雨水相隔離。
在遼闊的野生動物保護區,那些野生動物對雨水的感情更不用說了。成群的羚羊、大象、野牛、獅子、斑馬、角馬、長頸鹿;還有禿鷲、珍珠雞、黃冠鶴等等,雨水使它們如獲甘霖,如飲瓊漿,無不如癡如醉,思緒綿長。你看那成百上千只美麗的黑斑瞪羚站在一起,黃白相間的尾巴搖得像花兒一樣,誰說它們不是在對雨水舉行感恩的儀式呢!有雨水,才會有濕地,有青草,有泉水。雨水是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生物生生不息的保障啊!
我們是打傘的。我們把精制的折疊雨傘從地球的中部帶到了地球的南端。從車里一走下來,我們就把傘打開了,雨點兒很難落到我們身上。有一天,我們住進馬賽馬拉原始森林內的一座座尖頂的房子里。雨下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彩虹出來了,雨還在下著。我們去餐廳用早餐時,石板鋪成的小徑雖然離餐廳不遠,但我們人人手里都舉著一把傘。餐廳周圍活動著不少猴子,它們在樹上輕捷地攀緣,尾隨著我們。我們在地上走,它們等于在樹上走。據說猴子的大腦與人類最為接近,但不打傘的猴子對我們的打傘行為似有些不解,它們仿佛在問:你們拿的是什么玩意兒?你們把臉遮起來干什么?
回想起小時候,在老家農村,我也從來不打傘。那時傘是奢侈品,我們家不趁一把傘。夏天的午后,我們在水塘里撲騰。天忽然下起了大雨,雨下得像瓢潑一樣,在塘面上激起根根水柱。光著肚子的我們一點兒都不驚慌,該潛水,還潛水;該打水仗,還繼續打水仗,似乎比不下雨時玩得還快樂。在大雨如注的日子,我和小伙伴們偶爾也會采一支大片的桐葉或蓮葉頂在頭上。那不是為了蔽雨,是覺得好玩,是一種雨中的游戲。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打起了雨傘。一下雨,我便用傘頂的一塊塑料布或尼龍布把自己和雨隔開。我們家多種花色的傘有好多把。然而,下雨的日子似乎越來越少了,雨傘好長時間都派不上用場。如果再下雨,我不準備打雨傘了,只管到雨地里走一走。不就是把頭發和衣服淋濕嘛,怕什么呢!
2009年3月12日于美國華盛頓州奧斯特維拉村
參天的古樹
那是一棟獨立的別墅,我住在二樓的一間臥室。臥室的窗戶很寬大,窗玻璃明得有如同無。然而這樣的窗戶卻不掛窗簾。我只須躺在床上,便把窗外的景物看到了。窗外挺立著一些參天的古樹,那些古樹多是杉樹,也有松樹、柏樹和白樺等。不管哪一種樹,呈現的都是未加修飾的原始狀態,枝杈自由伸展,樹干直插云天。一陣風吹過,樹冠嘯聲一片。一種寶藍色的鳳頭鳥和一種有著玉紅肚皮的長尾鳥,在林中飛來飛去,不時發出好聽的叫聲。我看到的更多的是舉著大尾巴的松鼠,它們在樹枝間躥上跳下,行走如飛,像鳥兒一樣。松鼠是沒長翅膀的鳥兒。它們啾啾叫著,歡快而活潑。它們的鳴叫也像小鳥兒。樹林前面,是一片開闊的草地。和草地相連的,是蔚藍色的海灣。海灣對面,是連綿起伏的雪山。
把目光拉回,我看到兩只野鹿在窗外的灌木叢中吃嫩葉。它們一只大些,一只小些,顯然是一對夫妻。我從床上下來看它們,它們也回過頭來看著我。它們的眼睛清澈而美麗,毫無驚慌之意。墻根處綠茵茵的草地上突然冒出一堆蓬松的新土,那必是能干的土撥鼠所為。雪花落下來了,像是很快便為褐色的新土堆戴上了一頂白色的草帽。
是的,那里的天氣景象變化多端,異常豐富。一忽兒是云,一忽兒是雨;一陣兒是雹,一陣兒是雪;剛才還艷陽當空,轉瞬間云遮霧罩。雪下來了。那里的雪花兒真大,一朵雪花兒落到地上,能摔成好多瓣。冰雹下來了。碎珍珠一樣的雹子像是有著極好的彈性,它打在涼臺的木地板上能彈起來,打在草地上也能彈起來,彈得飛珠濺玉一般。不一會兒,滿地晶瑩的雹子就積了厚厚一層。雨當然是那里的常客,或者說是萬千氣象的主宰。一周時間內,差不多有五天在下雨。沙沙啦啦的春雨有時一下就是一天。由于雨水充沛,空氣濕潤,植被的覆蓋普遍而深厚。樹枝上,秋千架上,繩子上,甚至連做門牌用的塑料制品上,都長有翠綠的絲狀青苔,讓人稱奇。
那個地方是美國華盛頓州西南海岸邊的一個小村,小村的名字叫奧斯特維拉。我和肖亦農先生應埃斯比基金會的邀請,就是住在那個環境優美的地方寫作。過去我一直認為,美國是一個發達國家,也是一個年輕國家,不過到處都是高樓大廈,沒有什么古老的東西。這次在那里寫作,我改變了一些看法,發現古老的東西在美國還是有的。美國雖然年輕,但它的樹木并不年輕,美國不古老,那里生長的樹木卻很古老。肯定是先有了大陸、土地、野草、樹木等,然后才有了美國。看到一棵棵巨大的蒼松古柏,你不得不承認,美國雖然沒有悠久的人文歷史,卻有著悠久的自然生態歷史。而且,良好的自然生態就那么生生不息,一直延續了下來。這一點,看那漫山遍野的古樹,就是最好的證明。
出生于本地的埃斯比先生,為之驕傲的正是家鄉詩一樣的自然環境。他自己寫了不少贊美家鄉的詩歌,還希望全世界的作家、詩人、劇作家、畫家等,都能分享他們家鄉的自然風光。在一個春花爛漫的上午,和煦的陽光照在草地上,埃斯比突發靈感,對他的朋友波麗說:咱們能不能成立一個基金會,邀請全世界的作家和藝術家到我們這里寫作呢?埃斯比的想法得到了波麗的贊賞,于是,他們四處募集資金,一個以埃斯比命名的寫作基金會就成立了。基金會是國家級的社團組織,其宗旨是為全世界各個流派的作家和藝術家提供不受打擾、專心工作的環境。基金會鼓勵作家和藝術家解放自己的心靈,以勇于冒險的精神重新審視自己的寫作項目,創作出高端的文學藝術作品。
基金會成立以來,在過去的九年間,已有蘇格蘭、澳大利亞、尼泊爾、加拿大、匈牙利等六七個國家和地區的九十五位作家、藝術家到奧斯特維拉創作。他們都對那里的居住和創作環境給予很高評價,認為那里寧靜的氣氛、獨處的空間、優美的自然風光,的確能夠激發創作活力。
我由衷敬佩埃斯比創辦基金會的創意。他的目光,是放眼世界的目光。他的胸懷,是裝著全人類的胸懷。他的精神,是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有了那樣的精神,他才那么給自己定位,才有了那樣的創意,才舍得為文化藝術投資。他的投資不求回報,是在為全世界的文化藝術發展作貢獻,在為人類的精神文明作貢獻。埃斯比的舉動堪稱是一個壯舉。
一九九九年,埃斯比先生逝世后,波麗繼承了他的遺志,繼續發展基金會的事業,不斷擴大基金會的規模。基金會擴建基礎設施的近期目標,是每年至少可以接待32位作家、藝術家到那里生活和創作。波麗一頭銀發,大約七十多歲了。她穿著紅上衣,額角別著一枚蝴蝶形的花卡子,看去十分俏麗,充滿活力。她對我們微笑著,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奶奶。她在互聯網上看到對我們的介紹和我們的作品,向我們深深鞠躬,讓我們十分感動。
由中國作家協會推薦,經埃斯比寫作基金會批準,我和肖亦農有幸成為首批赴奧斯特維拉寫作的中國作家。一在樹林中的別墅住下來,我就體會到了那里的寧靜。我們看不到電視、報紙,也沒有互聯網,幾乎隔斷了與外界的信息聯系。那里樹多鳥多,人口稀少。我早上和傍晚出去跑步,只見鳥,不見人;只閱花兒,不聞聲。天黑了,外面漆黑一團,只有無數只昆蟲在草叢中合唱。在月圓的夜晚,我們踏著月光出去散步,像是聽得到如水的月光潑灑在地上的聲音。寫作的間隙,我平躺在客廳的沙發上,看著掛在涼棚屋檐下由道道雨絲織成的雨簾,一時不知身在何處,寧靜而幽遠的幸福感從心底涌起。不能辜負埃斯比寫作基金會的期望,亦不能辜負那里優美的自然環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我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兩篇散文,記了兩萬多字的日記,還看完了三本書。
我們剛到那里時,杏樹剛冒花骨朵兒。當我們離開時,紅紅的杏花已開滿了枝頭。
2009年3月26日于美國華盛頓州奧斯特維拉村
黃梅少年
去年秋天到湖北看黃梅,轉眼一年過去了。每每想起黃梅之行,有一件小事縈繞于心,不記下來像欠了一筆賬似的。不是欠別人的賬,是欠自己的。
那天上午參觀四祖寺。四祖認為,修行并不神秘,日常生活就是修行,種田就是修行。一邊種田,一邊修行,自食其力,方可修行得好。我受到啟示,想到寫作也是一種修行。修行需要靜心,安心,專心,一個人一輩子只干好一件事就行了。這與寫作的道理是相通的。
接著參觀毗廬塔。據說此塔建于唐代,是四祖寺前唯一一座唐代建筑遺存,不可不看。我們拾級而上,一座方型的白塔赫然矗立在我們面前。同行的朋友們,有的駐足對塔仰視,有的繞著塔轉,有的選角度在塔前照相。我卻一眼在塔側的松樹下看到一位少年。松樹根部建有水泥方池,那少年在池沿邊靠坐著。我走過去一看,見少年用短扁擔挑了兩只蛇皮塑料袋子,一只袋子里裝滿香品,另一只袋子里裝的是礦泉水之類的飲料。顯然,這些東西都是準備賣給香客和游客的。我們走過來時,已經看見有人在路邊擺開了攤子,在賣同樣的東西。可是,少年為何躲在一邊,不把東西拿出來賣呢?我猜,少年可能在等一個人,等的人十有八九是他的奶奶,等奶奶來到之后,由奶奶把東西拿出來賣。我猜的沒錯,一問,少年果然是在等他奶奶。他們的家離這里比較遠,又都是山間小路,他挑著擔子走得快,奶奶走得慢,他就提前來到了。秋季開學后,少年剛上小學四年級。這天是星期六,少年不上課,就幫奶奶挑東西上山。少年的眉眼挺清秀的,只是有些瘦弱,臉色也有些發黃。
初小玲也過來了,俯著身子,關切地看著少年,輕聲和少年交談。少年很羞怯的樣子,初小玲問一句,他就答一句,不問,他就不說話,還低著頭,低著眉,不敢看人。我聽出來了,少年的父母都在杭州打工,家里剩他一個人,只好跟著奶奶過活兒。在我國農村,目前有數以千萬計的留守少年兒童,這位少年無疑是其中的一個。我的老家也在農村,對農村留守兒童的情況知道一些。在我二姐那村,有一個孫子留給爺爺看管。一天午后,孫子掉進水井里淹死了。爺爺把孫子放到床上,摟著孫子,自己喝下農藥也死了。還有一個當奶奶的,腿上有殘疾。當聽說孫子掉進了河里,她一邊往河邊爬,一邊喊人救她的孫子。孫子被人送到醫院搶救,奶奶在家里準備好了農藥,一旦孩子救不活,她也不活了。幸好,孫子被救過來了,奶奶才沒有死。沒有死的奶奶接著看孫子。想想那些留守兒童,看看眼前這位從小就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少年,我心一里一酸,淚水頓時涌滿了眼眶。我控制著,沒讓眼淚流出來。一個人老大不小了,動不動就流眼淚,顯得感情太脆弱,也容易讓朋友們笑話。
少年的奶奶還沒來,我有些等不及了,想幫少年的生意開一下張。我問他礦泉水賣不賣?他說賣。我指著一瓶娃哈哈礦泉水,問多少錢一瓶。他說兩塊。我給了他兩塊錢,他給我拿了一瓶礦泉水。我自己買一瓶少了點,還想幫少年推銷。我問孫郁喝不喝水,孫郁把手中的礦泉水瓶舉了一下,說他已經有了。孫郁瓶中的礦泉水所剩不多,他很快領會了我的意思,之后三口兩口把水喝完,把空瓶給了少年。少年面露欣喜,很快把瓶子接過去了。看得出來,少年知道空瓶子也能賣錢,他對空瓶子是在意的。我見陳戎沒拿礦泉水,把她喊過來,執意給她買一瓶。娃哈哈礦泉水沒有了,只有純凈水。我問少年:“純凈水也是兩塊錢一瓶吧?”我這樣問,若是生意油子會順水推舟,會說是的。可少年說:“不是,純凈水一塊五一瓶。”我沒有零錢,照樣掏出兩塊錢給少年。少年也沒有零錢找給我,他的樣子有些為難。我說:“算了,不用找了,就算也是兩塊錢一瓶吧。”
繞過毗廬塔往上走,山上還有更高的建筑。我們登到高處,舉目遠眺,見天是那么藍,云是那么白,山是那么青,水是那么綠。山下有大塊的棉田,棉田里開遍了溫暖的花朵。田埂上有水牛在吃草。烏鴉翩然飛來,落在水牛背上。烏鴉一落在牛背上,似乎就凝固下來,凝成了一幅畫。在河邊和水渠邊,婦女們在那里洗衣,漂衣。他們洗好的衣物,就手展開,搭在岸邊叢生的茅草上晾曬。在秋陽的照耀下,那些衣物五彩斑斕,十分亮麗。這里那里種了許多橘子樹,橘子已經熟了,綠中帶黃的累累碩果壓彎了枝頭,幾乎墜到地上。黃梅真是一個美麗的地方,難怪禪宗的前三位祖師四處云游,沒有固定居所,直到四祖、五祖才在黃梅選址建寺,有了弘揚佛法的固定場所。
我們下山原路返回。走到塔前的一個攤位邊,一位老奶奶攔住了我。我正不知怎么回事,老奶奶說:“你買水多給了五毛錢,我孫子告訴我了。不找給你錢了,給你幾個橘子吧!”說著,兩手各抓著兩個大橘子往我手里塞。我一看,可不是嘛,那少年正站在攤位后邊不聲不響地看著我。我不能接受老奶奶給我的橘子。再說,五毛錢也值不了這么多橘子呀。我連說不要不要,我們已經買了橘子。緊走幾步,把老奶奶躲開了。
走了一段回頭看,那少年還站在那里看著我。不難想象,少年的奶奶一趕到,少年就把我多付了五毛錢的事對奶奶講了,而后,少年哪里都不去,一直在那里等我。一看到我,他就對奶奶把我指出來了。
這個黃梅少年啊,讓人怎能忘記你呢!
2008年10月8日于北京
作者簡介:劉慶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農村。當過農民、礦工和記者。著有長篇小說《斷層》《遠方詩意》《平原上的歌謠》《紅煤》等六部,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走窯漢》《梅妞放羊》《遍地白花》《響器》等二十余種,并出版有四卷本劉慶邦系列小說。
短篇小說《鞋》獲1997年至2000年度第二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神木》獲第二屆老舍文學獎。中篇小說《到城里去》和長篇小說《紅煤》分別獲第四屆、第五屆北京市政府獎、獲《北京文學》獎六度,《小說選刊》獎三度,《小說月報》百花獎二度,《十月》文學獎二度,《人民文學》獎二度,全國煤礦文學烏金獎四度等。根據其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第53屆柏林電影藝術節銀熊獎。曾獲北京市首界德藝雙馨獎。
多篇作品被譯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等外國文字。
劉慶邦現為中國煤礦作家協會主席,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一級作家,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
特邀推薦 馮 晏
責任編輯 晨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