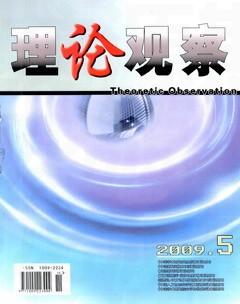發展:在人與自由之間
陳秀娟
[摘要]同樣是基于對人、對自由的深情關懷,對發展中國家現實問題的深切關注,阿馬蒂亞·森與卡爾·馬克思之間,如此相似,卻也各有持重。兩者最終都把目標指向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讓個人自由成為了“自由聯合體”或社會的承諾。但是,森與馬克思之間,人與自由·和諧發展何以可能,社會又如何承諾個人自由與發展,其側重點是不同的。
[關鍵詞]自由;人;和諧社會;阿馬蒂亞·森;馬克思
[中圖分類號]B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234(2009)05-0055-02
對普通公民而言,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了,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那么就意味著發展了;社會公共設施改善了,也就更意味著發展了。但是,阿馬蒂亞·森卻視角獨特,他直接把發展上升到自由的高度,說:“發展可以看作是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至于前面所說的關于收入水平提高、技術進步、社會現代化等等的觀點,那只是狹隘的發展觀。
一、關注自由:以自由看待發展
“自由”這一概念在阿馬蒂亞·森那里,既有空前的高度,也有最低的起點,具有明顯的“眼高手低”的特征。之所以說他“眼高”,是因為森直接就認為“自由”才是發展的首要目的,經濟增長僅僅是狹隘的一方面。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我們非常明顯地看到,森對自由的持重。更可貴的是,他所關注的自由,并非虛假的字面上的自由,而是“實質上的自由”,即“享受人們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的可行能力”。具體上來說,“實質自由包括免受困——諸如饑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過早死亡之類——的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夠識字算數、享受政治參與等等的自由。”n,為什么把“自由”或“實質自由”作為發展的首要目的呢?森直接點明原因:自由所具有的“評價性原因”(對進步的評判必須以人們擁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進為首要標準)和“實效性原因”(發展的實現全面地取決于人們的自由的主體地位)就決定了它在發展過程中居于中心地位。他舉例,對于一個期望長生不老的人——瑪翠依來說,即使她擁有全世界的財富,她本身感覺可能也是不自由的,因為她并沒有享有到她所珍視的向往的那種生活。在中國古代的皇帝中,這種現象也常有所聞。有人甚至建議把對GDP的關注轉向對國民幸福指數(GHP)。所以森認為,發展的最終目的就是擴展自由。
之所以說他“手低”,從阿馬蒂亞·森對自由手段性的分析、對“可行能力”的探討、對貧困饑荒的關注以及他本人所具有的濃厚的“現實關懷”和“問題意識”中,原因即顯明朗化。在森那里,自由不僅僅是發展的目的,他還強調“自由是促進發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他具體分析了五種手段性自由:政治自由、經濟條件、社會機會、透明性擔保、防護性保障。這些工具性自由能幫助人們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們在這方面的整體能力,同時它們也相互補充。在分析這五種工具性自由中,他對民主與饑餓、貧困與可行能力的關注是十分值得我們學習的。關于民主與饑餓。森表示:“饑荒從來沒有發生在以下國家:獨立,舉行常規的周期性選舉,有反對黨提出批評,允許報界自由報道、并可對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問而不受嚴密審查的國家。”按照他的說法,饑荒不會發生在民主社會中,只發生在專制統治下,其中對中國文革時期的饑荒也作了分析。關于貧困與可行能力“一個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種自由。是實現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的實質自由。”他通過論證表明,貧困不僅僅是收入的低下,更是對可行能力的剝奪。例如,對于一個生活在富裕國家的窮人來說,他可能因為無法進入上層社會而失去參與政治生活的可行能力,這種現象在西方世界名著中常常有所體現。另外,在這“眼高”與“手低”之間,森對婦女兒童等弱勢群、對發展中國家、對被壓迫的底層人民的關注,關注他們的經濟條件與政治自由、關注他們的主體地位與生活需要、關注他們的社會福利與可行能力,這一系列活動和大量的研究無不深深地體現了他濃厚的“現實關懷”和“問題意識”,真正貼近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可以說,森把他對“自由”的持重都落到了“人”這個主體身上,他是非常關心人的。
二、關懷人:以發展促進自由
同樣是出于對人、對人的自由的關懷,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關注,一下子拉近了阿馬蒂亞·森與馬克思這兩位在不同國家,不同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思想家之間的距離,馬克思指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在這里所講的“人的發展”不是指“集體”和“社會”,而主要是講個人,是個人作為類存在物、社會存在物的發展,或者說是個人身上的類特征、社會特征的發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更是馬克思、恩格斯等所追求的終極價值目標。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敘述“三大社會形態”理論時指出,伴隨著人的活動和社會關系的變化,人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而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由此不難看出,他們兩人都把發展的目標指向,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但是至于如何實現自由發展,兩人各有所側重。森側重以個體實質自由的角度,他認為自由是促進發展的重要手段,也即是在上面所敘述的五種工具性自由。但馬克思則更注意從宏觀實踐和經濟基礎的角度。一方面,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實現,還是在于人的實踐活動。人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斷開發自己的潛能、提高自身的能力、擴展社會關系等各方面,最終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另一方面,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發展生產力是推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根本途徑。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其實,對于社會或國家而言,實現個人自由全面發展與實現社會發展是息息相關的,沒有個人的全面發展,就不可能有社會的全面發展,同時,人的全面發展也只有在全面發展的社會中才能實現。因此,對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最終實現也要落腳于一個人與社會高度和諧發展的社會,也即是馬克思所說的那個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自由聯合體”,這樣一個“自由聯合體”(共產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是“建立在個人的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在這里,人與自由,和諧發展事實上已經成為了可能。
此時,森在闡述了他的自由發展觀后,也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提出了他的最后訴求:“讓個人自由成為社會的承諾。”那么放之于中國的現實下,作出這樣承諾的社會就是和諧社會。
三、和諧社會:以人為本,自由全面發展
和諧社會,經濟發展,讓人與自由,和諧發展逐步成為可能。
社會在個人自由的實現中的確承擔著重要的責任。特別是對某些弱勢群體,例如殘疾人,如果沒有社會給予幫助,他就難以生活,更談不上自由。又如“盲人道”的設置對盲人而言可是一根救命線。所以說“以人為本”是我們當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遵循的首要原則。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六個方面都蘊含著以人為本的思想,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國家關系的總概括。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人及其自由,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也要靠社會經濟發展。因此,可以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促進和提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和終極目標。二者是雙向互動的發展過程。共同統一于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之中。
總體上來說。堅持以人為本,才能更好地激發人們的創造活力。人是生產力在社會當中最活躍的力量,人越是得到全面發展,就越能為社會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和精神產品,就越能促進社會和諧。
另外,細細考察,我們可以驚奇地發現,阿馬蒂亞·森和馬克思所關注的某些問題域是非常相似的。包括“以人為本”、對人、人的實質自由以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重視、對個人自由實現的社會和社會發展承諾、對發展中國家的思考等,而且兩人都對某些現實問題和生存困惑表現了極大的關注。森最大的貢獻在于,把發展上升到自由的高度,讓我們深切明白到,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途中,不僅僅關注經濟增長,更要關注社會、政治進步;不僅僅關注富人福利,還應該注重社會保障弱勢群體;要合理配置教育資源,提高社會普通成員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可行能力。森濃郁的“中國關懷”也為解決某些中國問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如對教育安排、三農問題、災后重建問題都有參考價值。
[責任編輯: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