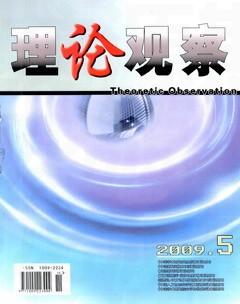大眾司法司法民主與司法正當性重建
許 可
[摘要]一場關于司法職業化、司法大眾化和民主化的討論在學界展開,而爭論實質在于如何在司法公信力削弱的背景下重建司法的正當性。盡管司法大眾化在過去很長的時期內保證了公眾對司法的信賴,但由于社經環境的變化,現在亟需一種與司法職業化相容的司法民主方式以實現司法正當性的重建。
[關鍵詞]司法民主;司法職業化;司法大眾化;司法正當性
[中圖分類號]D9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234(2009)05-0082-02
一場關于司法職業化、司法大眾化和民主化的討論在陳忠林教授、賀衛方教授、何兵教授等飽學法儒之間展開。由于爭論的議題與法官遴選、審判方式、法院作用乃至司法理念等問題息息相關,這場論爭遠不是言辭之爭或學理之爭,而是關乎“司法改革向何處去”的大問題。在各方聚訟紛紛之中,我們不妨先心平氣和地追問一句:何為“司法大眾化”和“司法民主化”?它們對當前司法改革的意義又是什么?
一、司法大眾化與司法正當性
1944年4月27日,毛澤東在同謝覺哉談論邊區司法問題時明確指出:“司法也該大家動手,不能只靠專間案子的推事、裁判員,還有一條規律:任何事都要通過群眾。”。毛澤東的這一論斷為肇始于上世紀四十年代陜甘寧邊區的“大眾司法”制度奠定了“群眾路線”的基調。新中國建立之后,人民司法對群眾路線的貫徹得到了進一步地提倡與發揚,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長沈鈞儒就強調指出:“人民司法工作,是依靠人民、便利人民、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人民司法工作者應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而群眾路線是人民司法的一個基本問題。”在群眾路線的指引下,民眾通過公開審判、就地審判、巡回法庭、人民調解、人民陪審、人民團體代理等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大眾司法制度廣泛參與到司法活動中來。正是在這種民眾對司法的參與下,民眾對法院和司法人員的隔膜得到了消解;對裁決實質正義的追求得到了回應;對黨和政策法規的認同感得到了增強。因此,大眾司法固然是鎮壓敵人的刀把子,而另一方面,它也是團結群眾的軟力量。通過硬軟結合的方式,大眾司法使得人民法院和人民政府成為群眾具體可感的形象,并最終在人民群眾內部完成了對司法權威和正當性塑造。
透過大眾司法和司法正當性的視角,我們不難發現當前對“大眾司法”的呼吁恰恰源于我國司法正當性的削弱。這種削弱從宏觀上體現為民眾對司法工作欠缺認同:2004年到2006年,在中央一級的人民信訪和上訪事件中,涉及到司法審判的上訪比例逐年增高,2006年約與行政違法行為上訪的比例相若。而在200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對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的反對票和棄權票合計比例竟超過20%;在微觀的層面上,則體現為民眾對法院裁決不認同:在2005年法院執結的1,439,235件案件中,強制執行431,803件,經執行人員以強制手段為后盾并反復告知利害關系(說服教育)后執行的1,007,432件,而在收到法院執行通知后即自覺自愿履行的案件幾乎為零。正是看到了民眾對法院和司法滿意度和服從度下降的事實,敏銳的觀察者才發出了回歸“大眾司法”的呼聲。
二、司法大眾化的困境
但問題是,即使人民群眾真的進了法院,即使我們學習繼承了“馬錫五審判方式”的大眾司法傳統。充分發掘出建國多年來大眾司法的經驗,切實貫徹了以“三個代表”思想為指導的“司法為民”理念,我們是否就能夠重新建立起當代的司法正當性?我想是不夠的。這不僅僅是因為“大眾司法”本身存在著嚴打、公開處決、游街示眾等“法律恐怖”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因為,傳統的“大眾司法”所依托的社經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被各階層的利益分野所取代,保衛勝利果實的政治目標被建構和諧社會所取代,大一統的意識形態被趨向多元的價值觀念所取代,高度組織化的人民群眾被日益增多的原子化個人所取代。簡單的生活、刑事糾紛被復雜的經濟、行政糾紛所取代。在國家轉軌的大變革中,大眾司法既無法從觀念上凝聚出民眾的一致意愿,也很難從制度運作上保證民眾對審判的有效參與。因此,無論人們厭惡還是欣喜,一種以法律人為基礎、以法律知識和技術為載體、以法律程序為外貌的司法方式最終成為現實的選擇,獨立、依法、專業的形式主義法院形象也逐漸成為法院在司法改革中的一種自我認同。
三、通過司法民主實現司法正當性
問題并沒有解決。大眾司法發現了病因,卻沒有開出切實可行的藥方。我們有必要在汲取大眾司法所蘊含的“民主價值”的基礎上,在更深入和更廣闊的視野內為中國的司法尋找救治之道:這就是“司法民主”。如果說大眾司法是中國的創造發明,那么司法民主則有著更為久遠的歷史。從古希臘的“陶片放逐”到英國中世紀的“陪審制”,再到當代對“司法責任”的強調,司法民主和政治民主一樣源遠流長。盡管關于司法民主的理論和制度紛繁蕪雜,“民眾參與司法”的本質是始終如一的。但“參與”并非僅僅意味著自發自愿的親自參與裁決(司法直接民主),它還意味著參與選擇別人代替我們裁決(司法間接民主)。密爾的話為后者作了精彩的辯護:“人民應該是主人,但是他們必須聘用比他們更能干的仆人。”司法間接民主將人民放在了監督者和最終制約者的立場上,通過選舉的“預期反應原理”、社會利益集團的互動關系以及有效裁決的制度性框架來控制法院的權力行使。與體現為陪審制度、參審制度以及中國特色“大眾司法”的司法直接民主相比,司法間接民主更加適應知識分化、人數眾多的現代社會,也有著更加靈活多樣的司法制度選擇。除了為人們所熟知的代表機關、新聞媒體、社會輿論對司法的監督外,當代民眾參與司法的廣度和深度已經大大拓展了:對法官選任的參與、對法官工作評價的參與、對法院審判的參與等民眾參與方式在強化司法責任的同時,回應了民眾對法院的民主要求。
(一)民眾對法官選任的參與
雖然漢密爾頓對民選法官心存憂慮,認為他們會因此屈從于大眾的輿論壓力而無法“忠實履行”其作為“有限的憲法的防御堡壘”的艱巨職責。但到2003年為止,美國僅有11個州還延續著行政長官和立法者任命法官的模式,而大多數州則采取了選舉和“混合制”的推選制度。后者是指司法提請委員會提名的候選人由州長首先任命,再由選民投票決定最終留任與否。之所以有這樣的轉變是由于人們相信,法官應當對選民負有更多的民主責任,同時民選法官也會更認同自己與民眾的聯系。日本的“最高法院人民審查制”與上述“混合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在其任命后第一次舉行眾議院議員大選時,交付國民審查,自此經過10年之后的第一次舉行眾議院議員大選時再次交付審查,此后亦同。(日本憲法第79條)而世紀之交的日本司法改革,又進一步強化了國民對地方法官候選人提名的知情權和咨詢權。
(二)民眾對法官工作評價的參與
如果說選舉法官是民眾對法官的起點控制的話,那么
對法官任職工作的評價就成了民眾的過程控制。美國的阿拉斯加州、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州、新墨西哥州、田納西州和猶他州,均設立了獨立的法官評價委員會,該委員會聽取包括陪審員、訴訟當事人、證人、法院工作人員、社會機構、政府官員等一切可能接近法官工作的民眾的意見,對法官的秉性、處理案件的效率、庭審的時間等等作出評價,(但不涉及法官的判決和意識形態)并將這些信息通過各種方式向公眾公開。
(三)民眾對法院審判的參與
社會民眾并非僅僅作為法院的旁觀者而存在的,那些被深深卷入訟爭的當事人以及以訴訟為業的律師群體才是對司法正當性最為關切的人民群眾。如果說民主意味著任何人或組織都不能自我僭取無限的權力的話,那么在訴訟中限制法官的審判權就成了司法民主的重要目標。在這一思路的指引下,訴訟中的當事人享有各種訴訟權利,以達到制約法官審判權的目的。在新型當事人主義(以選擇自由和個體滿足為基本價值尺度)的框架內‘,當事人的“程序主體地位”得到了最大范圍的尊重和維護,它意味著在訴訟過程中是當事人的訴訟行為,而不是法官的職權行為推動著訴訟實質意義上的進行。因此,盡管最后作出判決的是法官,當事者卻被視為形成判決的主體,即法官只能在當事人事實主張和權利主張的約束下作出判決。作為一種需要專門知識和使命感的自由職業,律師群體的根本價值在于為公眾服務的精神。律師在訴訟中一方面通過論證當事人主張的合法性以影響法官的判斷,另一方面通過法定方式否定法官某種裁判的不合法性。因此,律師的職業與其說是為了當事人的利益,不如說是為了對抗司法機關的不當行為。法律的歷史早已表明,沒有職業律師階層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和司法民主。
四、結語
民主是醫治正當性危機的良藥。人民之所以遵守法律,并不是因為他們害怕強力,而是因為法律是他們平等參與和創制出來的,他們之所以接受法院的裁決,是因為他們相信他們服從法律就是在服從自己。在這一意義上,一個缺乏民主、頻頻背離民意的司法注定不可能長久地被民眾所尊重。正是在司法正當性的視野里,司法民主化才有了遠遠超出司法職業化的重大意義。我們相信,通過大眾司法的創造性轉化,一種與司法職業化相融的人民司法制度將有助于實現法官盡責和人民承認,并最終成為中國司法正當性重建的可能前景。
[責任編輯:敖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