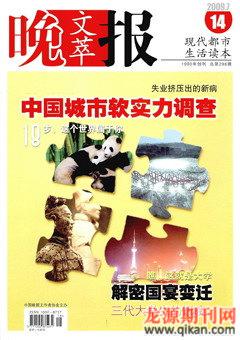中國城市軟實力調查
黃 琳
城市是不是一個好東西——這個西方爭論多年的話題,在中國急劇的城市發展和擴張中,也開始為人們所關注。
城里的人們,開始體驗“城市病”:交通擁堵、資源緊張、環境惡化、貧富落差,還有人情淡薄和無根的漂泊感;而城外的人們,還在紛紛涌入。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稱,2008年末全國農民工總量超過了2.2億,也就是說,大約六分之一的中國人口往返于城鄉之間,試圖跨越城鄉差距的鴻溝。他們在城市邊緣試探,希望能盡快融入其中但卻不得要領。
一座城市,在摩天大樓、開發區、高速公路之外,怎樣能從人心之中凝聚更多發展的動力?一座城市的管理者,怎樣能讓想進城的人多一份親切感、歸屬感,怎樣能讓城里的人多一份自豪感、忠誠度?
1990年,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這個新鮮概念的時候,是在國家層面展開觀察——與經濟、軍事等硬力量相比,軟實力更多的是一種精神性力量,包含一國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的國際影響力與感召力。
將“軟實力”這個度量衡從國家層面延伸至城市,其價值和意義更加切實可感。復旦大學國際公共關系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為城市管理者提供了一幅新的發展圖景。與追求GDP的硬實力不同,城市軟實力是建立在城市文化、城市環境、人口素質、社會和諧度等非物質要素之上的,它涵蓋了一個城市的文化感召力、環境舒適度、政府公信力、社會凝聚力、居民創造力等。
這些指標看起來很“軟”——不像GDP那樣量化標準清晰,主觀感受有時也融入其中,甚至還有歷史積累與現實問題的混雜交錯;但在和諧社會與科學發展的大目標下,它們卻構成了一座城市永葆魅力、生生不息的“硬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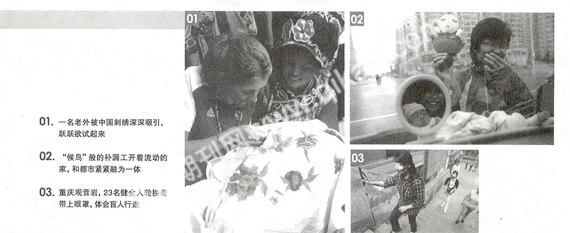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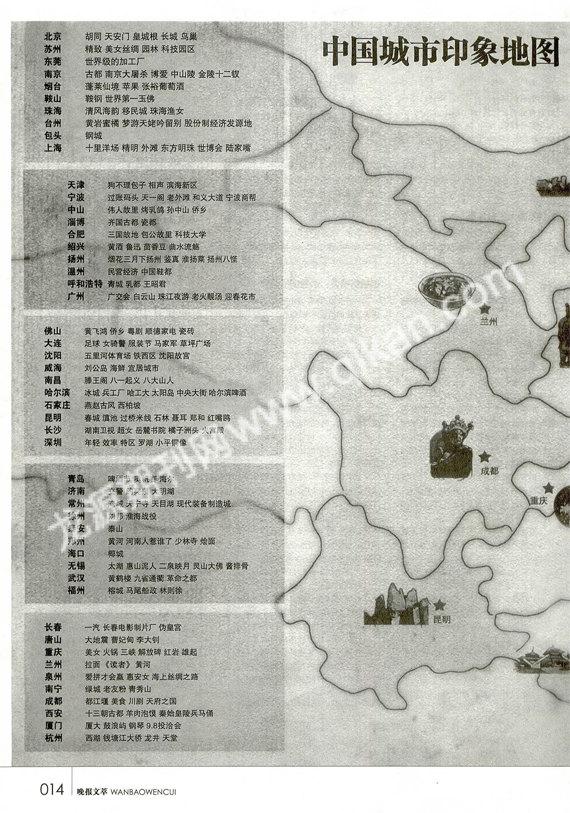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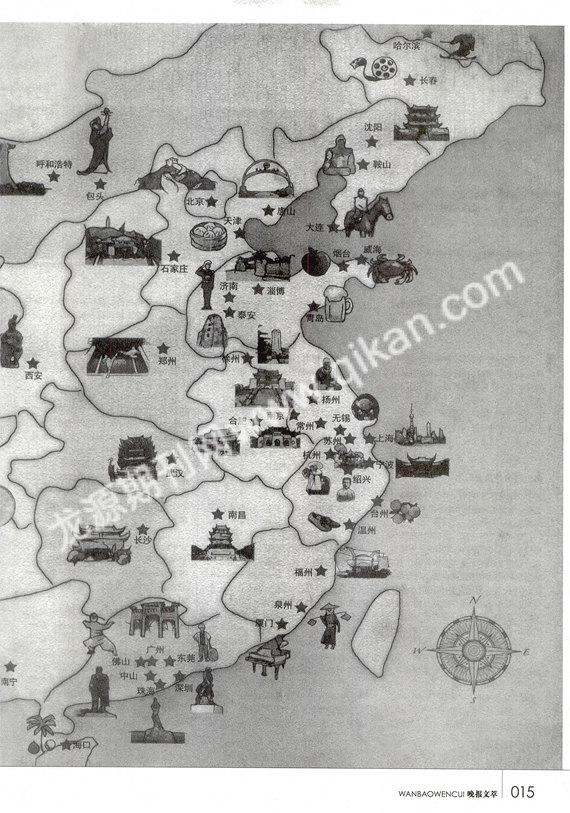
簡而言之,軟實力,是外界對于—座城市的直覺反應,是市民對這座城市的認同與忠誠,更標志著城市決策者的智慧與情懷。
城市軟實力:五大關鍵詞
“現在的問題是,沒有幾個城市能夠清晰地知道自己城市真正的資源是什么”
關于城市或地域的話題,總有層出不窮的新鮮,也總有不知疲倦的爭論。
最新的一個例子是,在網上流傳的一幅“河南人心中的中國地圖”上,中國被分成了兩部分——河南與河南之外。河南那片寫著:俺家;其他地方則是:傷害我們的人。雖是調侃,但歧視和反歧視顯而易見。
對于城市管理者而言,如何改變外部對于城市的負面影響,保持并塑造城市魅力,確是一個難題。復旦大學國際公共關系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教授說:“一個城市如何被看待,本質上就是城市軟實力問題。”在他領銜的中國城市軟實力指標體系研究中,“城市形象”被賦予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形象傳播力形象是個易碎品
同樣在網絡上流傳的一份中國城市班級名單里,“太原”被描述為一名普通學生,特點是:“勤勞樸實的勞動人民的孩子,家底不好,學習有時顯得有些急于求成。家里開了很多煤廠導致皮膚不好。最近開始注重保養和調整學習方法。”
但歷史上代表山西形象的,首推“晉商”。2004年春節,央視播出了八集紀錄片《晉商》,詳細介紹了明清時代稱雄中國商界膳年的晉商的興衰成敗。當時有評論說,這是山西改革開放以來,在全國做得最成功的一次宣傳,重新塑造了全國人民對山西的看法。
遺憾的是,近幾年,負面事件紛至。黑磚窯事件之后,在山西的“新陽泉論壇”上,有網友悲呼:“山西從黑窯和苦工那里賺了錢,但失去了什么?要多少錢、幾代人,才能挽回山西形象?”
“形象是個易碎品。”孟建說。
形象,也就是民間常說的“口碑”,其維護并非易事,尤其在如今傳播渠道無所不在的情況下,更是“壞事傳千里”。有研究表明,當某種形象被損害,要想恢復,至少要花費6倍的精力。
事實上,城市形象在中國還在發掘期。“只有差異化,才能讓每個城市找到自己的定位,才能真正成為‘這一個。”在孟建看來,同質化是目前城市形象“行而不遠”的根源。
根據他的研究,城市形象在中國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僅僅是城市營銷的概念,當時由一些廣告策劃人提出,但很快就遭遇麻煩——一些城市急于把城市資源變現,往往過度開發,有時還造成文物部門與旅游部門的沖突,前者要保護,后者要開發。
第二階段就是目前被熟知的“城市形象”,也叫“城市戰略”,較多關注城市發展的軟實力。
在中國城市軟實力調查的指標體系里,關于城市形象,除了媒體的負面報道曝光數、城市的口碑外,還有城市對外宣傳的力度。
孟建解釋說,很多城市對外宣傳力度不足,其背后真正的問題是思維方式的誤區:城市的領導者很多時候并未認識到,做什么永遠比怎么做更重要。城市形象傳播是一個具有規律的藝術,“真正的形象存在于人們心中,并不是做幾個廣告、搞幾個活動就能深入人心的。”
—方面是傳播不夠,另一方面則是宣傳過偏或者夸大其詞。某些城市的形象宣傳就是一個“旅游廣告”,而更多的城市則是無限夸大現有資源。比如,有幾個湖,就自稱“水城”;綠化還過得去,就說成“最佳宜居城市”。“夸大宣傳,最終只會損害城市的軟實力。”孟建說。
文化號召力:提供什么樣的內容
關于城市的各種評價中,“沒文化”最具殺傷力。
新華網城市論壇上,近日關于杭州和南京又開始新一輪爭論。一名南京網友發出英雄帖,選吟詠南京和杭州的唐詩PK,誰的數量多誰勝。該網友率先拋出韋莊的《臺城》: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
很快,杭州網友接招,稱“白居易一個人就行了”,緊接著貼了“錢塘湖春行”等好幾首白居易描寫杭州的詩。不過,孟建卻說,他很怕城市文化這樣的提法。文化似乎成了一個筐,什么都往里面裝。
在城市軟實力指標體系中,專門提出了“文化號召力”。“一個城市是否有文化,有一些硬指標衡量。”他介紹說,文化企事業有多少,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多少,以及文化生活是否豐富、文化是否有特色等,都是城市軟實力中有關文化的“硬件”。
美國康涅狄格州立大學校長杰克·米勒關于“美國最有文化城市”的研究,也更多地體現在一些硬性數據的分析上,比如互聯網的使用率、圖書館的利用率、圖書報紙的發行率等等。
而目前國內一些城市對于文化的理解過于狹隘,急功近利,“把文化當做傀儡。”一位城市規劃研究者表示,比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就是用文化畫個圈去招商引資。至于文化如何成為主角,如何發掘一個城市的文化潛力和底蘊,—直沒有解決。
這位專家還對眼下很多城市大搞活動和各種節日頗有微詞。“只要有特產,就有相關的節日,有名人就有名人文化節,沒有的,搶也要搶一個來。”
孟建認為,節日在城市文化中只是較小的組成部分,更應該讓市民感受到隨處可見的文化氣息。
比如,建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除了圖書館、社會
活動中心等基礎設施建設外,關鍵還在于“城市提供什么樣的文化”。
“但現在的問題是,沒有幾個城市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的資源是什么。”孟建說。
政府執政力:向下看
城市軟實力評估體系里,政府執政力是重要部分。基本的數據資料審核包括:本科以上學歷的公務員比例,以及上一年度城市里副處級以上官員違規比例等。
“官場風氣直接關系到城市的影響力。”孟建說。
兩年前,一篇關于阜陽的“政治生態災難”報道說:從上世紀90年代末原市長肖作新夫婦腐敗案起,到兩任市委書記王懷忠、王昭耀先后倒臺……一系列腐敗案,給阜陽的軟實力造成巨大傷害。
前阜陽市委書記胡連松在任時曾對媒體說,他剛到阜陽工作參加省里組織的招商活動時,每提到阜陽市,出席活動的客商們都說知道“那地方”,“語氣當中充滿著嘲諷意味。”
甚至一些外出務工的阜陽人,一度不愿明示自己的家鄉;某些當地企業,在做廣告時也不說是阜陽的,擔心產品銷售受到影響……
孟建說,在軟實力評估體系里,政府的管理、服務,都是政府執政力的考察因素。
他表示,作為城市的管理者,假如眼睛向下,多和市民交流溝通,在管理城市上就會少走彎路,增強執政力。在一些決策出臺之前咨詢市民意見,或許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破壞城市形象的“非議”之舉。
近日陜西風縣‘人造星星”引發的紛擾,就是一例。鳳縣在打造旅游品牌過程中,建了“綠色生態長廊”,仿造的徽式民居,綠樹青竹,被網民稱為“山寨版江南”;還搞了“人造星星和月亮”,巨資建造了噴射高度達186米的噴泉,在嘉陵江上筑壩蓄水形成30萬平方米的景觀水面,打造中國西部山區的“威尼斯”……
短短兩年內投資6.5億元,實施了5大景區、5大公園等幾十個大型景觀項目,當地人對此似乎并不認可,一些市民對媒體表示,風縣文化積淀濃厚,鳳縣民歌、民間故事數量占到全寶雞市的45%。“建人工月亮不如挖掘本地民歌。”
區域影響力:誰是區域的唯一
“在那山的那邊山的那邊有一群重慶人。他們活潑又聰明,他們調皮又靈敏。……他們齊心合力開動腦筋斗敗了成都人。他們唱歌跳舞快樂多歡欣。”
這個改寫了《藍精靈》歌詞的視頻,近來出現在一些城市論壇上,作者不用說,是重慶人。成渝之間的民間口水戰,不時風生水起。
不僅成渝,濟南和青島,大連和沈陽,廈門和福州,南京和蘇州,石家莊和保定,廣州和深圳……地方或者全國性的論壇上,網民們常常唇槍舌劍,力推自己的城市才是區域“老大”。
怎樣評判一個城市的區域影響力?孟建認為,幾個指標可以測評,如經省部級以上審批的國際活動數——反映全球化程度和國際知名度;地級以上代表團到訪的次數—一反映該城市在國內的政治地位;世界500強企業分支機構數一體現城市經濟影響力;城市居民認同度。
“城市間市民的口水紛爭可以視為主體意識的覺醒,也是城市軟實力進入公眾議程的體現,這是其進步的一面。”但是,對這樣的爭執,孟建并不贊同,“這對城市決策者并沒有太大的積極意義。”
他認為,對于城市決策者來說,至少應該理性地、客觀地思考兩個問題:我在這個區域中的比較優勢是什么?我如何與其他城市一起建構區域影響力?
城市凝聚力:主體的認同和接受
與其他指標相比,城市凝聚力是一個相對更主觀的指標。
孟建認為,一個城市是否有足夠高的接納程度,是否存在排外和歧視,是反映城市凝聚力的重要指標。“在人口流動越來越快的當代中國,城市包容度越來越重要。”
近年來有關調查表明,在中國的主要城市里,本地人對外地人的包容程度不如表面所見那么高,城市之間包容性表現得分差異也較大。尤其在教育和就業方面,很多城市對外地人的平等容納能力較低。
城市的歸屬感同樣是城市凝聚力的重要衡量因素。—方面它表現為城市是否能滿足居民衣食住行、醫療就業及教育的需求;另—方面,還在于這個城市能否讓其居民真正感到平等。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青年學者陸銘兩年前造訪巴黎拉雪茲公墓時,發現偉人巴爾扎克和肖邦的墓地非常普通,巴爾扎克窄窄的墓地除了有個頭像以外,沒有任何特別,肖邦的墓地狹小而局促。“在這個墓區里,偉人和平民躺在—起。”
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目標,而這種目標能在多大程度被人們所認同和踐行,反映著該城市的凝聚力。一個致力于做國際大都市的城市,和一個強調人居環境的小城市,盡管目標不同,但接受程度有可能是類似的。
孟建認為,這體現為市民價值觀的一致性,“對于共同目標和共同規則的認同和遵守,是城市凝聚力得以實現的核心條件。”在評價城市凝聚力方面,孟建提出了兩個硬指標,兩個軟指標。硬指標包括城市外來人口與戶籍人口比例、外省市派駐機構數;而軟指標則是城市歸屬感和包容性。
“城市的凝聚力應該是由各個方面來評價的——不光是政府機構,還有民間的各個群體。”孟建總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