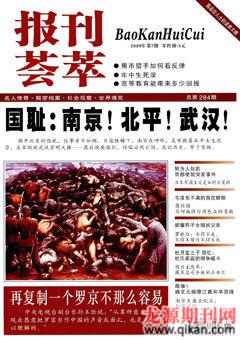“文革”中的知青典型怎么了?
劉小萌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場(chǎng)又一場(chǎng)政治運(yùn)動(dòng)紛至沓來(lái),席卷城鄉(xiāng)。許多知識(shí)青年,首先是那些典型人物,曾自覺(jué)或不自覺(jué)地投身其間。“文革”后期崛起的“頭上長(zhǎng)角,身上長(zhǎng)刺”的“反潮流”典型,更是深深卷入到政治斗爭(zhēng)的漩渦中。“文革”結(jié)束以后,如何對(duì)待這些知青典型,成為人們關(guān)注的一個(gè)問(wèn)題。
“反潮流”典型的下場(chǎng)
在眾多知青典型中,有極少數(shù)人如張鐵生、朱克家輩是經(jīng)“四人幫”親自選拔而一躍成為政壇新星的。“文革”結(jié)束后,他們被定性為“幫派體系骨干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而分別受到法律懲處。
“白卷英雄”張鐵生是最先受到點(diǎn)名批判的知青典型之一。1976年11月18日,《山西日?qǐng)?bào)》發(fā)表《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的文章,揭露張鐵生于當(dāng)年2月在山西省煽動(dòng)“層層揪”所謂“黨內(nèi)走資派”的言行,拉開了揭批的序幕。11月30日《人民日?qǐng)?bào)》又刊載《一個(gè)反革命的政治騙局——“四人幫”炮制(答卷>作者這個(gè)假典型的調(diào)查》。調(diào)查揭露了“四人幫”制造這個(gè)“反潮流典型”的經(jīng)過(guò)及用心。此后,各地報(bào)刊紛紛撰文批判這一事件對(duì)教育工作和對(duì)青少年思想造成的危害。
但張鐵生的主要問(wèn)題還在于他與“四人幫”的政治關(guān)系上。1977年9月中共中央37號(hào)文件將王、張、江、姚專案組編輯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tuán)罪證(材料之三)》下發(fā)全國(guó)。其中公布有“新生反革命分子張鐵生的材料”,包括“白卷”影印件,中共遼寧省委關(guān)于張鐵生的審查情況報(bào)告。報(bào)告稱:審查證明,張鐵生是“四人幫”及其在遼寧的死黨和親信毛遠(yuǎn)新等人一手炮制的假典型,真右派,是“四人幫”篡黨奪權(quán)的一個(gè)反革命打手。報(b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