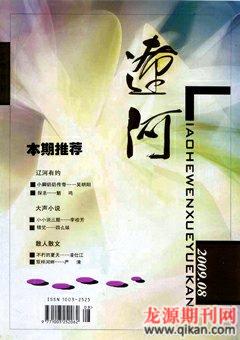雙梓河畔
嚴(yán) 清
一條清幽的小河從漁村流過(guò),綿延八十余里匯入嘉陵江。解放前叫梓江河,如今叫雙梓河,得名于由此分流的梓綿河與梓鹽河。雙梓河在漁村拐了一個(gè)長(zhǎng)長(zhǎng)的彎,把漁村正好圍了一個(gè)半圓,由此形成了一個(gè)很大的河灣,叫做魚家灣。
——引子
(一)血灘
雙梓河河谷狹窄、灘險(xiǎn)礁多,因而并不適合航運(yùn)。它算不上長(zhǎng)江這棵大樹的枝丫,充其量只是一節(jié)須根罷了。省區(qū)地圖上根本找不到它,只在縣志的地圖上可以看到那自東北而西南的一條孱弱的綠線。河流是孕育人類文明的搖籃,然而雙梓河的貢獻(xiàn)可沒(méi)那么大。就連一個(gè)成規(guī)模的小鎮(zhèn)她也沒(méi)能孕育出來(lái)。八十里的雙梓河上沒(méi)有航道、沒(méi)有碼頭,偶爾能見幾條采砂船漂在河面上,柴油機(jī)的轟鳴聲攪渾一碧清水。又或者,一葉扁舟滿載了剛收割的農(nóng)作物駛向彼岸。沿河有幾間水磨作坊,淙淙的流水傳承著古老的生產(chǎn)方式。
雙梓河進(jìn)入富驛鎮(zhèn)境內(nèi)的狹長(zhǎng)一段地域叫血灘。蓋因谷深灘斜,謂之“斜灘”,“血灘”疑為其訛音。總之,都已無(wú)跡可考。血灘一帶多巖石,當(dāng)?shù)厝朔Q之為“硝地”。谷物、玉米都無(wú)所收成。人們反倒樂(lè)意種上豆類等經(jīng)濟(jì)作物。農(nóng)歷十月,遠(yuǎn)遠(yuǎn)望去金黃色的黃豆莢子漫山遍野,那一抹金黃被雙梓河一分為二。收獲的季節(jié)是村民最喜悅的時(shí)光,家家戶戶把成熟的豆子連根拔起,然后捆成一扎一扎倒掛在樹枝上,等水分都干透了再用糧蓋(一種用于脫粒的農(nóng)具)把豆莢打下來(lái)。再用風(fēng)車除去豆殼,一粒粒豆子就分離了出來(lái)。
(二)魚家灣
血灘很少有濃密蔥郁的喬木。凡是綠樹成蔭的地方多半是院落了。南方的院落較之北方顯得十分稀疏、雜亂。北方地平,村落相對(duì)集中且容量極大。南方因?yàn)槎酁榍鹆甑貛?受地勢(shì)影響,村落顯得散亂。在南方,村下面還有更小的地域單位,叫“灣”。“灣”其實(shí)只是一個(gè)個(gè)有河流經(jīng)過(guò)或者連條小溪也沒(méi)有的小山坳,一般根據(jù)姓氏來(lái)命名,比方說(shuō),如果一個(gè)山坳里姓楊的人居多就叫楊家灣,姓李的多就叫李家灣。當(dāng)然也有例外,不過(guò)這種例外很少。往往是幾個(gè)灣連在一起組成村民小組,再由若干村民小組組成村。灣,在南方農(nóng)民眼里是一個(gè)極有分量的稱謂。因?yàn)樗侨藗兩a(chǎn)生活的大本營(yíng)、根據(jù)地。它是人們的精神家園和依托,灣的內(nèi)部有強(qiáng)烈的族群認(rèn)同感和凝聚力。灣與灣之間往往會(huì)因?yàn)槟撤N利益沖突而抵觸,甚至是大打出手,也會(huì)因?yàn)楣餐拿\(yùn)和遭遇而緊密地團(tuán)結(jié)起來(lái)。總之,灣是聯(lián)系人與人之間的紐帶,人們對(duì)灣的認(rèn)同要比村強(qiáng)烈得多。
魚家灣就躺在血灘北側(cè)。魚家灣的住戶不多,留守戶更少,差不多十室九空。他們像千千萬(wàn)萬(wàn)中國(guó)農(nóng)民一樣,放棄了祖祖輩輩耕耘的熱土,背上了沉重或空乏的行囊到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圓夢(mèng)去了。灣口有間棚屋在風(fēng)中搖搖欲墜,青瓦上的苔蘚泛著綠光。竹篾編夾的墻體上糊的泥巴已經(jīng)剝落了好些。明亮的陽(yáng)光透過(guò)那些縫隙射到屋里去,根根光柱更加襯托出棚屋的陰暗。
(三)百年棚屋
這里是魚家灣,這棚屋的主人當(dāng)然也姓魚。傳說(shuō)棚屋的第一代主人魚老太爺,是個(gè)比大地主窮,比富農(nóng)富的半拉子地主。后來(lái)被劃到地主一類,家業(yè)地產(chǎn)全被沒(méi)收,留給他的就是這間原本是他家長(zhǎng)工住的棚屋。魚老太爺在這間他輝煌時(shí)從不曾來(lái)過(guò)的棚屋里度過(guò)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時(shí)光。他沒(méi)有抱怨、沒(méi)有憎恨,他的死是那么的安詳。這個(gè)魚老太爺就是我外祖母的父親,也就是我母親的外祖父。棚屋留給了他的兒子、孫子。
關(guān)于棚屋的這些事是十五年前我隨母親、舅舅一干人去給傳說(shuō)中的魚老太爺燒紙祭墳時(shí)舅舅告訴我的。那時(shí)的我,稚嫩得不知道什么叫人生的無(wú)常與命運(yùn)的叵測(cè),糊涂得為了一塊糖就可以出賣朋友和兄弟。我和大哥坐在汽車后排爭(zhēng)搶著長(zhǎng)輩們給的糖果。汽車在機(jī)耕道上顛簸,不知道搖了多久、顛了多久。只聽到舅舅拉手剎的“咯咯”聲響過(guò),感覺(jué)就該到了。天有些冷,但有一股子新鮮勁兒,也覺(jué)得不怎么冷了。 母親暈車,下車時(shí)她扶住車門俯下身去嘔得厲害。
魚老太爺家的墳地在雞公嶺,去雞公嶺的路上我見到那間棚屋,門楣上的楹聯(lián)字跡已很模糊,依稀可以辨出是“人勤春早”四個(gè)字。門框上的春聯(lián)早被頑皮的孩子撕去了半截,左邊只剩下“天增歲月”,右邊剩下“春滿乾”。門板上的門神我說(shuō)是尉遲公和二郎神,大哥卻說(shuō)是二郎神和托塔天王李靖。銹跡斑斑的大鐵鎖掛在門扣上。屋檐下有一條深深淺淺的溝,事實(shí)勝于雄辯地證明了水滴石穿的古訓(xùn)。
(四)雞公嶺
棚屋上了鎖,棚屋的第三代主人——我母親的表哥,我的表舅,大概趕集置辦年貨去了。我的兩個(gè)小表弟呢?是和鄰家的小孩一起放牛去了,還是被大人們帶出去了呢?沒(méi)有見到親人,母親和舅舅都有些失望,最后決定直接去祭墳。香、燭、紙、炮都挺沉的,舅舅額頭上滲出了一層油油的汗。繞過(guò)一個(gè)彎,爬上一個(gè)坡就到了雞公嶺。
陰陽(yáng)先生(道士)說(shuō)雞公嶺是一塊好地,它管著血灘的風(fēng)水,決定著血灘的人脈。有一年鎮(zhèn)上決定修公路要穿過(guò)雞公嶺,工程隊(duì)都在這里駐下了,血灘的村民硬是扛了鋤頭、釘耙把他們給趕走了。所以雞公嶺就漸漸成了墓地。越來(lái)越多的死者葬在這里。甚至一些老而未死的人都請(qǐng)了陰陽(yáng)先生來(lái)這里把風(fēng)水看準(zhǔn)了,好讓自己死后有塊如意的葬身之地。魚老太爺?shù)膲灦训美细?燒紙時(shí)母親對(duì)舅舅說(shuō):“地主死了都是要挨斗的,當(dāng)年外公這墳可不準(zhǔn)壘這么大。后來(lái)魚家的后人每年都在墳上培上新土,這墳才變這么大的。”母親叫我和大哥,還有幾個(gè)表弟表妹們排成一排跪在魚老太爺墳前磕頭。一下、兩下、三下,那時(shí)的我們,還不知道磕頭的莊重。
紙燭的煙熏味在空氣中彌漫,鞭炮的噼啪聲撕開晌午的寧?kù)o,幾縷炊煙從農(nóng)舍里竄出來(lái)?yè)u曳著動(dòng)人的舞姿。
(五)表舅和表舅媽
所有的祭祀活動(dòng)都結(jié)束的時(shí)候,一個(gè)飽經(jīng)滄桑的中年漢子背了個(gè)背篼朝這邊走來(lái),臉上洋溢著南方農(nóng)民特有的質(zhì)樸的笑。他的身后有兩個(gè)孩子,看樣子要比我小。母親說(shuō)那就是我表舅,棚屋的第三代主人。兩個(gè)孩子是表弟,大的叫認(rèn)元,小的叫陶二。農(nóng)家孩子的名字來(lái)得自然,沒(méi)有詩(shī)情畫意,也無(wú)需引經(jīng)據(jù)典。大人們免不了一番寒暄,孩子們就少了許多禮節(jié)。幾家的小孩在墳前的菜地里打鬧了起來(lái)。在那“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的喜慶日子里,我認(rèn)識(shí)了我的兩個(gè)小表弟——棚屋的第四代主人。或者,他們未來(lái)不再屬于棚屋——如果命運(yùn)眷顧他們的話。
記憶最深刻的事情是,那一天沒(méi)在表舅家吃飯。表舅開了鎖,母親和舅舅一前一后跟著表舅進(jìn)了屋。大哥和表弟表妹們還在屋外打鬧。我站在門檻上,一只手拉著門扣,這樣就只開了半扇門。屋內(nèi)的陳設(shè)極其簡(jiǎn)單,一張跛了腿的桌子擺在屋角,旁邊有兩條凳子。桌上放著一只掉了漆的熱水瓶,桌子右手邊有一道門,門那邊就是廚房。沒(méi)有看到表舅媽。后來(lái)聽說(shuō)那天她知道家里來(lái)了客人就跑到隔房嫂子家去了。至今都不大明白表舅媽要躲什么。表舅叫兩個(gè)表弟去找他們的媽媽,然后一邊挽留母親和舅舅。舅舅放下一大堆糖果、營(yíng)養(yǎng)品,還有一包給兩個(gè)表弟的舊衣服就辭了表舅上車了。“真餓啊,怎么沒(méi)有飯吃呢?”我在車上問(wèn)。
(六)兩個(gè)表弟
白云蒼狗,時(shí)光如流,一晃十五年過(guò)去了。十五年在歷史長(zhǎng)河中不過(guò)就是一粒浮塵。十五年在人間,卻不知演繹了多少悲歡離合、花開花謝。我憨厚的倆表弟喲,也該長(zhǎng)大成人了吧?
去年暑假回家,父親的店里來(lái)了個(gè)小伙子。第一眼就覺(jué)得有些眼熟,好像在哪見過(guò),可一時(shí)又想不起來(lái)。母親告訴我那就是血灘的二表弟陶二。陶二沖我傻笑,那笑臉,好像我的表舅。母親說(shuō)陶二在店里做事很踏實(shí)很勤懇。閑暇時(shí)我也帶著表弟去娛樂(lè)城看電影、到蓮花湖看湖光山色。表弟告訴我這些年里發(fā)生了許多事。先是他兄弟倆雙雙輟學(xué),父親在工地上打雜摔傷了腿,母親在鄉(xiāng)里靠看水碗、端花盆、驅(qū)神鬼(都是川北農(nóng)村的迷信活動(dòng))掙點(diǎn)小錢撐持家用。后來(lái)大哥認(rèn)元和同村人外出務(wù)工打傷了人被收監(jiān),等等。
(七)尾聲
今春我又和母親一行人去血灘燒紙祭祖。大氣候還是那個(gè)樣子,不同的是機(jī)耕道寬了些、平坦了些,每個(gè)被轎車甩在后面的院落里都多了一兩棟小洋樓。又到了棚屋面前,西墻的一角已經(jīng)坍塌了,門上的鎖已銹成一團(tuán)爛鐵。門檻也已經(jīng)腐朽,靠近門框的地方還生了一叢黑色的菌。也許是腳步聲太響,驚起一只沉睡在屋檐下的野雞。野雞飛走,拉下一泡屎,差點(diǎn)灑在我身上。
雙梓河在鮮見的冬日暖陽(yáng)下泛著粼粼的波光。那些整日待在鋼筋、混凝土森林中的白領(lǐng)、藍(lán)領(lǐng)們租了小皮艇在河中不緊不慢地行進(jìn),目的是貪婪地呼吸這里氧氣富足的清新空氣。
滄海桑田,人事已非。千年流淌的雙梓河喲,蕩滌著多少人的夢(mè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