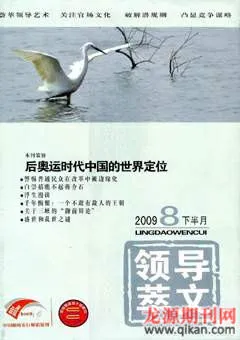和平發展
代曉靈
在當今這個“多點崛起”的時代里,世界為何偏偏對中國焦慮?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中國的行為邏輯、政治和文明主張沒有系統的、全面的、令人信服的展示和表達”,“從根本上說是缺乏一種向世界說話的戰略”,而2008年的奧運會適時地給了我們一個解答的機會:伴隨著孔子的三千門徒手持竹簡齊誦《論語》名句,舞蹈演員以身體為筆墨書寫出一幅別具匠心的“和”字,這所要表達的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的思維。
北京奧運會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綿延五千年的輝煌文明史,其中的一個“和”字也展現了縱橫五千年的和諧觀,而中國當前的崛起會否對世界和平的建構造成威脅,秉承“不為帝王唱贊歌,只為蒼生說人話”的態度,歷史視角或許能給我們提供最好的證明。
和平,作為歷史的傳統
迥異于西方思維“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克勞塞維茨)、“為了勝利不顧一切政治后果”(麥克阿瑟),中國自先秦時代以來傳承著“非戰”、“慎戰”、“禮戰”的和平思想,“和為貴”、“兼愛”、“非攻”等論述不勝枚舉。奧運會上“用世界語言講述中國文明”即是這些理念的展示。當然,中國歷史上也不乏戰爭,但這些戰爭實屬“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后的無奈之舉。無論是周圍少數民族的入侵還是中原王朝的征戰,即便是在全盛的漢唐時期,在平定叛亂之后,也會采取和親、冊封、互市等方式博恩廣施,和平相處。西方一位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曾經指出:“中國人自身文明知識體系里并不包括侵略性的使命,他們總是歡迎其他民族成為他的文明世界的一員。”在1648年西方維斯特伐利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建構之前,中國已將以中原王朝為中心、和合思想為基礎的東亞朝貢體系維持了兩千年的時間,“并在哲學、文化、藝術、社會管理技巧、技術發明、政治權力、農業生產率、工業發明和生活水平方面高于世界先進水平”,實現了“中原王朝治下的和平”。正如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所說的那樣:“在中國的全盛時期,中國在全球沒有可以與之相匹敵的國家,沒有其他大國能夠向中國的帝國地位挑戰,甚至如果中國想進一步擴張的話,也不會有任何其他大國能夠抵擋中國的擴張,但中國還是比較有限地使用其武力。”作為朝貢體系的主導者,中國無意于干涉藩屬國的內政,卻在經濟上給予多倍于朝貢的回饋。體現中國傳統和諧世界觀最典型的范例就是鄭和下西洋,盡管遠涉重洋歷經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沒有掠奪和戰爭,它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和平之旅”,與隨后歐洲殖民者遍及全球的殖民戰爭、鴉片貿易、占領侵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到了近代,中國則成為了東西方強國在全球爭奪利益的犧牲品和祭奠品。鴉片戰爭前后的百年間,盡管被迫開放門戶、備受強國欺凌,但從洋務運動到五四運動,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首次喚醒中華民族之國民意識的同時,宣揚的絕非是嫉惡如仇的憤懣,而是學而致之的反思,這難道不是一個開放民族應有的“和合”秉性嗎?1949年新中國成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對外關系的基本國策,這難道不是和合文化在社會主義新時期的延續和重構?也許有人會質疑,20世紀冷戰間的那幾場熱戰偏偏都與中國掛上鉤,但究其根源,我們會發現他人眼中的“暴力手段和行為”實質上是兩極爭霸格局下的迫不得已或身不由己,中國豈是“沽名”的“霸王”,冷戰時的中國同東歐或西歐國家一樣,只是美蘇在全球博弈的一片棋陣。對于諸如朝鮮戰爭、中印邊界沖突、珍寶島戰役、中越邊界沖突等等,都是在祖國的領土主權和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后的自衛之舉,甚至前幾年發生的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中美撞機事件乃至去年國內的拉薩打砸搶燒事件等,中國的態度都是克制、冷靜地處之。這正如費正清所言:“中國的擴張主義是反擊性的,不是主動的、天生的。”
同樣是基于我們民族傳統的和平主義思想,才使得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維持了穩定發展的國際國內環境,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作為聯合國的合法成員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特殊地位和特殊影響力”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發揮世界大國的作用;順利收回香港、澳門,“一國兩制”新型模式初顯成效;經濟連續多年持續高速增長;2001年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已經成為“亞洲乃至全球的經濟發動機”;甚至在最敏感的臺灣問題上,都可以“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
和諧,未來的發展之路
和平復興是北京奧運會傳達給世界的一種信號:中國力量可以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中國力量可以改變世界,而這種吸引和改變,并不是西方想象中的“戰略敵手”、“新挑戰者”,而是基于和合文化傳統上構建“和諧世界”的大國理念和風范。在2005年第60屆聯合國首腦峰會上,胡錦濤主席就提出了“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倡議:要堅持多邊主義,實現共同安全;要堅持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繁榮;要堅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諧世界。之后,和諧世界的思想在各種內政和外交場合得以向世界各國廣為宣傳,成為“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世界觀的最新表述”,這也標志著中國進入了一個更加開放、透明和包容的新時代。
雖然西方媒體仍是全球輿論的主導者,但在全球化的推動下,和合傳統理念與和諧世界思想也已開始漸漸為人所接納,在西方媒介中也已不乏對其客觀深入的評論。戴維?布魯克斯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和諧與中國夢》中指出:“世界的劃分方式有很多種,貧窮的或富裕的,集權的或民主的,個人主義社會往往注重個人的重要性,集體主義社會則看重和諧和責任。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整齊劃一的表演即是中國奇跡般崛起背景下東方集體主義路線展示的和諧社會的景象。” 對此,和平主義的歷史傳統也許從某種程度上能證明我們的“清白”,但我們寧愿用自己的話來詮釋:“要體現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構建和諧世界的過程里面有我們的參與和推動,但我們不是領導,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是“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真正的成功需要全人類的共同努力。
奧運雖已遠去,但中國仍在崛起。面對一個已經逐漸強大起來的中國,“如果能夠正確對待的話,世界沒有理由懼怕”,因為和合文化伴隨著中國的興盛,同時也是世界的繁榮,它必能閃耀其人文價值,這既是歷史知性的回歸,也是和諧的中國社會與和平的世界家園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