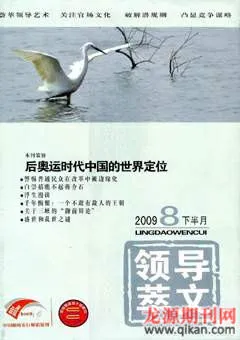中國崛起必需遠洋海軍
鐘 化
擁有真正意義上遠洋海軍
單從技術能力的角度上來說,能夠建造真正意義上的遠洋海軍的國家很多。可是,當今世界上,擁有真正意義上遠洋海軍的國家只有一個,當然就是美國。
海洋作為當今世界上最為廉價的物流載體的權力變遷,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實力政治版圖的變遷。自大發現時代之后,幾乎每一個海洋勢力的崛起都伴隨著一個大國的崛起。
真正意義上的遠洋海軍,是以遠洋攻防為直接目標的海軍,是能夠與任何海洋強國在大洋深處爭奪制海權的海軍,是能夠獨立擔負并完成戰役和戰略目標的海軍。在美國海軍獨步天下的今天,無論是俄羅斯還是英國、法國的海軍,都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遠洋海軍,充其量不過是遠洋部署型海軍。他們的海洋力量,能夠在遠洋對美國海軍形成一定的威脅,但說到爭奪制海權,那就是白日做夢了。
正如世人所看到的一樣,世界歷史上,諸多具備足夠的技術和經濟條件打造真正意義上的遠洋海軍的國家中不乏失敗者。他們,最終沒有通過打造真正意義上的遠洋海軍給國家帶來興旺,相反,擁有了不適合的遠洋海軍,帶來了國家實力結構的崩潰。
中國的遠洋競爭對手
同樣,在我國日益具備了打造真正意義上的遠洋海軍的技術能力的同時,我們該不該著手打造真正意義上的遠洋海軍,如果要打造,該如何讓真正意義上的遠洋海軍的打造服務于國家崛起,而是不給國家崛起平添阻力。這些,都是中國人需要深思的。
日本,在沒有對于歷史有清晰的認識之前,無疑是我國宿命的對手。即便剝離了歷史,日本的戰略位置仍然決定了其在我海軍進軍遠洋的過程中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潛在威脅。我國發展海軍的過程中日本的感受,我國大可以忽略掉。特別是從中遠期的角度上來看,在龐大的經濟規模的支撐下,海洋力量對日本的全面超越和壓制是我國海軍建設過程中必然的使命。包括釣魚島和東海問題的解決,無論是和平方式或者不得已的戰爭選擇,都離不開強大的海洋實力。
俄羅斯,短期和中期內,兩國之間的潛在聯盟關系是很難動搖的。大格局下,雙方互相需要,共同支撐著世界大棋局上較弱的一角。然而,從遠期來看,俄羅斯的復興是必然的。豐富的資源,必將再次支撐俄羅斯成為世界上的一股重要力量。作為一個未來的強國,俄羅斯的選擇是多樣的,可變的。因此,現在可以被有效利用的來自俄羅斯的資源,在未來未必會一直能夠被有效利用。這就對我國的海洋崛起提出了一個至少二選一的要求。在我國在遠期與俄羅斯的戰略關系發生實質性變化之前,要么打造好真正意義上的遠洋海軍,要么打造好資源基礎。
印度,與我國的關系相對復雜一些,不確定性也要大上不少。至少,從當前情況來看,印度表面上和美國接近,以獲取實質性的利益。可是,在行動上,印度卻表現出了待價而沽的態度。在中美之間,印度暫時還不愿意做出選擇。因而,我國也必須考慮到在打造真正意義上的遠洋海軍的過程中的印度因素。
歐洲,雖然前景并不十分明朗,但是同樣是我國打造真正意義上的遠洋海軍的過程中不能忽略的因素。甚至,歐洲在未來世界大格局上的意義是無可替代的。其作用將要超過印度和俄羅斯對于中國的價值。畢竟,歐洲是未來可能的三極世界中不可替代的一極。僅僅這一點,就足夠奠定歐洲的地位。顯然,很難想象歐洲會偏袒中國。可是,歐洲也絕對不會過分偏袒美國。它如果想在未來的三極世界中獲得足夠的分量,那么大西洋聯盟的裂痕,必須要繼續拉開。也因為其中的互相作用關系,中國也可以間接地影響這一進程的速度。而這一進程的速度又直接關系到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速度。
如果說,在2003年之前,我們可以想象從陸地打開局面聯系中東的話,那么2003年之后,我們必須認清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美國的力量已經截斷了我們從陸地上聯系中東主要原油產地的通道。即便陸地能夠有所進展,主要還是在中亞方向,至多加上伊朗。這個時候,與俄羅斯的關系就顯得尤其重要了。龐大的資源背景和已經開始復興的勢頭,這都是我國所需要借助的力量。
中國應該優先發展的戰略關系
在中美歐框架內,我們必須與歐洲建立良好的關系,在中歐俄三角內,我們又必須對俄羅斯有所傾斜。也只有這樣,才是最為美妙的。而中美俄三角內互相之間的關系,又將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有多少資本可以用。前面看似矛盾的條件,卻并非不可能完成。其實,歐洲需要的是共同的經濟利益;而俄羅斯,主要是從政治上的支持。歐洲沒有辦法付出讓中國在中歐俄三角中支持它的代價。那么,結果顯而易見。
也正是在這個階段內,中國的力量倒是有可能涉及印度洋了。能做,并不意味著我們一定要去做。讓印度在這個階段信任我們是必要的。印度,在這個階段,也將開始從區域范圍內威脅到美國在波斯灣地區戰略優勢。一旦對抗開始,想要很快改變風向可就不容易了。如果中國進入了印度洋實力體系,那么結果是中國和印度成為同一實力體系中接近的兩方。與美國的慣性控制比起來,一個鄰接印度的國家的海洋威脅顯然來得更實際。
我國不是美國,我國還沒有解決的很多問題,美國已經解決了。這就意味著,我們自身的問題比美國要多。一方面,我們需要時間來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實力的增加又是我們解決問題的必需。正因為這樣,制衡力量的存在才顯得尤其重要。當年的冷戰,正是因為沒有一個足夠強大的制衡力量,才讓美國可以幾乎肆無忌憚地去與蘇聯進行全面對抗,最后把蘇聯拖垮。在那個時代,沒有任何一個除美國外的國家能夠接手蘇聯解體后的大量戰略遺產。這也就不存在蘇聯在自己行將崩潰之前刻意讓第三方賺便宜的機會。
實際上,只要前期和中期控制得當,到了這一時期,俄羅斯與我國的良好關系未必不能保持。多長時間,筆者當然無法預料。日本,也可能緩和起來。日本就是這樣,在絕對力量面前的選擇,某些時候還是比較明智的。至于印度,他的經濟當前比中國慢一輪。更重要的是,他在印度洋。在中東地區的石油資源枯竭之前,印度洋的重要性和西太平洋比,美國人似乎更愿意選擇印度洋。
印度如果愿意跟上我國的海洋步伐,那是他們的本事。美國是否會竭力在印度洋方向進行一場保衛戰,筆者認為,這是必然的。美國不會輕易讓印度控制了自己的命脈。在中國的命脈和自己的命脈面前,抉擇總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俾斯麥當年玩那么多球的壯舉,我們倒沒有必要重復。我們所面對的局面,還沒有那么復雜。關鍵是,有了思路,必須要通過細節的操作去實現。要讓有對抗意圖的雙方,都成為我們的朋友,就要分別與他們找到足夠的共同利益。
在這個世界上,一個我們可以有效掌握的共同利益就是自己的經濟。經濟不僅僅是真正意義上的遠洋海軍的物質基礎,同時也是建立一支真正意義上的遠洋海軍所必須的利益基礎。只有這個利益基礎在,我們才有資格去玩這個海權政治的游戲。
(摘自《兵器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