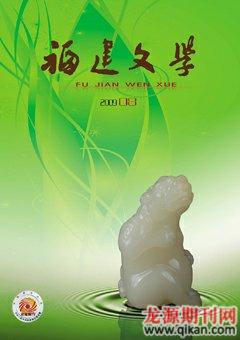雜豆粥
王兆福
我是女人,女人是要生孩子的,可我被斷定不能生孩子。我相信世界上很多女人和我一樣,都有著相同的煩惱。我渴望有個孩子。
副司令說,世上不生孩子的女人多了,也都活得好好的。副司令是我的丈夫。在家里我是正司令,家里沒有孩子就等于沒有士兵,我們倆就成了光棍兒司令。婆婆也在一旁安慰道,別想太多,好好過日子就得了。我婆婆就是我們的上級首長。我一直對這娘倆心懷感激,總覺得對不起老夏家,總是覺得欠了人家什么。
三年前,我和副司令我的丈夫夏天樂結合了,每次當他向我身體內射擊時,我都能幻想著有無數小蝌蚪爭先恐后地向深處游去,我感覺自己慢慢被這些小東西撕咬著,身體仿佛也被通上了電流。可是接下來的日子里,我的身體就像被遺忘的莊稼地,光禿禿地荒著。
結婚一年后,我和副司令去過一次醫院,接待我們的是一個身材高大的男大夫,有濃重的胡須,眼珠子有點兒發藍,第一眼看到他我就沒有好印象。他先是向我和副司令做調查,問的都是夫妻之間的事情。然后單獨和我們談話,問我的時候,問題很具體,我紅著臉很難啟齒也不敢抬頭,憑著直覺我知道,他那帶色兒的藍眼珠子一定是緊緊地粘在我的臉上了。接下來我拉上副司令小偷一般地逃離了醫院。后來我問夏天樂,那個大夫問你什么了,副司令說問我硬不硬,我說你怎么回答的,副司令說,我說開始硬后來軟。
流氓!我堅定地說。
我開始回避醫院回避醫生,親朋好友們說有病不背醫,扯淡去吧,一想起那位藍眼的男大夫我就發怵,面對一個男人對答如流地講述自己的性事,我覺得真是太傷自尊了。我對夏天樂說,那你自己去看吧,只要不是你的問題,不就明白了嗎?上級首長我的婆婆也在催促著夏天樂,小云說得對,你去看看就行了。
后來醫院的結論還是有了:副司令行我不行。我癟了。可是上級首長和副司令不僅沒蔑視我,反而更關心了,這樣讓我很感動。我想,我這一輩子命好,遇到了好人家。
后來就是副司令苦苦積攢的資源在我身上一次次地白白流失了,后來我的身體依然荒著,后來我成了一個不能生育的女人了,后來周圍的人們開始改變了看我的眼神。
有一天上級首長我的婆婆對我說,老家有位中醫世家的遠房表嬸,看女人的事很神,讓她給你瞅瞅。
婆婆帶領著我們回了趟老家,我見到了這位中醫表嬸,一位有著敦厚面頰的老太婆。她用溫濕的手指開始給我號脈,還捏了捏我的乳房,又抬頭看了看我的氣色,說,身子板兒不賴,你回去準備準備,過些日子你再來,我引薦你去一個地方,在那好好治上一陣子,我管保你好。說完了這位表嬸神秘地一笑,眼角的皺紋變化著很迷人。
回來的路上我一直納悶,這位女中醫很怪,看完病既不說病因也不開藥方,什么地方這樣神奇,能治我的病?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不過我還是盼望著,盼著能去那里看看。即便是沒有效果,到外面走走,散散心也不錯,我一直盼望能有一個機會和借口,讓自己換一個環境放松一次,我實在是受不了人們那怪異的眼神兒。
看著天越來越高,云越來越淡,我想屬于我的季節來了,于是我向單位請了長假說是出國探望生病的舅舅,向著北方去找那位遠房表嬸。
人有的時候就是這樣,越是離你遠的東西你越想靠近。
到女中醫家下了出租車,見曬場上早已停了兩輛轎車,分別是黑的和白的。一只大公雞率領著幾只母雞繞著兩輛轎車好奇地看,眼神兒中流露出一種期待。我一直認為,雞們是很有能力的動物,尤其是母雞,沒有公雞的參與,自己的理想都實現,照常按部就班地下蛋。
我進了表嬸家,屋里人不少,但都是站著,表嬸正埋頭在桌上寫著什么。屋里有兩條長板凳,一條是鐵木混合的,一條是椴木的。鐵木混合凳子上面坐著一男一女,衣著氣質都不俗,椴木凳子上面坐著一個和我年紀相仿的男子,頭發黑黑的向后背著,梳得很利落。看上去像是本地人,卻有一股儒雅的氣質。見了我好像一愣,然后向我友好地微笑著打招呼。我也矜持地向他點點頭,覺得這個人好像很面熟,而且是我喜歡的那類男人。這個想法的突然出現,嚇了我自己一大跳,我最近很怪,思緒經常開小差兒。背頭男子禮貌地將身子向凳子一端挪了挪,示意我坐下。我沒有謝絕,就在他的旁邊坐了下來。我忽然聞到他身上有一股特別的氣味,我很著迷,可我又一時想不起來這是一種什么氣味。
我估計這幾個人都是在等中醫看病的。中醫表嬸一抬頭看見了我,溫和地笑笑,說你終于來了。于是從桌子上撕了一張印著“毛氏診所”的便簽,寫上“老表親不孕,多添加一味藥。毛豆特別關照”,然后又從抽屜里拿出了一枚玉石篆刻圖章,哈了一口氣,深深地蓋了上去。對我說,凡事都有破解的法兒,病啊,一靠藥,二靠心。然后又對凳子上的那對男女和背頭說,你們幾個一輛車,我讓對五兒送你們。都是坑洼小路,你們要耐得住性子啊。
中醫老太太給他們每人一張和我一樣的處方便簽,便吆喝對五兒送我們上路。
那個叫對五兒的小伙子用搖把幾下就把那輛農用三輪車發動了,還提前放了一個木凳子讓我們幾個踩著登車。你別說,還多虧了這個凳子,如果讓我們四個人獨立爬上這輛農用三輪車還真費勁。我想,有的時候人們要成就一個愿望或者達到某種目的,還真的需要借助,尤其是當人們的理想和現實有距離的時候,有了借助就會達到目的,關鍵是我們選擇的這個“借助”是不是很合適。比方現在我們其中的一個干部模樣的男人,他的理想是要上車,可他的現實是挺挺的啤酒肚子,于是,一個凳子就成了合適的“借助”。在選擇凳子方面,看來還是對五兒有經驗,因為他經常接待病人,到這里來的病人,估計坐他的車都需要凳子的幫助。
路上我們和對五兒說笑,,啤酒肚子問對五兒,你這名字有意思,怎么起的啊。對五兒笑著說,小的時候和人家打撲克,人家出的對尖兒,我“啪”地就把手里的一對五兒砸下去,管上!人家說你對五兒怎么能管我的對尖兒啊,我說五比一大啊,怎么不能管你?看牌的人們笑得前仰后合,后來人們見了我就叫“對五兒”了,叫響了啊。我們聽了也都笑了。對五兒見我們高興,繼續說,出對尖兒的老蛋子現在可樣兒了,當鄉長了,最后還是管著我,命啊。
農用三輪車過一個土坎,對五兒加油,車尾巴冒起了一股嗆人的黑煙。
我用手捂住了鼻子,而思緒卻沉浸在對五兒和對尖兒的比較中。在撲克中尖兒就是一,誰都知道五比一大,可玩撲克游戲誰都想手里攥著尖兒別攥著小五,游戲的人們津津樂道誰都不懷疑一能絕對管五,甚至用一管小五那簡直是太可惜,因為除了四都能管五,四就是撲克中的草根兒了。人們習慣了一高高在五之上的規則,那是因為玩游戲的人們都知道,也許就在下一次,尖兒就會被自己抓到手!他媽誰定的規矩呢?只有像開農用車的對五兒這樣的莽撞孩子,剛剛學習抓牌不懂規則,才敢冒撲克游戲之大不韙,“啪”地將小五打在尖兒的身上。
哈哈。世上的事情真是太難說了,徒有虛名的事情太多,玩撲克五和一比五就是徒有虛名,在家我這個正司令和我丈夫副司令比我就是徒有虛名。
我們要去的地方叫“孟園村”。在一條小溪前,對五兒把農用三輪車停住,說,我的車過不去了,剩下的路你們自己走吧,只有半里多地了,看那座紅樓就是,不遠。
摸爬著幾塊大石頭過了小溪,往前走,路很好,莊稼也很好。紅樓是一座小學校,今天這里好像有什么慶典活動,孩子們在村里路上三三兩兩地往學校走,特別搶眼的是他們每人手里都拿著一個氣球,氣球上涂抹了各色的顏料,不是很均勻,所有的氣球好像都長著一個耳朵,像是喂嬰兒的奶嘴。等走到近前,我這才發現,原來他們手里的氣球,都是用安全套吹起來的。
村委會和學校在一個院子里,接待我們的是一位干凈利落的鄉村婦女,一見到我們幾個就快人快語:村里人都叫我毛豆嫂子,你們也這樣叫吧。我們各自獻上“毛氏診所”的便簽,她看了看又瞅瞅我們四個,一一對上號了。她說今天你們來得正巧,村里正在舉行一個支教捐贈儀式,南方一個電視臺捐贈我們村小學二十萬元。電視臺的上官臺長我見過,挺漂亮的一個人兒,就是年輕時得過中風,落下個歪嘴的毛病,話說快了還總擠眼兒。這病折磨了她整整十年啊,扎針吃藥還去過國外,不見效,去年在我們這里住了三個月,毛病治好了,把她高興死了啊。
毛豆嫂子越說越興奮,我們幾個也越聽越新奇,尤其是同來的那個女人,還驚呼道,真神兒啊。毛豆嫂子繼續說,你說上官臺長這個人兒可真心細,還捐來了一批防寒坎肩,給每個孩子一件。她說我們鄉下地寒風高,不能讓孩子們再受風寒了,她吃夠了中風的苦。
同來的女人又說,“孟園”可是聲名遠播啊,沒有毛老中醫的介紹還進不來呢。毛豆嬸子答道,你們都是有身份的人,治你們的病我們有把握,怎能不收啊。男人和女人笑得很舒展。
我又想起了孩子們手中的氣球,就小聲問毛豆嫂子,大人們的東西怎么被孩子們拿去吹氣球了呢?毛豆嫂子豪爽地說,我管著村里的計劃生育,串門的工夫就給女人們塞兩盒,我們這兒,男人們都不愿意用,富裕著呢。孩子們經常偷了吹氣球兒,村長說,村里總有捐贈儀式,需要慶祝,這氣球吹起來既結實又省錢,這法子不錯。
真想不到,本來既矜持又遮遮掩掩的東西一旦被改變了原有的屬性或者意義,新的狀態和呈現竟是那樣無拘無束逍遙大方。我問自己,這種改變需要什么條件呢?
背頭男人一直站在我的身邊,他身上的氣味讓我很舒坦,很陶醉。他問我你喜歡這里嗎?我說不錯。他說我叫K,經營一個企業,生產飼料添加劑。生意還好,就是外面的應酬太累了,患了失眠癥,經人介紹就到這里來了,既有躲避的意思也有看病的意思。我的目光一直審視著周邊的一切,包括村邊那一排高大挺拔的白楊。很久我漫不經心地問K,你身上是飼料添加劑的味道嗎。K疑惑地看著我,回答說,添加劑沒有味道啊,我身上有什么味道?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說,我也說不清。
我們四個被毛豆嫂子安頓下來了,原來村里已經住了很多病人,村里根據各自不同的病因和行業分了五個班:黑豆班、綠豆班、紅豆班、花豆班、黃豆班。紅豆班和黃豆班是女生班,黑豆班、綠豆班、花豆班是男生班。我被分在紅豆班。K和啤酒肚一個在綠豆班一個在黑豆班,那個女人分在黃豆班。
住的條件很不錯,都有獨立衛生間,席夢思軟床很干凈,唯獨床上都沒有枕頭。一問,說枕頭要到庫房去領。管庫房的人問,你在哪個班?我說,紅豆班。管庫房的人給了我一個裝滿紅豆的布袋兒枕頭。枕頭外表都相同,就是裝的豆子不同,分在什么班枕頭就裝什么豆子。
毛豆嫂子介紹說村里發展教育業和療養業,病人們都慕名而來,一傳十,十傳百。經過“毛氏診所”初診合格后才送到我們這里來,只要是覺得自己有病,城里的大醫院看不好,就可以到我們這里來,甭管是失眠、焦慮、疑神疑鬼、血脂高、血糖高、肥胖病、不孕癥、早泄、陽痿都包好。村里的收入主要是靠捐贈,到這看病的哪個不是在家或單位說了算的主兒,以單位的名義捐資助教,臉面上好看社會上也稱贊啊。我們也搞會員制,捐一次費,全家隨時看病療養。說到這兒,毛豆嬸子偷偷地一笑,經常有人帶相好的來呢。
第二天,村長給我們講了第一節公共理論課。據說,到這來的人,都要聽村長的公共理論課,這課對今后的治療至關重要。村長說,你們這些人都需要補氣,女的需要補陰氣,男的需要補陽氣,然后還要一起補地氣。你們太缺少地氣了。沒有地氣支撐的人,飄啊,浮躁啊,不知道天高地厚啊,膽大妄為啊,病就來了。你看我們村里的男人和女人,不缺地氣,干活吃飯心平氣和。不僅如此,不缺地氣的人,生孩子也隨人心愿,不用套子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就是靠男人和女人的陰陽之氣調節。陽氣足了就生,陰氣足了就不生。所以啊,上邊發的套子到了我們村,就成了孩子們手里的帶色兒的氣球了。
來這里的病人,每天的公共治療項目是參加村里的輕度勞動和日光曬蒸。輕度勞動包括推碾子和搖老式水車。
搖水車要兩個人一組,毛豆嫂子安排同來的男女一組,我和K一組,他們上午去搖,我和K下午去搖。我和K各自拿一個鐵搖把,套在水車頭的主軸上,水車頭兩邊有兩個淺坑,我和K左邊站一個右邊站一個,我俯下去,他揚起來,我們倆一上一下地搖,水車頭帶動履帶般的木舌,把水嘩嘩地從水溝里提上來,沿著壟溝流到地里去了,灌溉了村里的莊稼。這個項目可以喚醒腹部、腿部、還有手臂的肌肉,還可以喚醒人們的心智。搖了兩三次,我便找到了搖的玄機,兩個人合力干的事,一個人出力小了,另一個人就要出力多。于是我開始故意偷懶,身子抬起來的時候假使勁,K身子俯下去的時候,就有些吃力了。其實呢,兩個人的事情,只有兩個人心里最清楚,可是K佯裝不知。這樣搖了幾次我耐不住了,對K說,你這個人很狡猾。K詭秘地瞟了我一眼,把身體壓下去,說,我可是夠賣力氣的啊。哈哈,這個K很懂女人。女人最愛使小花招兒,不點破的男人是高手。
除去搖水車,我和K還去曬場推石碾子,就像城里殷實人家露臺上的走步機,讓人的腿運動,別閑下來,區別是:走步機是在原地運動,推碾子是做圓周運動;走步機有點假,推碾子實實在在。我推碾子,K就在一旁石凳上坐著看,K推石碾子,我也坐在石凳上對著他笑。
毛豆嫂子對我特別關照,這是個心腸很熱的女人,也很善解人意,她只比我大一歲。晚上我常到她的辦公室聊天,往往這個時候,K也在。有一天K中間出去了,毛豆嫂子對我說,我看K對你不錯,你們倆好像很投緣。我飛快地掃了她一眼,馬上把目光收回,沒有說什么。見我沒有反應,她又說,女人在世上漂泊,要順著水流兒走。
這話既像是說給我聽,又好像是說給她自己聽。我驚奇地發現,廣闊的鄉村沃土真是藏龍臥虎,這樣一位看似普通的鄉村女人,竟能這樣深刻地感悟生活、感悟人生,我自嘆不如。這一定是一個內心埋藏著很多秘密的女人,通過她我更有理由相信,在這里我所做的一切,自有它的道理。我還堅信,我的病只有在這里才能得到痊愈。我一定按規定做好項目認真吃藥,我能行。
藥是村長親手制作的,應該說是熬制的。
藥的制作過程很簡單,可制作時間很長,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朝九晚五是藥的制作時間。學校后操場有個棚子,青磚砌成的煙筒高高聳起,棚子里有青磚砌成的一個大灶臺,灶臺上有一口大砂鍋。據說前些年是一口大鐵鍋,后來改成砂鍋,更改的原因有兩個:一來鐵鍋風吹日曬容易生銹,二來鐵鍋不如砂鍋保護藥性。村長是個實事求是且雷厲風行的人,跑了好多地方才訂制了現在這個砂鍋。在灶臺不遠的地方還有一口水井,水井旁長著一棵枝杈嶙峋的老槐。提水用的轆轤、繩子和木桶就拴在老槐的一條橫杈上。
豆皮兒和豆花兒初中畢業就不上學了,幫著村長熬藥,做著熬藥前的準備工作。每天病人們起床梳洗完畢,必須把自己枕了一宿的豆子抓出一把,放到灶臺前的一個鐵篩子里面。每當這個時候,操場上的氣氛都會顯得不同尋常。人們排著長隊,恭敬而虔誠,每一個走到鐵篩子面前的人都會放慢腳步,盡量把放豆子的速度縮短到最低點。
“黑一把”,“花一把”,“紅一把”,“黑兩把”……豆皮兒在篩子旁一邊檢查一邊報著數,豆花兒在一旁記錄。豆子放完了,豆皮兒從水井里提水沖洗滿篩子的豆子,反復三遍,各色豆子經井水一洗,精氣神十足,豆皮兒和豆花兒一起把洗好的豆子倒進砂鍋。
人們準備豆子的時候,村長在棚里忙著勾兌他的莊稼根兒液,他面前的架子上,整齊擺放著很多玻璃器皿,浸泡著莊稼植物的根莖,土豆的、紅薯的、胡蘿卜的、生姜根的、白菜根的、苦菜根的、稻草根的、小麥根的、高粱根的……這時的村長很像一個化學家,用吸管把這些浸泡液提取出來,混合到一個廣口瓶里,輕輕地晃動搖勻,然后一股腦地倒進砂鍋,豆皮兒和豆花兒這才把砂鍋加滿了水。
“點火!”村長吆喝著。高粱稈、玉米秸、豆稞子、麥秸以及雜木劈柴燃燒了,青磚煙筒里升起濃重的煙,煙中夾裹著莊稼群體燃燒時特別的味道,漸漸彌漫在操場四周,然后升高變淡向著“孟園村”以外的地方飄去。
我們的藥要在太陽落山前吃。每一人一個小木碗,一只木勺。豆皮兒和豆花兒忙著給病人們盛熬好的粥。村長說,吃嘛補嘛,這味藥叫“雜豆粥”,大補人體需要的地氣。
我吃雜豆粥的時候忽然想起了臘八粥。北方在農歷臘月初八,有熬臘八粥的習俗。和夏天樂結婚后,年年的臘八,婆婆都要熬粥。婆婆熬的臘八粥,用料很講究,都是食品中的上流階層,主料除去豆子還有福建的桂圓、河北的紅棗、新疆的馬奶子葡萄干,外加上好的冰糖。我覺得太甜、太膩,往往吃上幾口就給夏天樂了。而村長制作的雜豆粥不同于臘八粥,粥體很稠,口感很香,吃一口,酸中帶甜,甜中有苦,苦中好像還泛著辣,入口就化,一絲特別的氣息穿過喉嚨,便會通透全身。
我曾問毛豆嫂子,這雜豆粥和臘八粥差不多,又不是藥能治病嗎?
毛豆嫂子一臉莊重,說,雞蹬食,狗刨食,豬拱食,各有各的道兒,村長的藥看療效。
我開始留心這個女人的語言,我確信她的話是對的,我也確信這藥能治好我的病,因此我每次吃粥的時候都很認真,吃完之后,小木碗總是干干凈凈的。
K總是和我一道吃,他說這粥很像他們生產的飼料添加劑,是個補充,而且是關鍵的補充。我發現K也是一個很有思想的男人。我還發現不論做什么,自己好像總是和K在一起,有時他偶爾不在,我好像還很牽掛他。
一天我和K去搖老式水車,累了我們坐在水溝邊歇著聊天,這時突然有一條花蛇從草叢里爬了過來,我驚叫一聲,下意識地躲進了K的懷里,K也摟著我說,蛇怕人。然后扶著我迅速離開了水溝邊。
自從“花蛇”事件后,我和K的感情在悄悄升溫。也許是離開家太久了的緣故,我的丈夫夏天樂,在我的世界里漸漸變淡,K在我的世界里一天天清晰,白天有K陪伴,我很開心,深夜我卻獨自一個人瞪著窗外的樹影發呆。
同屋的女醫生,早已鼾聲如雷,我卻清醒得如高空之上那輪朗月。和女醫生一道來的啤酒肚是她的同學,著名的私家偵探,患了幻聽癥,總覺得有人在身邊竊竊私語。女醫生是一位外科醫生,最近患了色盲癥,經常把灰色看成紅色,這令他們很煩惱,并結伴而來。真是職業好,身份好,收入好。這對“三好”男女一個要探究一個世界,一個要拯救一個世界,唯一的遺憾就是,兩人都身體有疾患。
世界上有多少男人和女人和他們一樣,忍受著各自不一樣的煩惱呢?
這天晚上,我和K又聚在毛豆嫂子那聊天。聊了一會兒,毛豆嫂子說家里來親戚了,你們就在我這兒呆著吧,我這里清靜,走的時候你們把門給我鎖上就行了。
我和K都沒有回住處的意思,話題就聊到了我同屋的女醫生和私家偵探。K說,我們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和國際接軌,比如私家偵探行業,你看人家國外電影里的偵探干練敏捷,而再看看我們的私家偵探,腆著啤酒肚子,如何翻墻越脊,追影潛伏?等他氣喘吁吁爬上樓,嫌疑人早跑了,他就光剩站在那里喘了。
哈哈哈……我笑得噴了一口水,鼓動著說,我們的偵探主要是靠推理,就像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中的偵探波羅,不也有一個大肚子嗎?K反駁說,人家肚子里裝的是智慧,我們偵探肚子里裝的都是啤酒。人家波羅思考問題的時候還叼著一個大煙斗呢,我們偵探叼什么,叼奶頭還差不多。
我被K一浪高過一浪的幽默掀動著,自己仿佛就是浪尖上的一只小舟,身不由己飄忽不定。我們天南海北地聊著忘記了時間。K拿走了我的杯子,添了些開水捧給我,溫情地注視著我:喝吧,不燙。
我一飲而盡。一種感動撞擊著我,一種欲望脅迫著我,我覺得我在飛,身子很輕,臉很熱,心中像有一團火。我好像入睡了。
“粥……粥……”我軟在了K的懷里。
氣息,神態,迷離的眼神,還有聲音,以及我扭動的身姿,還有悄悄流動的欲望一起飄過來,我會被突如其來的陽光震蕩得眩暈,會發出美妙的歌唱。我就是一架精美的鋼琴,渴望有一雙神奇的手指,在鍵盤上多情地游走,不斷激蕩出最敏感的音符,我知道,在山谷中,一道淺溪在靜靜地流淌,灼熱而激動難以控制,那是醞釀了很久的熱流,肆無忌憚地在谷底蔓延,淹沒了柔軟的荒草地,那里渴望復蘇,渴望一道陽光般的光束,有力地射入幽深的谷底,讓谷底的春天提前到來……
陽光很暖和,照在了我的臉上,我醒了。
我發現自己躺在毛豆嫂子辦公室的床上,身體第一感覺就是乳頭有些微痛,還有就是女人的敏感地帶。我明白自己失身了。
我就這樣躺著,不想起身,此時我的心態很復雜,操場那邊人們已經排隊交豆子了,豆皮兒的喊聲也斷斷續續傳過來:“紅一把”,“黑兩把”……
聽著聽著,我的淚水已經淌滿了面頰。
K離開了“夢園村”,他沒有向我告別,說有一單涉外生意急著簽,這是毛豆嫂子告訴我的。我知道,對許多事,毛豆嫂子心知肚明。
我堅持喝粥并參加毛豆嫂子安排的項目。在這些項目中,其實我最喜歡日光曬蒸。
村長在他的第二節公共理論課上這樣說,陽光總是被人們忽視,衣服總是把人們包裝得嚴嚴實實,衣服樣式千變萬化,本來一樣的身體也就千變萬化了,衣服遮擋了陽光和皮膚接觸的道路,皮膚就要發霉,發了霉的人就會有病。人們要努力延長光著身子的時間,延長和日光接觸的時間。
“孟園村”有兩處日光曬房,一座男的專用,一座女的專用。日光曬房建設得很講究,遠遠看去像是水晶的建筑,傾斜的房頂全部用玻璃安裝的。走進曬房熱浪撲面而來,馬上讓人覺得任何衣服都是多余的,頓生要把自己裸露的欲望。
在K走后的時間里,我幾乎每天都要到這里來。
陽光透過玻璃熱烈真誠,絕不放過任何肌膚任何角落,甚至還會讓人們發霉的情感復蘇。曬房里全是裸露的軀體,放眼望去真好像是一幅“蓮藕豐收圖”。
我喜歡一個人裸著身子在這里呆上一個上午,不斷變化著身體的角度和太陽默默地交流。
人一旦溫暖就會有欲望,俗話說,飽暖思淫欲,這話一點都不假。有時在太陽的撫摸下,蠢蠢欲動的念頭會像一把小撓子兒,在身體的各個角落不停地撓,讓你在人體的生理黑洞里焦急地徘徊。一想到生理的概念,我心里一驚,我算算時間,壞了,我發現該來的沒來。我的生理周期一向很準,我有些擔心。又等了一周,還是沒有動靜,我開始吃驚了。我確信自己一定是懷孕了。這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是K,一個是這里的治療,尤其是村長的雜豆粥。
我開始不安了,腦子飛快思考如何處理自己的身體。就在我不安的同時,我更多地還是敬畏“夢園村”、敬畏村長、敬畏砂鍋,還有那味叫“雜豆粥”的藥。就這樣惶恐與敬畏著,我接到了夏天樂的電話,說婆婆不行了,讓我馬上回去,我的病也不用治了。我馬上收拾,并向村長、毛豆嫂子還有豆皮兒、豆花兒告別。我拿出了五千元錢交給村長,當時我有兩句話要說:第一句是謝謝你們讓我夢想成真,第二句是這錢算是我給村里孩子們的捐助,讓他們也夢想成真吧。可是我只說了第二句,第一句話我永遠留在了心里,沒說。
回到家的時候,婆婆已經走了,親戚朋友們都在幫著料理上級首長我的婆婆的后事,奇怪的是在忙碌的人群中,我好像還發現了K,他一直低著頭,跟在夏天樂身邊。他怎么會出現在這里,并且和夏天樂早就熟悉。這個問題在這樣的日子里我也不便向夏天樂多問了。
也許是身子太虛弱了,也許是心理上有沉重的壓力,反正在處理婆婆的后事的某一個時候,我眼前一黑暈倒了,等我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身邊還有一個鄉村的老太太正拘謹地看著我。見我醒來了她很是高興,說道,閨女可把你盼得睜眼了。她見我疑惑就自我介紹說,我是天樂的嬸子,在這里照顧你。
天樂呢?我問道。
嬸子搖搖頭說不知道,只是拿出一封信給我,我心有些緊張,很久不愿意把信打開。我在和我的耐力抗爭。
轉眼到了農歷臘八,按照北方的習俗,要熬臘八粥。我去了趟超市,買了一袋雜豆熬了一鍋臘八粥,盛了一碗放在桌上涼著。我的眼睛先是定在這碗粥上,然后慢慢移開,掃描著屋里的一切,最后還是落在夏天樂留給我的信上,我再也抗拒不了了。
我的丈夫夏天樂在信里寫道:小云,我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支教了,不要打聽我,你要好好照顧自己。其實你沒有病,問題在我這里,媽不讓告訴你,醫院的結論也是假的,和你一道去的那個做飼料的廠長,是我老叔家的三兒子,都是提前安排好的。媽的意思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眼里的文字慢慢變得模糊,桌上那碗雜豆粥中不斷有熱氣升騰,漸漸地把我的身子包裹住了,讓我變得沒有了半分力氣。
責任編輯 練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