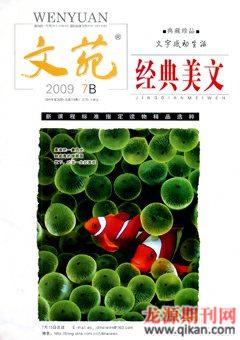我們為什么讀書?
雷 達
本期話題:
誰在偷走我們的閱讀
一份資料表明,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每年人均購書量不到5冊;國民閱讀率連年下降,每年有超過一半的識字成人一本書也沒讀過。
這已經是一個讓人觸目驚心的數字,但是請注意,在那可憐的不到五冊的人均購書量中,有多少冊是《鐵路列車時刻表》?有多少冊是《城市交通規則》?又有多少冊是正在匆忙應對大中小考的學生們為我們分擔的?一冊?兩冊?還是三冊?
毫無疑問,我們的閱讀正在被人不知不覺地偷走。
也許在拿“書”用做“敲門磚”的人生階段結束之后,對許多人來說,那是至今記憶慘痛的時光,從五六歲開始,童工般地背著沉重的書包去上學,行走在早晨與黃昏灰暗的路燈之下,心中的歡樂和光明也一點點死去,于是再也不碰這種印成一冊一冊的東西。
可是聽聽自己心靈的聲音,在這片空曠的田野上,怎能缺少一束溫暖的陽光、缺少一片遼闊蔚藍的天空?
找回我們的閱讀吧!讓閱讀的泉水,重新灌溉我們的心靈。
常問作家為什么寫作,也就常問作為評論者的自己為什么讀書。為了心靈?為了生存?為了功利?為了消遣?為了改造世界的抱負?
在我看來,從來不問這個問題的人不是讀書的人。在這個浮躁的時代,凡是追問這個問題,并陷入苦惱的人,也許才是真正靠近了讀書意義的人。
人生苦短,幸虧有了書,人類在時間和空間上才能把見聞擴大無數倍,有的甚至等于多活了幾個人生。在書中流連忘返,善于汲取精華者,是珍視人生的本質與自由的人,是心靈的向上者。當然,人們讀書的目的不可能是單一的,多樣目的交叉并存。可是,當根本性的需求變得茫然的時候,就會出現閱讀的危機。
3歲的時候,父親因病故去,留給我們的似乎只有沉重的書了。小時候的我很孤獨,常在書架間獨來獨往。雖然這些書我根本看不懂,但它們似乎給了我一種神秘的力量。
及至能讀一點書時,記得首先翻開的是梁啟超、魯迅等人的書。那時當然不知好在哪里。直到漸老時才意識到,其實他們已經來到了我的靈魂,在悄悄開啟我的心靈之門。
我把這樣的讀書統稱為心靈的閱讀,盡管有時也帶有為寫作而吸吮營養的急迫目的,但能讀得進去,靈魂是投入的。
可是近年來,情況發生了變化,我的讀書生活也隨之出現了危機:想讀的書,永遠沒有時間讀,不太想讀的書,卻占去了大量時間,而且永遠也讀不完。我好像在進行著一場永無盡頭的長跑。有時會產生荒誕感:看似永遠在讀書,又好像永遠沒有讀書;或者,不知我在讀書,還是書在讀我?我也想好好地讀一批好書,把它們放到書桌最顯眼的地方。可是一年了,兩年了,除了翻過前言提要,還是顧不上細讀。它們已擺了很久,好像對著我冷笑。
當然,這跟我的職業也有關系。我是習慣于對創作思潮和文學作品發言的人,可現在作品數量激增,動不動數以千計,即使選擇很小部分,也是驚人的數字;更要命的是,真正經得起閱讀的書沒有幾部,大部分書因為貧血和缺乏真切體驗而不好看,卻又不能不看。于是,我的讀書姿態常常是:一卷在握,正襟危坐,每個細胞都很緊張,為的是在最短的時間抓出一些要領,形成一個評論的框架。所謂藝術的直覺,沉醉自失,含英咀華,都談不上了。我讀得專注,讀得累,可就是沒有發自內心的感動。這不能不說是讀書的異化。我把這種閱讀叫做“實用閱讀”或者“功利閱讀”。
我不知道,像我這樣得不到閱讀快感卻又不停地大量讀書的人,現在到底有多少,這個隊伍是否還在擴大?但我知道,為了拿碩士、博士頭銜和教授、研究員職稱,天天硬著頭皮讀著并不愛讀的書的人,不在少數。至于為了出“學術成果”,為了發“權威”,發“核心”,殫精竭慮,刻意把文章弄成一種標準模式的,天底下真不知有多少。這些文章大都不是為了讓人看的,而是為了拿來“實用”的。也許這一切情有可原,但總得給心靈的閱讀留出空間,讓讀書回到讀書的本義上去:在精神原野上的自由馳騁。
現在,我很懷念這樣的我:在書店的一角斜倚著,默默地讀著,不覺天已黃昏;在圖書館坐了一整天,閉館的電鈴聲響了,周圍的人都走了,我滿足地伸了一個懶腰;午睡時看書,書掉到地下了,我也沉沉睡去……所以,有一天,當我的一個學生問我,我們為什么讀書時,我說:為了心靈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