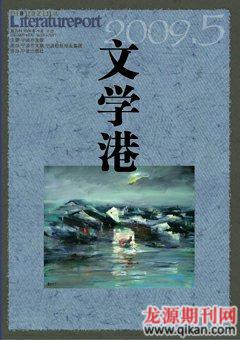病床上的母親(外一首)
陳洪標
苦命的母親,每次父親帶她來杭州
都是上醫院,做各種檢查
沒有一次是特地來玩的
也沒有一次是輕輕松松的
父親肩上挑著,手里拎著
有風濕病的母親,手里拎著,肩上背著
家里現成的,地里剛收的
能帶的都帶上了
大米、黃豆、芝麻,土豆、蘿卜、毛芋
都是自家種的,沒有農藥不用化肥
番薯淀粉、涼粉、湯圓米粉,甜酒、米酒、高粱燒
都是母親親手做的
一年四季,變換花樣
我的兩室一廳大獲豐收
成了老家的谷櫥和地窖
這樣每次汗里來雨里去
他們最多呆不過三天
就要急匆匆回去
每次回去,帶回家的
不是醫生配的大包小包的藥
就是醫院各種檢查的片子
這次來,苦命的母親
挨了一刀,把右乳房全割了
十天前,母親只是感覺有點痛
到鎮上的衛生院一檢查
醫生說,有腫塊,要上大醫院
這一來,一時就走不了了
在病床上,母親每天在算
再過幾天能回家了
其實,母親很后悔
早知道會這樣,就不該來
一點小病小痛,看出了大麻煩
花了這么多錢
我和未婚妻,還有不知內情的父親
輕聲細語,用各種辦法安慰母親
像小孩一樣哄著
善解人意的母親,看看我們
終于給放寬心了,穩定了情緒
妹妹和妹夫,小弟和女朋友
趕來了,母親很難為情
忍著傷口麻藥剛過的陣痛,咬著牙
非要從病床上坐起來,說你們這么忙
不用趕來看的,沒什么大事
母親心里過意不去,眼里濕濕的
囑咐我們大家不用為她擔心
苦命的母親,她還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還以為,很快就可以讓父親帶她
回家
母親心中的一盞燈
白天,母親總是手忙腳亂
跟在父親的屁股后面
累得一會像牛一會像馬
一些在田地里勞作的方法或姿勢
經常被大聲糾正,或者被阻止
有時,還會被嚴厲催趕
毫不留情面
母親低著頭,心里窩著的火
一個勁往手里的鋤頭使
可是,再受氣,只要一抬頭
看到眼前的這個男人,背上的汗水
嘩嘩的,母親心就軟了
硬梆梆的一肚子氣,噗嗤一聲
沒了。母親在心里嘆一口氣
這個干活不要命的主啊
帶著一陣暗自的心痛之后
倒像自己做錯了事
乖乖地跟在父親后面
悶聲不響,不敢回話
不敢頂嘴,更不敢偷懶
忙完一天的農活
到了晚上,母親從勞累中起來
慢悠悠地,點上了心中的一盞燈
熟練的樣子
很像干農活的一把好手
這已成了母親夜里的一種習慣
四十年了,沒有一天不是這樣
母親心中的這盞燈
從二十歲嫁到陳家開始
就一天接一天地點著
之前,為娘家的父母兄妹點著
為偶爾出遠門的男人點著
之后,圍著孩子轉
三個兒女,三盞燈
每天晚上點在母親的心頭
有時全點著
有時點了這盞點那一盞
有時一盞又一盞的,在走馬燈
有時點得太多,睡不著
有時累了,累得睡著了
那點在心頭的燈,還亮著
柔和的透透的光暈
像浮在池塘中的一輪明月
很寧靜很安逸
有時,連母親自己也不知道
這盞燈,為什么從來都不需要特意去點
也不需要添些燈油
自己就汩汩地如山泉水一樣
入夜而來,天明而去
六十歲的母親只知道,這盞燈
在家中的地位。它是一個家的象征
是她與遠離家門的子女
心靈交流的一種古老儀式
父親當兵出身,年輕時不懂
一個女人最樸實的秘密和武器
現在一起生活了40年,慢慢明白了
也能看到母親心中的這盞燈
跳動著,淡淡的火苗
緩緩的很平和,外面裹著一層層
囑咐。擔心。牽掛。還有渾濁的淚水
像成年的蠟燭油,積掛在邊上
默默無聲
一天,六十七歲的父親終于知道了
母親心中的這盞燈是什么
愁
是母親點在心中的一盞燈
為突然長大飛走的子女
為身邊一天天少去的親人
被淚水和思念包圍的這盞心燈
濕濕的,醒在每天深夜的某個時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