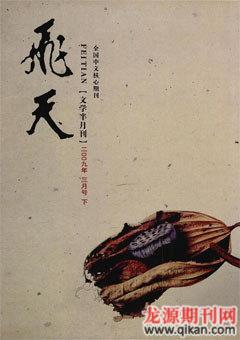論《歷史的天空》不確定性的智慧
李 潔
“塞萬提斯認為世界是曖昧的,需要面對的不是一個唯一的、絕對的真理,而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對真理(這些真理體現在被小說人物的想象的自我身上),所以人所擁有的,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一種不確定的智慧,做到這一點同樣需要極大的力量。”
作家徐貴祥的作品《歷史的天空》憑借著特殊的詩性力量獲得了第三屆人民文學獎,第十屆全軍文藝獎,第八屆全國五個一工程獎,第六屆茅盾文學獎,而這種詩性力量就是體現在作家所描繪的一片歷史的天空,他記錄了一個特殊的年代,書寫了一段奇特的人生——主人公梁必達(梁大牙)因逃避日軍迫殺到凹凸山投奔國民黨軍,陰差陽錯闖進了八路軍的根據地,從此走向了戰爭和政治,在復雜的政治斗爭和激烈的戰爭中,逐步顯示了優秀的品質和卓越的智慧,由一個不自覺的鄉村好漢成長為一名足智多謀的指揮員,最終修煉成為一名具有高度政治覺悟和斗爭藝術的高級將領。小說在戰爭虛實和營造戰爭氛圍上采取了虛實隱約的寫法,因為“實”而具有歷史縱深感和現實意義,因為“虛”而頓生空靈灑脫。隱隱約約,虛虛實實,使整個作品在“不確定”中體現出作家的寫作智慧。作家所展示的是“曖昧”世界中的歷史與民族戰爭,一切顯得復雜而迷霧重重。當農民和軍人雙重身份集中在同一個人的身上,當國軍、共軍雙重的政治立場面對同一場民族戰爭時,作家的書寫方式仿佛“不確定”起來——他想通過這種模糊來還原一個真實的歷史,同時,帶著對戰爭的冷靜思考和悲憫的情懷,作家想書寫一種真實的人生。“戰爭作為人類生活的非常態,它最會暴露人性中最原始、最深層、最復雜的種種欲望和要求,每一個人的靈魂在戰爭面前呈現出它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所以作家在創作中便體現出一種非確定性的智慧——憑借這種智慧,作品《歷史的天空》打動了很多人,它把讀者帶回了那段硝煙四起,金戈鐵馬的歷史天空之下,同時引發人們去觀照戰爭,觀照自己,觀照人生。
一、文本中的形象塑造
徐貴祥在《歷史的天空》中將章節段落的銜接基本處理為“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格式,交替地寫八路軍和國民黨軍兩組人物的各自的事件場景。兩位主人公梁必達、陳默涵各牽一線,各想其主,誰知陰差陽錯,想投國軍的梁必達邁進了八路軍陣營,幾番思考便抱著“咱還是先當著試試,合適了咱就當到底,不合適了再說”的態度成了八路;而陳默涵也歪打誤撞,抱著先保住性命他日再投共軍的念頭邁進了國軍陣營。作家在兩位主人公的道路選擇上便賦予其一種難以確定的色彩,面對未來將如何作出自己的選擇?將自己有限的生命置于怎樣的政治立場之中?在文本中,我們沒有看到人物一開始就抱著如何如何圣潔的政治信念,也沒有看到人物的思想覺悟處于一個怎樣高的層次,他們似乎并沒有成為所謂的命運主宰者,反而有一種造化弄人的無可奈何,這種偶然使他們的命運顯得游移不定,無可奈何,這種偶然使他們的命運顯得游移不定,讓無數人平添種種設想。
兩條線索互相交替,以梁必達、陳默涵為中心衍射出一群活靈活現的人物——知人善用的梁庭輝、堅持原則的張普景、溫柔可人的東方聞音、英勇善戰的石云彪、軍事素養深厚的莫干山、素有巾幗之氣的高秋江……作家的可貴之處在于沒有將“國”“共”兩黨的政治標簽分門別類地貼到各屬其主的人物上去,沒有讓國民黨軍顯得十惡不赦,丑態百出,相反,描寫了一群真正為民族大義獻身的錚錚鐵骨。作家沒有吝惜地將崇高之感置于他們身上,讓所有的人看到了首先作為人,然后是國民黨軍人的一群“中國式的脊梁”——高秋江對莫干山的一往情深讓我們理解了一個女軍官的俠骨柔情;莫干山、石云彪戰死沙場同樣具有勾魂攝魄的動人力量。作家從對人的終極關懷出發,注意表現軍人的人情味。他沒有拘泥于國共這一政治界限,使人格成為衡量人一生最可靠的標桿。人格在這種不確定中成為一種信仰,超越了集團、政治,使得歷史可以理解,使得權力得以制約。同樣,作家也沒有極力去塑造所謂的“高大全”形象的共產黨人的代表。他沒有勾勒出理想的完美英雄,也沒有描繪一個“神性大于人性”的傳奇英雄。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梁大牙是一個英雄,但這個人物所打動人的不是他的殺敵無數,也不是他過人的戰略戰術,而是他身上的那種平民化、人情化、人性化的味道。作家已經打破了以往軍旅題材寫作的固定英雄模式,而是通過一種“消解”的方式,甚至可以說是用“不確定”的英雄模式去勾勒一個另類的英雄,這個人物突破了我們以往對待英雄的固定認識——似遠似近,若有若無,亦正亦邪,集人性、神性于一身。梁必達時而是一個農民,時而又是一個軍人,時而顯得無賴,時而又剛正不阿,他的出現,讓歷史的天空深不可測,使那些探究歷史根由,尋找歷史真實的人們陷入黑暗與光明永恒的交戰之中。他的性格顯得復雜而又神秘:“在他的靈魂世界里,深不可測,波譎云詭……他的智慧和他的神秘同樣是除他本人以外的任何人也休想探究的。”作家將這種不確定感置于梁大牙本身,使這個人物形象更具光彩和魅力。
作品本身就像一個波濤起伏的大海,而人物便被作家拋向了起起伏伏的浪潮之中,人物命運沒有被規定最后的方向——由他們本人開始了優勝劣汰的角逐,因此人物的命運發展就顯得迷霧重重——開始分道揚鑣的梁必達、陳默涵幾經輾轉最后殊途同歸;開始與梁必達在同一陣營中的江古碑,李文彬卻在權術、陰謀的較量中被扔進了歷史深處;眼看與梁必達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東方聞音卻在殘酷的斗爭中過早的香消玉殞。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什么是善?什么是惡?先前主張秘密槍決粱必達的張普景成為了他一生都無法缺少的“諍友”;被梁必達時時稱作“白匪”的陳默涵卻在“文化大革命”中與他相互扶持,走過了生命中最艱難的歲月;與梁必達出生入死,經歷槍林彈雨的朱預道卻在“關鍵時刻”把梁推到了政治斗爭的風口浪尖;看似革命立場堅定的江古碑也僅僅是玩弄權術的陰謀小人。作家讓人物變得不可捉摸,他們的性格一直在發展,徐貴祥在面對歷史時提出了很多的問題,但他始終不想給人們一個確定的答案——歷史是確定的,但人性是復雜的;理想與價值是確定的,但人的行動卻難以捉摸。在確定與模糊的矛盾之中作者使所有的讀者領略到歷史的本質,使我們看到了那個特殊年代中國人真實的存在。
二、文本中的價值判斷
克羅齊曾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作家徐貴祥將對戰爭、成敗,歷史,英雄的全部思考貫穿于《歷史的天空》之中。在這個漫長的思考過程之中,作家盡力避免主流軍旅文學從主觀意念出發,把人物變成階級群體的符號,而是盡量還原歷史,淡化以傳奇為主的英雄模寫范式。開始對早已形成具有普適性的問題進行重新的價值判斷,而判斷結果所呈現出的不確定形態引發了人們更多的思考。
什么是英雄?建國以來,軍旅文學創作中涌現了無數個英雄形象——智勇雙全的少劍波,孤膽英雄
楊子榮、寧死不屈的江姐、許云峰、齊曉軒、華子良。作家們為了突出的表現英雄人物的光輝品質,有意識地隱退他們的一些不重要的缺點,使其在作品中成為群眾向往的理想人物,“高大全”成為英雄人物身上確定的品質,這些原則也成為了衡量許多作品人物塑造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但這已確定的審美范式卻日益引起讀者們的審美疲勞。當《歷史的天空》以一種另類的方式塑造了一群另類的英雄,作家把所有的人都放置在戰爭這一非常規的狀態之中,無論是誰,梁大牙、張普景、莫干山、江古碑、李文彬等都會暴露人性中最原始、最深層、最復雜的種種欲望和要求,每個人的靈魂在戰爭面前都會呈現出它的多樣性和復雜性。“英雄”首先是一個人,他無法擺脫生存、情欲的干擾,作家淡化了“神性”,甚至消解了長久以來附在英雄身上的崇高色彩。梁必達最初看來是一個貪財、好色、匪氣十足的無賴,誰都無法將他與日后的英雄聯系起來,但伴隨著他的精神成長,這樣的英雄卻讓所有的人信服,他是可觸、可知、可感的;陳默涵飽腹詩書,雖然“誤入”國軍,但他就是中華民族脊梁式的人物代表之一;東方聞音嬌小可人,看似手無縛雞之力,但她用生命譜寫了巾幗不讓須眉的贊歌。還有莫干山、石云彪、張普景、高秋江,他們早已顛覆了以往英雄的形象,但作家從不同的角度描繪了他們一點一滴的精神成長過程,用一種不確定的命運偶然成就了他們成為英雄的必然——他們是人,同時他們的人格閃爍著人性的光輝,這種人格成為一種終極審判,基本價值與永恒正義。作家沒有給予英雄一個確定的定義,卻使“人格”在這種不確定性中成為一種確定的信仰,超越了集團,政治。在作品中也有過這樣的表述,“文革”中梁必達在勞動農場與陳默涵傾心交談,曾如此言道:“現在我有個重要的體會,好人就是好人,放到哪里他都是好人,壞人就是壞人,放到哪里他都是壞人。江古碑參加八路,有很大的偶然性,他就是參加了國民黨,他還是個壞人。參加什么組織可以選擇,選擇的過程也有偶然性,但是要當好人和壞人就不是偶然的了。”
什么是成敗?作品并沒有“以成敗論英雄”,但徐貴祥描寫戰爭年代,必然會思考成敗。在文本敘述中,作家縮小了“戰場”的敘事份額,淡化了民族戰爭必然會最終取得勝利的樂觀情緒,而聚焦于戰爭中本民族內部的權力斗爭。梁必達親歷的這段革命歷史不僅被黨派之爭搞得撲朔迷離,還籠罩著紛繁復雜的黨內派系爭端。作家已經無法用成功與失敗去定性政治事業的運作中都無法規避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猜疑、算計和爭斗的內耗。無論成功還是失敗,都是伴隨著人的陰謀、權欲、死亡、流血、犧牲、痛苦,但正是這些無法避開的斑駁雜色呈現出人的一種真實的生存狀態——梁必達該任縣大隊長還是該槍斃?縣大隊長(梁必達)同縣委書記(李文彬)的文武斗法;極“左”當道的“純潔運動”;運動之后的“李文彬事件”;“文革”中江古碑興風作浪;“文革”后梁必達與竇玉泉最后的競爭,這一系列的政治傾軋帶來了很多的苦難和死亡。成功、失敗,對任何一方來說都是一種不人道——戰爭是不人道的。政治斗爭是殘酷的,但這一切都是歷史向前發展必然經歷的過程,作者在一種不確定中得出的獨特的價值判斷,才使人們對戰爭的反思更加深刻,才使歷史本身顯得真實,也使文本《歷史的天空》更加具有當下性。
三、作家的審美范式
軍旅評論家朱向前的《在“兩個參照”中閱讀王伏焱》一文中:“畢竟時代變了,90年代不同于80年代——這是一個社會轉型的時代,暫時的價值失范和消解英雄,導致了軍人地位的邊緣化和神圣光環的淡化。”其實,朱向前所描述的就是90年代以后很多主流意識形態的作家所面臨的文學生態環境。
伴隨著20世紀八九十年代商品經濟的沖擊,文化大眾化和大眾文化日益充斥著我們的生活,電子技術的發展,媒體宣傳的泛濫,使作為主流文化的“傳聲筒”之一的軍旅文學的神圣光輝一度暗淡下來。新時期文學的生態環境悄然嬗變,政治語境迅速嬗遞為商業語境,使軍旅文學的創作者們無法像五六十年代的紅色小說家那樣一覽無余地傾瀉“被規訓的激情”。作家們試圖開始進行一系列的嘗試——崇高的消解,反精英的英雄敘述模式。作家徐貴祥在《歷史的天空》中同樣努力做著這方面的嘗試。
固定的審美范式被打破而又未及時建立新的審美普適價值時,勢必會使許多創作者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作出種種不同的嘗試,而本身的這種嘗試就帶有不確定性。
小說《歷史的天空》的結尾看似一個“大團圓”的結局——梁必達轉移戰爭目光,開啟現代化軍隊建設。但整個小說仍然籠罩著神秘感——李文彬被俘和死亡成為一個被多種不同觀點言說的歷史,其間糾纏著高秋江在解放前后的神秘失蹤。此外,還有梁必達的“深不可測,波譎云詭”的靈魂世界的探究,張普景戲劇性的瘋狂以及瘋狂的界限的質疑。層層迷霧籠罩的歷史使讀者有著種種“霧里看花,水中望月”的迷惑,而這種種迷惑又更進一步加深了關于歷史的思考。
作家始終沒有給予“英雄”一個明確的定義。在顛覆了英雄神話與莊重風格之后作家揭示了一群人的精神成長歷程,他似乎已經以一種并不確定的方式確定地回答了歷史所提出的問題——人本身生存狀態的真實性。一位平面化的“高大全”僅僅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中構建的神,而絕非人;歷史因為神秘無法言說才是真實。面對歷史長河中的人與事我們可以給予一個公允的評價,但無法提出完全確定的標準。文本記錄一種人生,人生的反復無常注定了文本情節的悲喜交加,這也許就是《歷史的天空》能夠走得這么遠,同時獲得如此多的殊榮的真正原因。
通過《歷史的天空》,我們看到了以徐貴祥為代表的一批軍旅文學創作者堅定地守住這塊陣地,在放棄曾經的審美范式的同時,他們努力尋求將軍旅文學的政治優勢轉化為文學優勢的可能。沒有親歷過戰爭的他們思考著怎樣還原那段硝煙彌漫的歷史歲月,他們沒有放棄英雄,因為這個時代仍然需要英雄,希望英雄之路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