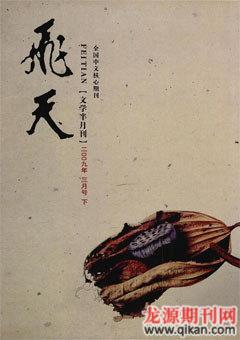視覺文化時代文學教育的反思
趙曉輝
視覺影像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正以強有力的勢態控制著我們的生活,這意味著—個更加追求官能愉悅的文化形態的生成,同時也意味著人們思維范式的一種轉換。處在視覺文化時代的文學教育,受到影視、互聯網等媒介的強勢影響,傳統的以紙媒為核心的教育方式受到了很大沖擊,由此而產生了文學詩意教育的危機。筆者旨在從視覺時代的文化癥候入手,結合平日的教學體驗,對在視覺文化氛圍之下的文學教育進行一些反思。
電子媒介突破了純粹技術的領域而以極強態勢進入到現代生活中來,在我們的生活中,它幾乎形成了—個顯而易見的文化權利中心。“目前居‘統治地位的是視覺觀念。聲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組織了美學,統帥了觀眾。”“在數字化媒體的強勢覆蓋下,‘讀圖勝于讀文,‘讀屏多于讀書,直觀遮蔽了沉思,快感沖擊美感,文化符號趨于圖像敘事已是不爭的事實。”在視覺文化主導的年代,文學必須通過電子傳媒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傳播,越來越多的公眾從影視傳媒的渠道來接受文學,甚至文學名著也要借助影視改編之東風才能熱銷。電視頻道里某些學術講座的火爆多多少少都帶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才能得到觀眾的追捧,很多人都是在接受了電視學術講演的引導后才去閱讀紙媒書籍的。視覺文化時代大眾奉行的是直觀、感性、具體的原則,“一切必須是當下的滿足,精神生活已變成了飄忽而過的快感。隨筆式的文章已成為合適的文學形式,報紙取代書籍,花樣翻新的讀物取代了伴隨生命歷程的著作。人們草草地閱讀,追求簡短的東西,但不是那種能引起反思的東西,而是那種快速告訴人們消息而又立刻被遺忘的東西。人們不再能真正地閱讀,并與他所讀的著作結成精神的同盟”。在這樣的時代語境當中。文學教育有如下一些現象值得注意:
首先,就教學方法而言,在今天的高校課堂上,多媒體教學的使用十分普遍。與傳統的教學模式相比,多媒體教學能有效地把文字、聲像等信息合并處理,將教學空間構建成具有較強互動性、可視性的教學情境。為適應新形態教學需要,多媒體教學網絡資源庫日益豐富,一批適于課堂教學的課件相繼被開發出來,對多媒體教學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就高等教育主導部門所倡導的教改來說,包括教育部啟動的精品課程建設中,十分強調現代教育技術和手段的使用。這具有強勁的導向作用。教學方式的多媒體化在這一評價體系中也越來越重要;另外,教材出版行業的競爭日趨激烈,與紙質教材配套的網上教學資源已成為各大教材出版社相互競爭的重要手段,一些教育出版社在努力實現教學資源的集成轉變,在紙質教材基礎上還爭相配有大量圖文音像資料的教輔及名師示范光盤。其中也出現了一些值得反思的現象:在教學中部分教師過度倚重多媒體教學,一定程度上存在“照屏宣科”的現象。在教學中,一旦課件播放出現問題,便會影響教學效果。教師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制作和設計多媒體課件上。在課件中穿插大量圖像、聲效等,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教學內容,忽視了文學教育最根本的審美感發作用。加上多媒體教學課件極易傳播復制,文學這種十分注重詩意啟蒙的教育活動在一定程度上變得多多少少有點程式化、刻板化。
其次,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日新月異的視覺傳播技術使得學生對文學的視覺訴求越發強烈,而對文學所應有的深度理性思考和審美感發等方面較淡漠。在課堂上教師若對某一文學作品進行較為學理化的闡釋,勢必會有部分學生覺得索然無趣,假如適當地添加一些文學作品改編的影像或圖片資料,學生們則會興味盎然。聯系當今文化市場不難發現,出版物中圖像化的傾向愈加顯著,越來越多的插圖讀物受到歡迎,單純的文字使人缺乏興趣,“看”比“讀”更簡單也更饒有趣味。由此可見,視覺文化時代的電子媒介往往對我們施加了無法逃避的隱性暴力,學生往往在沒有細讀文本,由此而產生一己之興發感動的情況下就已經被施加了先入為主的視覺信息,這樣對于文學的接受,多少都會帶有被動和盲目的色彩。
當然,以上所論并非對視覺文化時代的電子媒介抱有偏見,相反地,如果加以適當引導和利用,電子媒介也會給文學教育帶來新的契機。在視覺文化的語境下,我們在文學的教育中要繼續倡導文學的詩意教育,這意味著如下幾方面的努力。
首先,在授課方式上,要注意多媒體教學軟件的適當使用。須知,在文學教學中,教師以富有魅力和情趣的講解,傳達文學作品中生生不息的審美感發作用,引導學生體會人類精神的詩化,從而調動學生對于文學的興趣,最終獲得一種精神的感染和超越,這是教學之本,乃是任何形式的電子媒介都不能替代的。因此,多媒體的使用既不宜過于沉寂,也不應該喧賓奪主。使用多媒體,應視具體的教學情況而定。教師在制作課件時,不應以畫面、視頻等視覺性元素為主,在學生的視覺素養、審美能力還未得到充分提升的情況下,過度使用這種視覺性資源必然導致知識的娛樂化、淺易化,使“形象性感知”代替了以反思沉吟為主的“話語性認知”,也終將背離文學教育的終極目標腳。
其次,在課堂教育方面,要有意識地廓清電子媒介的不良影響,重視品味涵詠,以富含詩意的方式傳達文學作品“興發感動”之本質。由于視覺文化時代的很多信息資源是開放的,電子檢索與傳播也極為方便。由此而帶來的弊端是對于文學作品的闡釋存在極為嚴重的模式化傾向。這樣的解說,始終未能將作品“興發感動”的特質傳達出來,枯燥無味,連自己都不能感動,遑論學生了。葉嘉瑩先生認為:“說詩者之責任,卻原不僅在于能感受,而更在于能夠予以論釋和說明。如此,則在詩歌中所蘊涵和表現的這些‘能感之‘能寫之的種種因素,自然便是他所賴以分析和說明的主要憑藉。所以如果不能探觸到詩歌中真正生命之所在,不能分辨其‘境界之有無、深淺,對一首詩歌的好壞以及有無評說之價值都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這樣當然無法成為一位優秀的說詩人;然而如果在探觸感受到詩歌中這種生命力之后,而無法對之做精密的分析和說明,當然也同樣無法成為一位優秀的說詩人。”不僅說詩者如此,在教育中作為文學闡釋的主導者,對于文學作品所描摹的自然之景乃至宇宙萬物應有一種“情動于中”的關懷之情,并能詩意地傳達作品所蘊含的興發感動之生命。
再次,在學生的閱讀方式上,應積極倡導返回紙媒的閱讀習慣。現在高校學生的學習已經相對個性化、自由化,可惜他們讀書的時間反而減少了,相應地看影視、上網卻占據了大量時間。因此,有意識地倡導返回紙媒的閱讀,尋求詩意豐盈的個人化閱讀體驗,彰顯文本和讀者之間豐富多樣的藝術張力,乃是十分重要的舉措。誠如王一川先生所云:“要想抵制或跨越文學作品被電子媒介娛樂化的命運,就需要重新回到文學文本的語言閱讀中,因為只有在這種嚴肅的語言閱讀中,我們才有可能真正洞悉詩的聲音和世界,從而驅散種種媒體的娛樂化迷霧,而把自己的人生重新照亮。”
總之,以上所論并非對視覺時代的電子媒介懷有警戒與敵意,而是倡導在這樣的視覺語境之下,以積極冷靜的態度去審視當前文學乃至文學教育的癥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