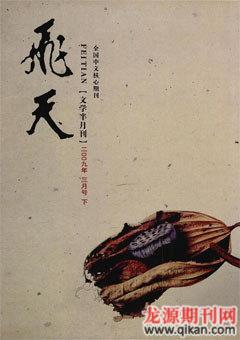淺論杜甫蜀中詩歌之反封建迷信
赫蘭國
作為我國封建社會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杜甫以其詩歌的現實性、人民性等優秀特征為歷來論詩者及讀詩者所贊許。其實,在其詩歌中與現實性、人民性共存的優點還有反迷信性一條。下面,本人僅以杜甫在蜀中時創作的《石筍行》、《石犀行》、《杜鵑行》為例,分析杜甫詩歌的反封建迷信思想。
大家知道,整個中國封建社會中,神話傳說、迷信怪誕之說流傳不絕,上自帝王,下到庶民大都篤信之而不疑,故而在歷代許多文人墨客的詩文中都不乏“怪力亂神”;特別是唐代,佛道并熾,李氏王朝兼收并蓄之,朝野上下信徒實藩。李白即是一個貨真價實的道士,成仙飛升等虛妄的說法李白都深信不疑。
杜甫生活在這么一個大的環境中,卻能始終保持清醒睿智的頭腦,抱有一種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甚或是無神論觀點,更顯其難能可貴。先觀其《石筍行》:“君不見益州城西……使人不疑見本根。”
《成都記》云:“距石筍二三尺,每夏六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測之,深不可及。以繩系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無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佑春,牛車碾地,忽陷,亦測而不能達。父老甚異,故有海眼之說。”《風俗記》載:“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筍焉,天地之堆,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濫。”
石筍因年代久遠,形狀奇特,被世人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不少人穿鑿附會,以為是鎮水神之物;杜甫對石筍“古來相傳是海眼”,海眼動就要洪水泛濫迷信的說法并不認同:“此事恍惚難明論。”他認為“恐是昔時卿相冢,立石為表今仍存”。可貴的是杜甫不僅破除了迷信,更重要的是他還發出了以下感嘆:“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忤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杜甫由世俗為石筍的傳說所蒙蔽,進一步聯想到皇帝為“小臣”所蒙蔽,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錯亂、國家傾危的惡果。顯然這是針對玄宗、肅宗兩朝政治之腐敗、小人當道而發的。
當代許多學者都非常贊許杜甫的觀點。如童恩正先生指出,詩人尖銳地駁斥了迷信的傳說,希望有壯士將它擲之天外,以免人民再受蒙蔽,這是有進步意義的。特別是早在一千多年以前,他就提出了這可能是古代墓葬的遺跡,更是難能可貴。董其祥先生認為:“杜甫不愧為現實主義的大詩人,對于這樣的歷史文物,不是以訛傳訛,任意猜測,謬種流傳,貽誤后世,而是親自調查研究,核對文獻記載,作出比較正確的判斷。”
陸游入蜀后,曾實地考察過成都石筍,其《老學庵筆記》卷五道:“成都石筍,其狀與筍不類,乃壘疊數石成之。所謂‘海眼,亦非妄;瑟瑟,至今有得之者。”要么陸游所見石筍并非與杜甫所見石筍是同一處,要么就是陸游的識見反不如早他數百年的杜甫,這更反襯出杜甫的過人之處。
再看其《石犀行》(見《杜詩詳注》卷十,詩句不錄),《杜詩通》云:“先王作法無非正道,如眾力提防,出于人謀者是也。厭勝乃詭道,何得參與?故此三犀無關經濟,如此訛言,只合與長川俱逝而已。若論經濟,必須賢相,方能調和元氣,自免波濤以恣凋瘵,何難藉人謀以平水土?而石犀奔茫,無能惑人矣。‘壯士提天綱,正謂賢相操國柄也。日‘安得,傷時無賢相也。”此可謂深得杜甫本心者也。
《華陽國志》記載,李冰曾作五頭犀牛來壓水精,防水患。杜甫對這一迷信說法也是不相信的。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秋天,灌縣發生水災,杜甫借此幽默地嘲笑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為神羞。”石犀不是可以壓水精嗎?為什么還出現水災了呢?石犀這個神物不應感到羞恥嗎?杜甫認為要戰勝水災,必須“終藉提防出眾力”,而“詭怪何得參人謀”?“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他這種不信“詭怪”,只信“人謀”和“眾力”的思想是遠遠高出同時代的人的。
最后閱讀《杜鵑行》:“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鳥?……萬事翻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群臣趨。”
此詩杜甫也非就事論事,他并不相信望帝化鵑的傳說,只是借此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而已。《杜臆》云:“‘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寂孤,骨肉滿眼,身實寂孤,其意可思。余謂味此二句,則此詩真為玄宗而作。楊妃死,高力士逐,雖千人侍側,猶孤居也。此情歲千言說不出,而七字說透,何等筆力!然通篇實賦杜鵑。‘常區區、‘傷形愚,哀其有情而不能達也。‘蒼天變化二句,讀之毛骨俱悚,不止詠杜鵑矣。”《杜詩通》曰:“此詩興也,蓋論人事之無常耳。大意只在末二句,所以喻世人富貴不足侍也。舊謂比明皇居西內,然‘羞帶羽翮傷形愚,豈所以論君上哉?”這里關于詩之所指向提出了兩種不同的觀點,我還是傾向于第一種觀點的;但無論哪一種觀點,都明確表示此詩的用意絕非在寫、在宣傳神話傳說。
杜甫的反迷信的思想可以說貫穿于他詩歌創作的始終,即使是青年時期創作的賦亦是如此。在《朝獻太清官賦》和《有事于南郊賦》中都表達了他對玄宗淫祀老莊的落后行為的不滿和批判。仇兆鰲云:“當時尊奉道祖,帝號崇祀,本屬不經。此賦(《朝獻太清官賦》)前言戡亂致治,而不及神仙杳冥之事;后言厘正祀典,而不及符應報錫之文……諷喻隱然……”
杜甫在一千多年前的落后的封建社會里,在“舉世皆昏”的時代而能保持如此清醒的頭腦是不無原因的,首先他是一個十足的儒者,繼承了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優良傳統;其次他一輩子窮愁潦倒,顛沛流離,生活在社會地層,與村氓庶民為伍作友,有時還親自耕作、覓食,對社會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故而成就了他超時代的、高于同時期同仁的認識水平。
杜甫詩歌“光焰萬丈長”,優點良多,特拈出此點,恰當與否待具法眼者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