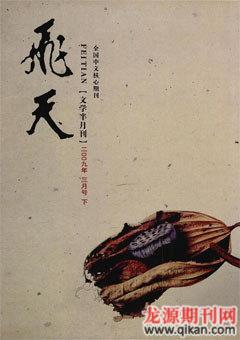土耳其:身份的焦慮
薛育赟
2005年,帕慕克因他的新作《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回憶》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提名。2006年10月12日,帕慕克榮膺巨獎(jiǎng),授獎(jiǎng)理由是“在探索其生身故鄉(xiāng)伊斯坦布爾憂郁的靈魂的過(guò)程中發(fā)現(xiàn)了文化間的沖突和多樣性的新象征”。《雪》是一部為帕慕克贏得巨大聲譽(yù)同時(shí)又給他帶來(lái)不少麻煩的書(shū)。這本書(shū)出版之后,土耳其舉行了燒書(shū)活動(dòng),不同的舉辦者焚燒《雪》的不同部分。這本書(shū)所引發(fā)的政教爭(zhēng)議令帕慕克遭到一些同胞的憎恨,甚至受到生命威脅,他成了一個(gè)被獵捕的人,幾乎不能在自己的國(guó)家安全地散步。一本書(shū)為什么能引起這么大的爭(zhēng)議,這得從土耳其和伊斯坦布爾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說(shuō)起。
一、伊斯坦布爾的歷史:沖突與融合
要理解帕慕克其人和他的作品《雪》,就必須了解伊斯坦布爾。帕慕克幾乎從未離開(kāi)過(guò)伊斯坦布爾,除了陪妻子在美國(guó)呆了一段時(shí)間外。伊斯坦布爾不僅是他的故鄉(xiāng),也是他創(chuàng)作素材和靈感的來(lái)源之地。雖然共和國(guó)建立后政府將首都遷到安卡拉,但這個(gè)有1700年帝國(guó)都市史的大城,依然是土耳其人民心中的精神之都。這個(gè)橫跨歐亞大陸的城市是了解土耳其的最好的窗口。
公元前660年,首先是古希臘^在此住,伊斯坦布爾是古希臘人在歐洲的最東端開(kāi)辟的前哨。這座古希臘的城池就根據(jù)領(lǐng)袖拜薩斯的名字命名為:拜占庭(Byzantium)。此后,拜占庭由波斯人、雅典人、斯巴達(dá)人,以及亞歷山大大帝統(tǒng)領(lǐng)過(guò)。直到公元193年被勢(shì)力強(qiáng)大的羅馬皇帝瑟提米斯·塞佛魯斯(septimiusSeverus)攻克,惡戰(zhàn)中全城盡毀,羅馬人以他們的方式將城市重建。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306-337)將首都從羅馬遷到拜占庭,而且開(kāi)始推崇基督教,將拜占庭改為新羅馬。他去世后,為了紀(jì)念他,改稱君士坦丁堡。13世紀(jì),威尼斯總督帶領(lǐng)的十字軍騎士攻破了此城。從公元1096到1296年的整整兩百年間,是歷史上所謂的“十字軍時(shí)代”,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矛盾,終于因?yàn)榍昂蟀舜蔚氖周姈|征而激化到無(wú)以復(fù)加的地步。
15世紀(jì),土爾其族的奧斯曼大軍從海峽那邊的大陸席卷而來(lái),并給了它新的名字:伊斯坦布爾。從此,原本的君士坦丁堡就改名為伊斯坦布爾。他們也將高度文明的伊斯蘭藝術(shù)根植到此處,這些信奉伊斯蘭教的征服者對(duì)圣索菲亞大教堂(Aya Sophia)作了一些改動(dòng),以符合他們的宗教觀,但并沒(méi)有破壞和移走原物,甚至還保留了圣母小圣壇。他們將教堂內(nèi)部金光燦燦的拜占庭壁畫(huà)用水泥覆蓋起來(lái),取而代之的是伊斯蘭藝術(shù)引以為豪的華麗紋飾。九百年的基督教堂從此變成了清真寺。
1923年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國(guó)將首都遷到安卡拉。新一代的政治家采取了跟奧斯曼王朝一刀兩斷的態(tài)度,徹底否定過(guò)去。對(duì)伊斯蘭教也采取政教分離,盡量淡化伊斯蘭教對(duì)社會(huì)生活的影響,把它處理為純粹私人生活的一部分。土耳其現(xiàn)代國(guó)父穆斯塔法·基馬爾·阿塔圖爾克(在國(guó)內(nèi)常譯作凱末兒)倡導(dǎo)西方的生活方式,主張歐化,普及西方教育,他認(rèn)為土耳其應(yīng)該重新變?yōu)闅W洲的一部分。在此政策的影響下,伊斯坦布爾的貝尤魯新城區(qū)逐漸歐化。從西方歸來(lái)的土耳其精英分子都在柏林或維也納受過(guò)教育,生活習(xí)慣已歐化,并用他們的在社會(huì)上的影響力去潛移默化其他的土耳其人。尤其那些富裕的家庭已基本不信仰伊斯蘭教,過(guò)著世俗的生活。但到20世紀(jì)50、60年代,隨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在全世界范圍的興起,土耳其社會(huì)的方向又慢慢回到了原本根深蒂固的伊斯蘭教傳統(tǒng)上,對(duì)奧斯曼時(shí)代的文化也有了重新的評(píng)價(jià)。對(duì)這種情況帕慕克如是說(shuō):“伊斯坦布爾在地理上是一個(gè)混合之地,土耳其也是。百分之六十的人保守,百分之四十的人尋求西化。兩股力量爭(zhēng)論了不下二百年。這種處于東方、西方的懸置狀態(tài),就是土耳其的生活風(fēng)貌。”
二、卡爾斯的努力:政變與掙扎
帕慕克的小說(shuō)《雪》描寫(xiě)的故事發(fā)生在20世紀(jì)90年代的土耳其東部邊境城市卡爾斯,主人公卡(Ka)是一個(gè)旅居德國(guó)法蘭克福的土耳其詩(shī)人。12年后為了母親的葬禮,他重歸伊斯坦布爾。在伊斯坦布爾《共和國(guó)報(bào)》報(bào)社里與年輕時(shí)的朋友相遇,朋友向卡建議,如果想看看12年來(lái)真正的土耳其,最好是去卡爾斯,在卡爾斯年輕女子患上了奇怪的自殺癥,并且這個(gè)城市即將舉行選舉。另外美麗異常的的大學(xué)同學(xué)伊珮珂也在卡爾斯。伊驪珂一直是卡傾慕的對(duì)象,同時(shí)他認(rèn)為她就是他要找的幸福。卡為了遙遠(yuǎn)而虛無(wú)的幸福踏上了去卡爾斯的路。
當(dāng)他到達(dá)卡爾斯后,大雪便封閉了這座城市。卡和伊佩珂在新人生糕餅店初次約會(huì)時(shí),就親眼目睹了那位禁止戴頭巾的女學(xué)生上學(xué)的校長(zhǎng)被槍殺,這宗槍殺案莫名其妙地讓卡卷入了卡爾斯的政治沖突的旋渦之中。在卡爾斯,女學(xué)生如果戴頭巾去學(xué)校上課,主張西化和世俗化的政府就認(rèn)為是伊斯蘭教對(duì)他們的挑戰(zhàn)。所以,那些戴頭巾的女學(xué)生一直被保安堵在學(xué)校外面,徘徊在校門(mén)口,在卡爾斯的寒冷天氣中慢慢變得絕望,最后一個(gè)個(gè)自殺。這種情況被宗教分子們加以利用,他們認(rèn)為女學(xué)生戴頭巾是遵從安拉的意志,禁止戴頭巾的女學(xué)生上學(xué)就是對(duì)安拉的不敬。所以宗教分子槍殺教育學(xué)院院長(zhǎng)時(shí)問(wèn)他:你對(duì)《古蘭經(jīng)》的“奴爾”一章第三十一節(jié)是怎么看的?院長(zhǎng)回答說(shuō)這一節(jié)中非常明確地指出,女人們應(yīng)該遮住頭部,甚至臉部。
第二天,在卡爾斯的劇院里上演了一場(chǎng)政變,政變是和一場(chǎng)名叫“祖國(guó)還是頭巾”的戲劇節(jié)目同時(shí)進(jìn)行的。舞臺(tái)上—個(gè)穿著黑袍的神秘女人來(lái)來(lái)回回決絕地行走著,因?yàn)橛X(jué)醒和對(duì)自由的追求,穿黑袍的女人要脫去黑袍,并將它放在了舞臺(tái)上的一個(gè)銅盆里,將汽油倒在上面搓洗起來(lái)。稍后,她掏出打火機(jī)將黑袍點(diǎn)著。這個(gè)行為激怒了站在劇院后排的宗教學(xué)校的學(xué)生們。宗教學(xué)校的學(xué)生們先是一片嘩然,接著像炸了鍋,噓聲、喊叫聲、怒吼聲響成一片。“不信安拉的宗教敵人!”有人喊道,“沒(méi)有信仰的無(wú)神論者!”此時(shí),女主角繼續(xù)在舞臺(tái)上解釋姑娘為什么扔掉了黑袍子,她說(shuō),不僅是個(gè)人,整個(gè)民族的寶貴品質(zhì)不在于衣著而在于靈魂,現(xiàn)在我們應(yīng)該從這些使我們靈魂受到玷污及落后的標(biāo)志——黑袍、頭巾、贊斯帽和纏頭中解放出來(lái),奔向文明和現(xiàn)代的民族,奔向歐洲。這時(shí),有人跳到舞臺(tái)上大喊道:“共和國(guó)萬(wàn)歲!”“軍隊(duì)萬(wàn)歲!土耳其萬(wàn)歲!阿塔圖爾克萬(wàn)歲!”“讓宗教狂們見(jiàn)鬼去吧!”
正在大家亂成一團(tuán)時(shí),從幕布兩邊各出現(xiàn)了一名士兵,又從后門(mén)進(jìn)來(lái)了三個(gè)士兵,上到舞臺(tái)上對(duì)準(zhǔn)觀眾連續(xù)開(kāi)了幾槍,幾人應(yīng)聲倒地。稍后,一輛坦克和兩輛軍車襲擊了宗教學(xué)校的宿舍,并拘捕了所有的學(xué)生,同時(shí)又拘捕了獸醫(yī)學(xué)校的學(xué)生。卡爾斯的庫(kù)爾德人也受到襲擊、拘捕、殺害。
20世紀(jì)80年代開(kāi)始,傾向西方的土耳其精英在外交政策上的一個(gè)主要目標(biāo),就是獲得歐盟成員國(guó)的資格。其實(shí),在20世紀(jì)20年代土耳其就為這一目標(biāo)而努力了。土耳其共和國(guó)剛一建立,凱末兒
就精心策劃了一系列改革:廢黜了蘇丹,建立西方式的政治模式:共和政體;廢除了哈里發(fā)的職位,哈里發(fā)是宗教權(quán)威的主要來(lái)源;廢除獨(dú)立的宗教學(xué)校及學(xué)院,建立了統(tǒng)一的世俗公共教育制度;中止了采用伊斯蘭法律的宗教法院,代之建立以瑞士民法為基礎(chǔ)的新的法律制度;用公歷代替了傳統(tǒng)的歷法,并正式廢止了伊斯蘭教的國(guó)教地位;禁止人們戴土耳其帽,因?yàn)樗亲诮虃鹘y(tǒng)的象征;凱末兒也拋棄了多民族帝國(guó)的思想,目的是建立一個(gè)同質(zhì)的民族國(guó)家,在這一過(guò)程中亞美尼亞人與希臘人遭到了驅(qū)逐與屠殺。30年代,凱末兒重新確立了土耳其人民民族的、政治的、宗教的和文化的認(rèn)同之后,積極促進(jìn)土耳其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西方化與現(xiàn)代化攜手并進(jìn),并預(yù)定將成為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工具。所有的這些就成為以后的阿塔圖爾克主義者們所遵循的教條。這種極端、激烈的現(xiàn)代化方式并沒(méi)有持續(xù)太長(zhǎng)時(shí)間,也沒(méi)有給土耳其帶來(lái)他們想要的現(xiàn)代化。
1987年4月,土耳其正式提出申請(qǐng)加入歐盟。在隨后的幾年里好幾個(gè)國(guó)家順利加入了歐盟,對(duì)土耳其卻是一拖再拖。在公共場(chǎng)合,歐盟官員指出這是因?yàn)橥炼涞慕?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低,不如歐洲國(guó)家尊重人權(quán)。私下里,歐洲人和土耳其人都明白,真正的理由是,土耳其是一個(gè)穆斯林國(guó)家。歐盟是一個(gè)基督教徒的俱樂(lè)部,而土耳其卻太穆斯林化,文化上與歐洲太不相同,太格格不入。多年的愿望得不到歐洲的重視,反而一再遭到忽視,土耳其人意識(shí)到:在歐洲,其實(shí)是沒(méi)有土耳其的一席之地的。“歐洲對(duì)于土耳其來(lái)說(shuō)是一個(gè)非常敏感脆弱的話題。我們站在門(mén)口,充滿希望和善意卻忐忑不安地敲打著你們的大門(mén),期待著你們能批準(zhǔn)我們加入。我和其他土耳其人一樣懷著熱切的希望,但是我們都有種‘沉默的恥辱感。土耳其敲打著歐洲的大門(mén),我們等了又等,歐洲向我們?cè)S愿后又忘記了我們。”
20世紀(jì)后期,原教旨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興起,又因?yàn)橥炼浼尤霘W盟一再受挫,所有的這些都刺激了國(guó)內(nèi)的伊斯蘭情緒,主流輿論和實(shí)踐越來(lái)越伊斯蘭化。到90年代,留伊斯蘭式胡須的男人和戴面紗的婦女激增,清真寺吸引了更多的人。先知穆罕默德的價(jià)值觀得到越來(lái)越多的人的吹捧。伊斯蘭歷史、戒律和生活方式得以廣泛頌揚(yáng)。在這種情況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土耳其得以發(fā)展壯大,并得到政府的默許和支持。在阿塔圖爾克禁止戴土耳其帽的70年后,土耳其政府實(shí)際上允許了女學(xué)生戴傳統(tǒng)的伊斯蘭頭巾上學(xué)。土耳其的伊斯蘭復(fù)興運(yùn)動(dòng)在公眾中激起了反西方的情緒,并開(kāi)始影響土耳其精英的世俗的、親西方的傾向。
《雪》的主人公卡出生在伊斯坦布爾的一個(gè)中產(chǎn)階級(jí)家庭,并且他本人又在西方生活了12年,深受西方影響。就是這樣一個(gè)堅(jiān)持世俗生活的精英,當(dāng)他回到土耳其,他以前所堅(jiān)持的無(wú)神論很快被瓦解,開(kāi)始懷疑自己的身份,并逐漸向伊斯蘭教靠攏。以下卡和卡爾斯教長(zhǎng)薩德亭在見(jiàn)面時(shí)說(shuō)的三段話,就明晰地紀(jì)錄了卡的這種變化。
“我在伊斯坦布爾的尼尚坦石的上流社會(huì)中長(zhǎng)大。我一直想像歐洲人一樣。我認(rèn)為信仰讓婦女們穿著袍子蒙著臉的安拉和成為一個(gè)歐洲人是無(wú)法同時(shí)讓人接受的,所以我一直遠(yuǎn)離宗教。到歐洲以后我覺(jué)得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安拉存在,不是那些蓄著胡須、保守落后的邊遠(yuǎn)地區(qū)的人所說(shuō)的那種。”
“我也想像你們一樣相信你們的安拉,做一個(gè)普通公民,可是因?yàn)槲倚哪恐袣W洲人的形象,我有些弄不清除了。”
卡個(gè)人的這種迅疾的、無(wú)奈的變化也是土耳其這個(gè)國(guó)家的尷尬與無(wú)奈。20世紀(jì)上半葉凱末兒主義不僅在土耳其大行其道,獲得絕對(duì)的主導(dǎo)地位,而且在整個(gè)東方也流行激蕩,但不管人類怎樣牽強(qiáng)地將歷史試圖放置于自己編織好的軌道,最終,它仍會(huì)回到自己的路線運(yùn)行。土耳其伊斯蘭教的復(fù)興,蘇聯(lián)的解體和中國(guó)近年來(lái)國(guó)學(xué)所受到的推崇,都說(shuō)明了這一點(diǎn)。卡從過(guò)去一個(gè)堅(jiān)定的世俗主義者、無(wú)神論者,轉(zhuǎn)變成現(xiàn)在的一個(gè)對(duì)安拉和教長(zhǎng)畢恭畢敬的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人類的單個(gè)個(gè)體是無(wú)法抵抗環(huán)境與歷史潮流的。
三、土耳其所需要的:勇氣與智慧
卡來(lái)卡爾斯的主要目的就是找到伊珮珂,將她帶到法蘭克福一起幸福地生活。卡到卡爾斯后很快和伊驪珂見(jiàn)面了,經(jīng)過(guò)卡的一番努力,伊驪珂答應(yīng)與卡一起到法蘭克福。后來(lái)卡卻意外地得知,伊驪珂和前夫穆赫塔爾離婚后,一直做神藍(lán)的秘密情人。神藍(lán)是一個(gè)狂熱的伊斯蘭宗教分子,涉嫌兩宗謀殺案。現(xiàn)在不知什么原因也來(lái)到了卡爾斯。卡深知,伊驪珂之所以要跟他離開(kāi)卡爾斯并不是因?yàn)閻?ài)他,而是要借他來(lái)忘記神藍(lán)。卡經(jīng)過(guò)痛苦的思考后還是決定帶伊驪珂去法蘭克福。可是,在卡準(zhǔn)備離開(kāi)卡爾斯時(shí),神藍(lán)被軍方殺死,伊驪珂認(rèn)為這是卡向軍方告密的結(jié)果。于是,伊佩珂拒絕了卡帶她走的請(qǐng)求,留在了卡爾斯,卡一個(gè)人孤獨(dú)地離開(kāi)。四年后,卡在法蘭克福遭到殺害。卡,一個(gè)要求民主與人權(quán)的知識(shí)分子,居然為了所謂的幸福,毫無(wú)原則地與軍方合作。卡和軍方的唯一相同之處即兩者都是阿塔圖爾克主義者,但正因此軍方曾經(jīng)將他驅(qū)逐出了土耳其。其實(shí),卡的悲劇是我們每一個(gè)人的悲劇。當(dāng)無(wú)論是宗教還是政府的力量變得霸道到足以危險(xiǎn)個(gè)體的生命時(shí),個(gè)體的選擇已變得身不由己、無(wú)足輕重、無(wú)關(guān)緊要了。這時(shí)的宗教與政府已遠(yuǎn)離它的本質(zhì),異化為壓迫、規(guī)訓(xùn)個(gè)體的東西了。本來(lái),宗教在本質(zhì)上是為了讓人們擺脫現(xiàn)世的苦難與無(wú)望,給人以彼岸的希望與救贖的。
帕慕克在他的作品中致力于探討土耳其的世俗主義者與伊斯蘭教主義者、西化與奧斯曼傳統(tǒng)之間的關(guān)系。在他的小說(shuō)《新人生》中就以反諷的方式審視東西方之間的差距。1985年出版的歷史小說(shuō)《白色城堡》講述了一個(gè)來(lái)自威尼斯的奴隸被土耳其軍隊(duì)俘虜?shù)揭了固共紶枺恢焙鸵粋€(gè)跟他長(zhǎng)得相像的土耳其學(xué)者住在一起。在此期間,他們向?qū)Ψ街v述自己的生命歷程和生活習(xí)慣,時(shí)間久了,他們慢慢變得比對(duì)方更了解自己。他們通過(guò)共同的努力為一位帕夏成功制作了慶典用的煙火,并共同制止了一場(chǎng)流行于伊斯坦布爾的瘟疫。最后他們互變身份,土耳其學(xué)者去了威尼斯,在那兒過(guò)著舒適的生活,而留在土耳其的威尼斯奴隸過(guò)上了原來(lái)土耳其學(xué)者的生活,波瀾不驚。帕慕克通過(guò)這兩個(g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的成功的身份互換,說(shuō)明了東西方是可以互相借鑒,共同發(fā)展的。
伊斯坦布爾那座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大橋,連接著兩個(gè)大陸、兩種文明,在伊斯坦布爾的圣索菲亞大教堂里的圣母像和伊斯蘭教的紋飾也和諧共存了幾百年。作為人類共同的東西方的相似應(yīng)該多于不同,我們應(yīng)該更多看到和諧而不是分歧。五百多年前,穆罕默德二世攻陷了君士坦丁堡,面對(duì)圣索菲亞大教堂,這基督教的經(jīng)典建筑,他既沒(méi)有焚燒也沒(méi)有毀壞,而是給予足夠的寬容與保留。在某些方面他就是今天土耳其人的榜樣。東方和西方、伊斯蘭教與基督教是否可以和諧共存,就看當(dāng)代的土耳其人有沒(méi)有先賢穆罕默德二世那樣的智慧與勇氣了。
其實(shí),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也是在不斷的尋求和改進(jìn)中得以發(fā)展壯大并取得了今天在世界上的強(qiáng)勢(shì)地位。在15、16世紀(jì),馬丁·路德、約翰·加爾文兩人對(duì)基督教進(jìn)行了大膽而又創(chuàng)新的改革,使基督教更加適應(yīng)當(dāng)時(shí)資本主義初期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促進(jìn)了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發(fā)展。法國(guó)歷史學(xué)家費(fèi)爾南·布羅代爾說(shuō)過(guò):“正如—個(gè)文明可以歡迎或排斥來(lái)自其他文明的成分一樣,它也可以接納或拒絕它自己歷史的殘存物。這一選擇過(guò)程并不緩慢,而幾乎總是無(wú)意識(shí)地或部分地進(jìn)行。但多虧這樣,一個(gè)文明通過(guò)‘分割出其古有的一部分,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改變著自己。”“在遙遠(yuǎn)的或晚近的過(guò)去所提供的大量資料和見(jiàn)解中,他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加以篩選,看重一些東西而忽略另一些東西;作為這種選擇的結(jié)果,它具備了一種既非全新也絕非與過(guò)去完全相同的形態(tài)。”
最后,正如帕慕克在接受采訪時(shí)所說(shuō):“在我國(guó),最為緊迫的首先是最大限度地強(qiáng)化民主觀念,構(gòu)建一個(gè)愈來(lái)愈公開(kāi)和多樣的社會(huì)。”有了民主,就可以讓大多數(shù)人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一個(gè)公開(kāi)的社會(huì)能將更多的民主讓更多的人分享。有利于一個(gè)多樣性社會(huì)的建立。多樣性社會(huì)的建立,則可以包容不同的宗教和文化,留給它們屬于自己的領(lǐng)地。有人問(wèn)帕慕克,你相信土耳其東西方的沖力之間恒久的對(duì)抗會(huì)和平地得以解決嗎?帕慕克如是回答:“我是一個(gè)樂(lè)觀主義者。土耳其不應(yīng)該為擁有分屬于兩種不同文化的兩種精神、擁有兩種靈魂而感到焦慮。精神分裂癥會(huì)使你變得更聰明。”“如果對(duì)你的一部分過(guò)分擔(dān)憂,你就會(huì)扼殺掉你的另一部分,你會(huì)最終只剩下單一的精神世界——這比有這種疾病更為糟糕。這是我的理論。我試圖在土耳其的政治上,在土耳其要求國(guó)家應(yīng)該有始終如一的精神的那些政治家們中間傳播這個(gè)觀點(diǎn)——他們認(rèn)為始終如一的精神或者應(yīng)該屬于東方或西方。或者是民族主義的。我對(duì)那種一元論的觀點(diǎn)持批判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