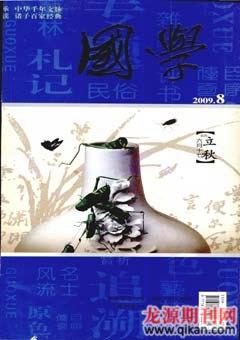儒家知識分子從后臺到前臺
資中筠
壹
秦朝泗水郡的一個小小的亭長,提了三尺劍,斬蛇起義,幾年殺伐下來,竟然取得天下。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傳奇。幾年前,在秦都咸陽,劉邦有幸親眼觀看始皇帝出行的盛況,那一派不可一世的天子氣象,直將這個小小的泗水亭長震懾得暈頭轉向。不知所措中,年輕的亭長唯有發出“大丈夫當如此”的感慨。劉邦心里當然明白,那不過是愛開玩笑的自己隨口說出的一句玩笑話。而今,笑話變成了現實,布衣真的做成了皇帝。除了相信命,劉邦還能相信什么呢?
布衣真的做成了皇帝,劉三也改了大號曰劉邦。這個傳奇不僅僅是劉邦的傳奇,更是中國歷史的傳奇。封建貴族的政治在暴力革命中煙消云散,在劉邦這里,歷史似乎是輕松地拐了個彎,步入一個平民政治的新時代。
在史書的記載里,這個泗水亭長乃是一個活脫脫的無賴平民:豁達大度并且還有一分鄉下人的幽默,不事生產并且喜好美酒和美女,還有,與人說話滿口臟字并且動輒罵娘。劉邦的朝廷班底,也大多是清一色的平民:周勃織草席為生,間或也在辦喪事的隊伍里吹吹簫;灌嬰走村串戶,販帛糊口;婁敬為人挽車;樊噲則更絕,乃是一殺狗的屠夫;申屠嘉為步卒;蕭何、曹參不過是刀筆之吏。其他如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也都是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
史學家把劉邦朝廷的這種情形名之曰“布衣將相之局”,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平民政府”。平民自有平民的好處,這個新興的階級一窮二白,如同一張白紙,正可以無所顧忌并且生氣勃勃地開辟新局。事實也正是如此,這群平民的崛起,其勢如暴風驟雨,所到之處,摧枯拉朽,莫可阻擋。秦帝國瓦解了,六國貴族及其后裔則風流散盡,便是那喚作“西楚霸王”的楚國貴族,也身死國滅,為天下笑。
但是,平民也有平民的致命缺陷。他們缺少知識,基本上沒有什么文化,這必然妨害他們的頭腦和眼光。許多時候,他們會執著于眼前的實利,陶醉于既得的享受,一時的得勝,甚至會讓這幫人歡喜得不思進取。一種宏遠的眼光與深邃的思想,在劉邦集團那里,無論如何是不具備的。
貳
更加致命的是,這個缺少知識和文化的集團,分明對于知識和文化有著一種本能的鄙視乃至仇恨。陳留高陽人酈食其,著了儒衣和儒冠來見劉邦,劉邦不見,還讓使者傳話說:“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素有“狂生”之名的酈食其只好氣急敗壞地高呼:“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儒士一變為頗具流氓氣息的“壯士”,劉邦這才破例一見。
天下平定了,劉邦仍舊不能意識到知識和文化的力量。楚人陸賈是頗具縱橫之才的儒生,以賓客身份侍從劉邦,成為沛公幕府難得一見的文化人,但劉邦欣賞的也僅僅是陸賈的口辯才華,常派遣他憑三寸不爛之舌游說諸侯。征戰天下或許可以單以力勝,治理天下卻需要文化的力量。陸賈識時務,曉權變,昔日他能忍受劉邦的無知,現在再也不能忍受了,他要為這個質樸少文的軍功集團做些文化啟蒙的工作。史載,陸賈時時在而今的高皇帝面前談論《詩》、《書》,每一次談論,劉邦都十分反感,有一次甚至還惹起劉邦的一頓臭罵:“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只是此時的陸賈不再含糊,他回敬道:“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接著又苦口婆心地講述了逆取順守文武并用的治國之道,這一次,劉邦居然被打動了,陸賈也就趁勢開始為大漢帝國擘畫文化藍圖。
叔孫通也是沛公幕府難得一見的文化人。他是魯國的儒生,秦時即待詔博士。較之陸賈,叔孫通更通曉時變,也更善于與時俱進,秦盛事秦,秦亡事楚,楚亡事漢,這一切他做起來都如魚得水。漢王照例討厭他的一身儒服,他就改穿楚人樣式的短衣。他為漢王舉薦人才,全是以勇力聞名鄉里的強盜大猾,跟從他的百余名儒生弟子,竟無一人在舉薦之列。弟子們私下里罵他,他就反問他們,現在正是力戰的非常時期,你們有力嗎?你們能戰嗎?
待到漢王以力定天下,叔孫通果然更能大顯身手。他為漢家做的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便是率眾弟子及魯國儒生制定朝儀。此朝儀兼采古禮和秦儀,意在張揚大漢天子的威勢,凸顯法家“君尊臣卑”的政治理念。昔日的漢家朝廷就像一個亂哄哄的大軍營,上朝的都是隨同劉邦出生入死的功臣,他們飲酒爭功,醉了就狂呼亂叫,嚴重的時候,竟然拔劍擊柱,大打出手。叔孫通的朝儀將此烏煙瘴氣掃蕩殆盡,代之以一套莊嚴肅敬的君臣之禮。新朝儀演練的那一天,一切如儀,滿朝文武的朝拜,讓劉邦終于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覺。
盡管有陸賈和叔孫通這樣的儒生點綴漢廷,布衣將相之局卻不曾有多大的改觀。在武力功臣的把持下,知識人很難有仕進的機會,這種局面幾乎一直維持到漢武帝初年。賈誼年少即通諸子百家之書,20余歲成為文帝朝最年少的博士。文帝對這位洛陽才子頗為器重,一年中多次予以破格擢升。眼看就要位列公卿了,賈誼卻遭到了軍功老臣的排擠,周勃、灌嬰等一致讒害他說:“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文帝無奈,只好疏遠賈誼,改任長沙王太傅。可憐的洛陽才子,就這樣成了屈原之后又一個“不遇”的典型。
叁
與中央朝廷大不相同,漢初的藩國卻是思想活躍、文采斐然的文化沃土。此時,去古未遠,養士的風氣仍舊濃厚,士人也還保持著戰國時期自由游走的游士風采。重要的是,漢初大封諸侯,在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下還雜有封建制的遺存,藩國的勢力很大,儼然獨立王國,它們的存在,為諸侯王養士提供了條件,也使士人的自由游走成為可能。還有,功臣集團把持朝政,妨礙了士人在中央朝廷的晉身之路,除了走向藩國,他們還能走向哪里呢?
鄒陽、莊忌、枚乘等游士來到了吳國。他們都留有戰國縱橫家遺風,以文辯馳名天下。吳王劉濞乃高祖親封的同姓王,一向驕貴,吳又有銅山海鹽之利,于是廣招亡命之徒,私自鑄錢煮鹽,一時富甲天下。四方游士紛紛涌向富庶的吳國,劉濞也厚待游士,欲借以擴充勢力。到景帝時,經過四十余年的苦心經營,吳王在漢天子眼中已成尾大不掉之勢。一面是朝廷的步步摧折,一面是劉濞的蠢蠢欲動,最終演成吳楚七國的大叛亂。
“七國之亂”實為大一統秩序的反動。渴求天下秩序定于一,一直就是百家爭鳴以來士人的一種情結。經由秦末的混亂之局,士人更是祈盼由一人整治天下秩序,所以,面對劉邦以布衣之身平定天下,漢初士人大多為之歡欣鼓舞。來游吳國的鄒陽、枚乘之輩,以他們縱橫家的眼光,觀出了此間的歷史大勢。他們知道,眼下的藩國,比如劉濞的吳國,它們的興盛一時,至多不過是往昔封建制的回光返照而已。所以,當發現劉濞確有謀反之志時,鄒陽和枚乘都曾上書苦心勸阻。在鄒陽的說辭里,諸侯不過是一些鷹類的鷙鳥,而漢天子則是兇猛的大鶚,兩方的實力對比,簡直就不成比例。枚乘的游說也充滿比喻性的說辭,他將吳王的恣意妄為比作“一縷之任千鈞之重”,又比作“抱薪而救火”,或者“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預告了吳王的災難性后果。
但是吳王依然執迷不悟,鄒陽、枚乘等不得不游至梁國。梁王劉武乃景帝同母弟,最受天子和竇太后親愛,宮室車馬之盛擬于天子,珠玉寶器之多過于京師。梁國早已成為一個巨大的游士集散地,四方豪杰和山東游士多會于此。梁王政治上野心勃勃,欲求立為太子,山東縱橫之士,如齊人羊勝、公孫詭之輩,正可以為之謀劃奔走。梁王還頗好辭賦,這些縱橫之士在謀劃奔走之余,或游觀射獵,或風流宴集,枚乘、莊忌、鄒陽甚至羊勝、公孫詭,都是梁苑雅集時的作賦好手。
梁苑的風流儒雅甚至還吸引了遠在京師的司馬相如。此時,司馬相如正在朝中為武騎常侍,景帝不好辭賦,這位風流才子的日常工作,便是侍從景帝格斗猛獸。正在郁悶之中,梁王來朝了。此次隨從的正有枚乘、鄒陽之徒,司馬相如與他們一見如故,談說甚歡。枚乘、鄒陽等人走后,司馬相如即刻稱病辭職,來游梁國,過了幾年與英俊并游的日子。因為有了司馬相如,梁苑更增添了幾分浪漫氣息,尤其是苑中的宴集賞雪,成為千古文人懷想不已的風流雅事。
還有淮南和河間兩國,也是當時游士喜游之國。淮南河間,一浮華一樸實,南北相映,皆蔚為大國。淮南王劉安崇尚辭賦,又致力于擴充勢力,藩國氣質近乎梁吳;而河間獻王劉德喜好書籍,修學好古,天下儒士,多從其游,其質實之風,在眾多藩國中一枝獨秀。
只是游士們自由浪漫的好日子,不會太多了。“七國之亂”業已平定,中央朝廷仍在緊鑼密鼓地“削藩”,而且朝廷自身也在努力變成一個文治的政府。游士們游走的空間在一天天縮小,而通往朝廷的仕進之路,卻一天天暢通起來。
文化的熏染,文化精神的養成,以漸不以驟,全然不似急風暴雨式的易姓革命。由一個質多文少的平民政府轉化成一個平民的文治政府,應該說,這是一種趨向,一種歷史的必然。只是大漢王朝幾乎還沒有邁開步子,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
士人真要涌進朝廷成為知識分子官僚,也就是士大夫,還必須等到漢武親政。正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改變了儒學的命運,改變了士人的命運,自然,也改變了大漢帝國的命運。
肆
漢初的草莽氣息和文化荒蕪幾乎持續了七十年。其間近四十年為文景之世,它以休養生息的治國方略為后世所津津樂道。休養生息要在因循簡易,仁惠寬儉,實不過是漢廷一時的權宜之計。創造傳奇的英雄時代業已逝去,創造新的傳奇則尚需時日,此間最有可能出現的是一些創造力相對平庸的所謂“繼體守文之君”。特定的歷史情勢已為文景設定好了角色,他們選擇黃老之學作為治國之道,積極地看,為大漢帝國的崛起積累了元氣;消極地看,務在養民不過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如果細究起來,黃老之學的清靜無為,只是一種表象,骨子里卻是尊崇刑名法術。循名責實,行一點法術,再加一點恭儉,便成了“無為而民自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文景朝的政治,是一種粗放并且軟化了的法家政治。
漢初黃老之學中的人物,今天只能從歷史里看出一些模糊的身影。最著名的應當是蓋公,或許正是經由他,黃老之學得以走進朝廷。曹參來到蓋公所在的齊國做丞相,下車伊始即召集長老和儒生,請教治理百姓之道,百余名儒生竟言人人殊,令曹參不知何從。機會留給了黃老之學,蓋公順理成章地做了曹參的智囊。蓋公的治民之道不外“清靜”二字,所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曹參按照蓋公所言治齊,“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在齊國,儒學甚至尚未與黃老之學展開正面交鋒,便敗下陣來。
后來,曹參繼蕭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這便是著名的“蕭規曹隨”。曹參將相齊的地方性經驗上升為整個帝國的經驗,他的丞相府充滿了木訥少文的忠厚長者,這群老者無所事事,只管日夜飲酒。有些朝中大員實在忍無可忍,就到丞相府進言。曹參的辦法很絕,來人一進丞相府,便招呼飲酒,并且一定要飲最好的酒。一巡酒下來,來人想說話了,曹參就再令上酒,直到客人酩酊大醉為止。
伍
漢武帝即位第六年,竇太后崩。漢武帝親政后的大漢帝國,才真正步入不可一世的“漢武時代”。此時,阻礙儒學崛起的勢力一一消退,武帝更銳意推明孔氏,表彰六經。一向崇儒的田蚡做了丞相,黃老、刑名等百家之言正式遭到罷黜,在立五經博士的基礎上,朝廷又為博士官置弟子員,同時勸以官祿,通一經以上者即可入仕。一個新的儒學時代到來了。
漢武帝卓然罷黜百家,而獨尊儒術,大儒董仲舒曾起過決定性的作用。武帝初即位,舉賢良文學百余人,董仲舒即在被舉之列。武帝三次制詔,董仲舒三次對策,遂脫穎而出。其對策大意,在于去刑法而任教化,而若任教化,則必獨尊儒道。可見“罷黜百家”之議,實最早出自董仲舒。
董仲舒的思想,也給年輕的天子以巨大震撼:表彰六經,以儒家之道治理天下,即是“退而更化”。明曰“退”,實則“進”,表面看是“復古”,實際上卻是制度的創新,文化的創新。
不過,漢武帝向以“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著稱,他喜好儒術,更多出于功利主義的考量。董仲舒和公孫弘在漢武朝的不同遭遇,正可說明漢武儒學的真相。董仲舒對策勝出,卻僅派任江都王相,其間一度廢為中大夫,甚至還因言災異而獲死罪,有詔特赦,才保全性命。后董仲舒改任膠西王相,因懼怕日久獲罪,不得不稱病免歸。而公孫弘,不過是曲學阿世之輩。治學上,公孫弘并非獨治儒學,還頗習文法,更擅長以儒術緣飾吏事。對如此一介俗儒,漢武卻尤其器重,十年間由博士而至丞相封侯。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這是漢代士人常說的一句套話。漢武帝正是“非常之人”,也果真建有“非常之功”。在他的手上,大漢朝廷終于發現了文化的力量,認清了儒學的真相,從而找到了適合于自己的意識形態,完成了由質向文的全面轉型。而作為文化載體的士人,也由游士一變而成“彬彬多文學之士”的士大夫。于是,大漢帝國自此進入一個全面崛起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