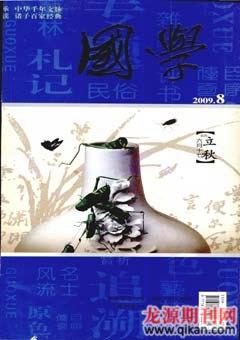文人行乞
陶方宣
古代文人落魄起來,只能跟流民一樣行乞,是乞討的乞,不是行竊的竊。餓到行竊就難看了,只有孔乙己的竊書者不為偷才稍顯風雅一點。文人行乞的不少,徐文長、唐伯虎都是。
文人好象很容易落魄,不會八面玲瓏,又不屑于經商,見到當官的還把腦袋瓜子抬得高高的,這樣下去哪有好日子過?老早的孔子蓬頭垢面坐在馬車上周游列國也相當于行乞,只是他學生太多,看不得老師餓飯,一人送一瓢小米一條臘肉,孔夫子的小日子就過飛了。古代士大夫伯夷叔不食周粟,寧愿在首陽山餓死,不知他討過飯沒有。晉人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回家到南山下開荒種豆連帶栽點菊花,當然比外出行乞要好一些。近人朱自清不吃日本米,因為他有筆,能賣文為生。其實要說起來,文人行乞還算好,不用賣唱賣身,他只要賣字賣畫就行,也算是發揮專長。
徐文長晚年一直以賣畫為生,他詩中就有“數點梅花換米翁”的句子,就是說你要買我畫的梅花不要緊,得按畫上梅花朵數決定米的數量,九朵梅花九斤米,十八朵梅花十八斤米,不能討價還價。有人送來十只螃蟹,他畫一只墨蟹送他;有人拿來三壇子好酒,他畫一壺酒再畫三個蘿卜謝他,雙方各取所需皆大歡喜。有米有蟹還有酒,這日子過得可美。傳說有天徐文長又沒得吃了,也沒人來買畫,張三看他挨餓,拋著手里的銀子捉弄他說:徐先生,有本事你讓李四呱呱呱叫三聲,我請你下館子,菜隨你點。徐文長說這好辦,帶著李四來到瓜田邊,指著一地滾圓的瓜說:這葫蘆長得真好。李四一看不對,糾正道:是瓜。徐文長不聽,繼續說:葫蘆葫蘆葫蘆。李四紅了臉,反駁道:瓜瓜瓜!張三在一邊笑倒,馬上帶徐文長下館子——好笑吧,文人行乞往往就留下民間傳說,這是中國特色,在世沒人管無人問,死后卻把風流韻事一齊往他身上堆。
唐伯虎便是這樣,當不了官,斷了仕途,最后就離開了家,開始討飯,其實他哪里有什么桃花叢中三笑點中美人秋香姑娘啊?他后期一直乞討為生。據說有次一群文人墨客聚會,要求賦詩飲酒,唐伯虎碰見,懇請讓他試試,人家笑他一個乞丐也能寫詩,就等著看笑話。他提筆寫下“一上”兩字,這根本不是詩的開頭,眾人搖頭,唐伯虎要酒,大家拿酒拿肉,看他如何把洋相出下去。他又寫了“一上”,眾人笑倒,這詩沒法往下寫了,他卻一口氣寫下去: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直到高山上,舉頭紅日白云低,四海五湖皆一望。眾騷客滿座驚奇刮目相看,想不到乞丐堆里竟然藏龍臥虎,一個個就慚愧得低下頭。
其實憑良心說,這首詩算不得精彩,也談不上深遠的意境,但這則文人行乞的故事,則畫出了一位中國文化人游戲人生遺世獨立的瘋顛和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