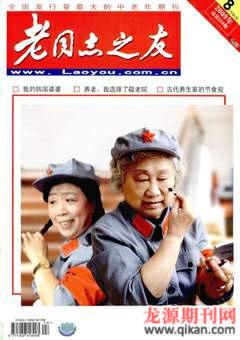千辛萬苦行大道
戴 墨
“沈水之陽,砂山域中,一幟迎天,列翠爭蔥;群樓環峙而立,軍營盤踞而雄。館居一隅,遙現白山黑水;物涵萬象,隱聞玉振金聲……”
沈陽軍區后勤史館落成了,在眾多高樓大廈的比肩下也許是矮小的。然而,它卻是一條筆直而寬敞的人間大道;
館長徐文濤大校,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用他夜以繼日的精神行走,歷盡千辛萬苦,燕子銜泥般地一個字、一個字地壘起了后勤60年的歷史豐碑!
千軍易得 一將難求
“欲行大道,必先知史。”這個“夙愿”早在聯勤部黨委們心里不知醞釀多少時日了。高樓大廈越建越高,亭臺樓閣越建越寬敞,可是,供歷史回顧接受革命教育的空間卻越來越窄了、少了!大多數人還存著“戰爭離我們很遠”,“我們離打仗很遠”的安逸之心……經過軍區聯勤部黨委的再三斟酌,決定建一個“后勤史館”,并把這副擔子交給了徐文濤。
徐文濤,1970年當兵,滿打滿算也近40年了,工作崗位從倉庫政工干事到軍區戰勤參謀,從秘書到醫院副院長、分部參謀長等一調再調,始終沒離開過后勤口。沒有人能比他更了解后勤發展史了。
高血壓、糖尿病,這都是些老病根兒了,最讓徐文濤不能釋懷的是那些善意的“勸誡”,諸如,一個后勤史館,不就是些吃喝拉撒的事兒嘛,你這么玩命還能折騰出啥名堂?但徐文濤心里憋著一股勁兒!他要把后勤史館建成“傳統教育的基地、學術研究的平臺、信息傳遞的中心、對外交流的窗口”,讓人們充分認識到后勤不“后”。
千回百轉 別開生面
有位老首長聽說他搞史館建設,主動給他當參謀,人在病床上還打電話告訴他又搜集到了哪些老照片。他記著老首長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我們時間不多了,趁著這把老骨頭還沒進棺材,也要對黨貢獻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與此同時,徐文濤看了幾十萬字的資料。想從浩如煙海的歷史長河中提取一粒火種,更不知磨薄了幾雙鞋底,僅軍內外有名的展館就跑了40多家。回來時,人瘦了一大圈。不說館內大項的土木修建工程設計,就是墻上的每個釘,地上的每塊磚,窗上的每塊玻璃到每種色彩,徐文濤都是拿眼睛一個個、一塊塊“盯”出來的。更別說館內幾萬字的文字說明、上千件珍貴的歷史文物以及2000余幅圖片的搜集整理打印編排等等,他時刻都像一只“銜泥壘巢”的燕子,更像一只嗅覺靈敏的老鷹。一天,駐地晚報披露一條有位老漢想給戰爭年代保存的11張收條找個家的信息,徐文濤立即趕到老人家。11張珍貴的收條成了館藏。他走后,有20多個單位相繼派人到來,當聽說被一位軍人捷足先登時,他們不得不嘆服:“軍人速度!我們來晚了。”
去年深秋,徐文濤到北京某機關查資料,好說歹說,他才得到幾小時的許可。后勤各部門的大事記、將帥名錄太豐富了。徐文濤興奮不已。直到晚上9點多,人家都下班回家了,看完晚間的新聞了,才恍然“想起”還有這么個人關在資料室。他早該走了吧?推門一看,人家嚇一跳,正埋頭在燈光下專心抄寫的那人,頭發已顯斑白,連身后站個人都不曾發覺……
千秋功業 山高水長
后勤史館開館那天,在遼沈大地的一隅仿佛再現了又一個長征勝利會師的盛況。毛主席當年的警衛參謀蔣澤民坐著輪椅來了;毛主席的“挑夫”龍開富的女兒領著兒子、兒媳來了;當年紅軍過臘子口的關鍵時刻,給毛主席找“報紙”的功臣曹德連的老伴兒領著兒子來了;當年挑著縫紉機長征的“紅軍裁縫”葛接調的孩子們來了;還有三過草地的老紅軍朱士煥也來了……
正式開館前兩個月,請求參觀的電話就快打爆了。不得不提前開館,省直各機關、新聞媒體、國有企業、干休所、學校、駐沈部隊……接踵而至!
無論新兵、老兵,他們走著,看著,不時激動地發出唏噓、驚嘆之聲。從1945年10月31日,東北人民自治軍總后勤部成立這天起,到東北解放戰爭、抗美援朝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以及“一切為打贏”的軍事變革新時期,他們不光尋到了自己沖鋒陷陣的身影,也看到了一代又一代后勤官兵前仆后繼的奮斗軌跡。
陳云的女兒陳偉力凝望著老父親在戰爭年代指揮若定的老照片,更是熱淚盈眶。她在留言簿上鄭重地寫下了自己的心聲:你們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牢記歷史,珍惜現在,開創未來。
不管怎么累,徐文濤心里都是甜的。當一撥又一撥老的,少的呼啦啦走進史館,他就仿佛看到了越來越多的“革命的火種”將一個個走出去傳播新的希望……“強大的后勤,勝利的保障”,那閃光的大字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支接力棒!
(沈陽軍區后勤史館現正向全國征集史料,詳情請見本期61頁)